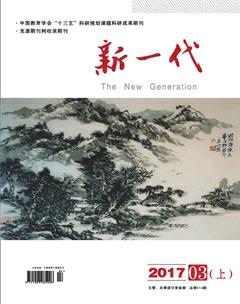淺議高效課堂在初中語文課堂中的構建方法
牛秀芳
(通渭縣雞川中學 甘肅 定西 743316)
摘 要:語文教學是初中的重要課程,可使學生在獲得知識的同時有全面的發展。在新課改背景下,對語文教學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我們要不斷更新自己的教學理念,完善自己的教學方式,為高效課堂的構建奠定基礎,以滿足學生的發展需求,為社會培養合格的人才。
關鍵詞:初中語文;高效課堂;構建
目前,新課改實施的如火如荼,教學改革的內容也逐漸深入,各科教師都將高效課堂作為了自己對教學工作追求的目標。因此,我們要不斷地對自己的教學理念進行革新,完善自己的教學方式,為高效課堂的構建奠定基礎,以滿足學生的發展需求,為社會培養合格的人才。目前,語文教學的狀況不算太好,教師經常為教學效率的低下而感到苦惱。為了實現高效課堂,我們應該在教學過程中采取怎樣的措施呢?在多年的初中語文教學中,筆者總結了一些相關的經驗,現對此進行一些淺顯的研究與論述。
一、教師的教學觀念要不斷更新,實施探究式教學
我們要通過教學觀念的改革促進探究式教學模式更好、更快地實施,使學生具備探究的精神和能力。而學生的自主探究才能使我們的教學效果高效。如進行七年級下冊第三單元《聞一多先生的說和做》的學習時,為了使學生對本文能有一個整體的感知,我對學生提出了以下幾個問題:(1).文章利用“說”和“做”兩個方面對聞一多先生進行描寫,作者是怎樣將這兩個方面結合起來的?(2).通過作者的描寫,你能夠看到一個什么樣的聞一多先生?(3).文章中描寫“說”部分有哪些?描寫“做”的部分有哪些?(4).文章的開頭是用聞一多先生的兩句話引入課文的,這樣寫有什么好處?(5).在文中,作者引用了唐代詩人杜甫在晚年時的“一月不梳頭”的典故,為什么要這樣引用呢?作者的用意為何呢?隨后,我讓學生結合這些問題在自主閱讀的基礎上對本文進行深入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與同組的同學進行討論,也可以去請教教師,要努力在閱讀中找到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尋找答案的過程中,學生會對文章內容有一個整體的把握和感知,他們的探究活動不僅能夠有效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能夠讓學生的主動性得到充分的發揮,他們在學習中的主體作用就能夠由此得到更好的體現。在這種學習模式下,學生對文本的理解就會更加深入,感知力也會加強,課堂教學收到了良好的效果,能夠在不知不覺中實現高效課堂的構建。
二、為學生創設適當的教學情境,激發學生的興趣
要想使教學效率得到有效提升,為學生構建高效課堂,我們首先要做的就是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只有使學生對知識的學習有了期待,有了濃厚的興趣,他們才會全身心地投入其中。這樣,我們的課堂教學也能實現高效,收到理想的效果。因此,在課堂教學過程中,教師要逐漸改變自己的教學方法和教學手段,利用豐富多彩的教學措施來吸引學生的注意力,讓學生能夠對學習內容充滿興趣,積極地完成知識的獲取,主動去對知識進行更加深入的探究,以飽滿的熱情和昂揚的斗志參與到教學活動中去。如進行《爸爸的花兒落了》的學習時,為了讓學生更好地感受文章的意境,我沒有采取以往那種平鋪直敘的講述方法,而是為他們創設了一定的情境,利用情境的力量來激發學生對于教學內容的興趣,使學生的心神全都融入當時的情境之中。具體做法如下:我在進行課堂導入時利用多媒體為學生播放了一首經典名曲——《送別》。悠揚婉轉的歌聲輕輕響起,時時回蕩在學生的耳畔“:長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在歌聲中,學生感受到了知己相交的珍貴,一種淡淡的憂傷涌上心頭。學生的情緒會隨著這首歌而起伏,不用教師再做過多的鋪墊和引導,也不用對教學進行多么精心的設計,學生就會在不知不覺中進入文章的意境之中,并主動進行閱讀和探索。利用音樂的力量,我為學生創設了與課文中的情感和體會大致相似的情境。這樣做不僅能夠使學生在教師所渲染的情境下順利地進入文中所描繪的場景,體會文章所要表達的思想情感,促發學生的學習動機,使他們對新知識的學習充滿興趣,還能幫助學生對本文的主題產生更加深刻的感悟。
三、在教學過程中進行情感教育的滲透,激發學生的情感
作為新時代的教師,我們的教學改革也包括在語文教學中進行情感教育的滲透,利用語文學習完成思想道德的培養,并幫助學從中獲得語文素養。比如,在學習七年級下冊第六單元《斑羚飛渡》這篇課文時,我首先通過運用朗讀法,讓學生對課文進行反復的閱讀,以深切感受老斑羚從容鎮定、犧牲自我的精神。然后再利用情景設置法,利用多媒體軟件為學生播放斑羚跳過懸崖時的幻燈片,使學生自然融入到課文的意境中去,與文章作者產生思想上的共鳴。利用這兩種教學方法可使學生深刻體會到文章真切細膩的描寫所蘊含的強烈情感,從而促使學生學習老斑羚那種從容鎮定、舍己為人的高尚品格,進而學會關愛動物,善待其他的生命,珍惜每個生命的存在,并珍愛自己的人生,達到了情感態度與價值觀教育的目的,為初中語文高效課堂的構建提供有效的條件。
綜上所述,初中語文高效課堂的構建工作并不是朝夕之間可以完成的,我們需要對此付出長期的努力和探索。我愿意和廣大語文教師一起,共同研究和總結符合初中階段學生學習特點的教學策略和措施,使初中語文課堂在我們的帶領和學生的配合下,獲得高質量、高效率、高收益的課堂教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