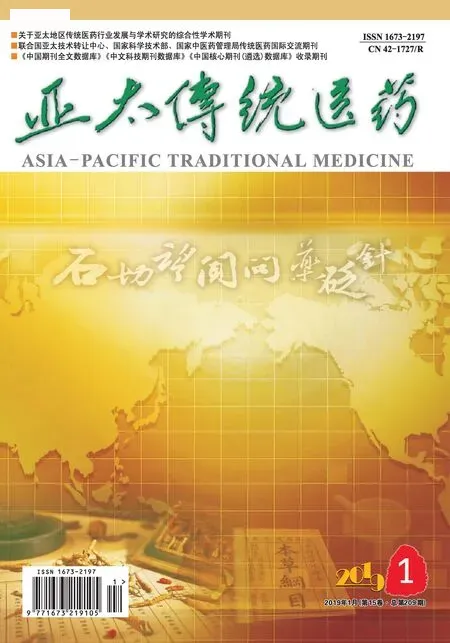呂冠華應用仲景方治療便秘臨床經驗總結
,
(1.遼寧中醫藥大學,遼寧 沈陽 110032;2.遼寧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遼寧 沈陽 110034)
便秘即大便秘結不通,排便周期延長,或周期不長,但糞便干結,排便艱難或糞質不硬,雖有便意,但便而不暢的一種病癥。漢代張仲景在《傷寒論》中稱其為“脾約”“閉”“陽微結”等,金元時期又有“虛秘”“風秘”“氣秘”“熱秘”“寒秘”“濕秘”“熱燥”“風燥”之分。中醫藥治療便秘多從潤下通便入手,為目前治療慢性功能性便秘的首選方法。呂冠華教授現任遼寧中醫藥大學附屬第二醫院脾胃肝膽科主任,研究生導師,從事脾胃肝膽科科研及臨床工作20余年,潛心研究專業學術,并不斷臨驗,在脾胃肝膽科常見病和疑難病的診治方面已經取得了很大成就。其近年來應用仲景方治療便秘取得了良好的臨床療效,現整理總結如下。
1 白術附子湯—溫陽通便法
白術附子湯具有祛風除濕的功效,主治風濕相搏,身體疼煩,不能自轉側,不嘔不渴,脈浮虛而澀,大便堅,小便自利。《金匱要略·痙濕暍篇》云:“若大便堅,小便利者,去桂加白術湯主之。”白術附子湯證出現便秘的機制是脾陽虛弱,水濕布散失調,一方面濕邪停滯風濕之證仍在,一方面脾不能主宰大腹,腸道運動減弱,大便不行同時脾為胃行其津液的功能下降,水液輸布失衡,水液盡走前竅而致便秘,腸道失其津液,更加重便秘的發生[1]。
驗案舉隅:患者呂某,男,78歲,2015年1月23日初診。主訴:大便10日未解。現病史:排便困難30余年,平素靠服用大黃、番瀉葉、果導片等維持,若不用藥,五七日不大便。就診時癥見:大便10日未解,多次便清水,飲食可,睡眠一般,舌淡紅,苔薄白膩,脈沉弦。中醫診斷:便秘(陽虛濕盛證),治以溫陽化濕,方用白術附子湯加減,處方:生白術100g、肉桂10g、厚樸20g、附子10g、干姜10g、桃仁10g、紅花10g、陳皮10g、當歸20g、木香10g、藿香10g、萊菔子15g。10劑,每日1劑,水煎服。2015年2月25日二診:服藥后1~2日排成形軟便1次,近日停藥后排稀水樣便2次,無腹痛,手足不溫,舌淡紅,苔薄白,脈沉細。效不更方,原方14劑。后患者間斷服藥,排便情況良好。
按:患者為老年男性,脾虧虛,陽氣虛衰,陰寒凝結,水濕內停,腸中糟粕難以下行,故見便秘。導師考慮到此患者雖有熱結旁流之征象,但舌淡紅,苔薄白膩,脈沉弦并非實熱之證,故用白術附子湯加減,療效甚好。方中附子溫陽通氣、溫補腎陽,除機體內寒濕之邪,還可解大便硬;白術健脾溫陽、化濕益氣,助脾運化以散其津液,解除便秘之苦,配附子加強其散寒之力,配肉桂、干姜以增強溫陽之功;木香、藿香配伍則可芳香化濕,除腸中之寒濕之邪。全方配伍,陽氣得運,寒散積化,化氣行水,內輸腸胃而大便自調,乃治病求本之法。
2 小柴胡湯—表里雙解法
小柴胡湯為和解少陽病之主方。《傷寒論》云:“傷寒五六日,頭汗出,微惡寒,手足冷……設不了了者,得屎而解。”《金匱要略·婦人產后病脈證第十一》云:“產婦郁冒,其脈微弱,嘔不能食,大便反堅,但頭汗出,所以然者,血虛而厥,厥而必冒……大便堅,嘔不能食,小柴胡湯主之。”小柴胡湯治療的便秘乃是仲景所謂的陽微結,是邪結于胸脅,熱郁于里,氣機不利,津液不下,胃氣失和所致的便秘,較陽明里實熱燥結之證,熱結尚淺,且表證未解,故稱陽微結。
驗案舉隅:金某,女,31歲,2015年6月12日初診,主訴:便秘伴腹脹6日。平素便秘,平均2~3d一行,口服果導片或番瀉葉后緩解,患者10日前剖腹產后6日未大便,排出少許糞塊,干如羊屎,仍腹脹,遂來就診。就診時癥見:惡寒重,發熱輕,頭痛如裹,腹脹,食欲差,呃逆,噯氣,乳汁少,平素脾氣暴躁,近日更重,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尺脈尤弱。中醫診斷:便秘(氣血虛弱兼風寒證),治以疏風散寒、益氣通便,方予小柴胡湯加減,處方:柴胡30g、黃芩15g、太子參10g、生姜10g、姜半夏10g、通草10g、王不留行10g、炙甘草10g、大棗10枚。7劑,每日3次,水煎服。2015年6月20日二診,服藥后每天可排便,頭痛減輕,食欲好轉,舌淡紅,苔薄白,脈弦細。原方加生白術30g,另囑患者避風寒、調飲食、暢情志、勿過勞。
按:患者平素津虧,氣血失運,外感風寒之邪致腸道失潤,糟粕干結,腸腑無力推動燥屎運行而致便秘,且病史較長,無痞滿燥實等實熱之征象,又因產后血虛,故不能猛攻峻下,而選用和解劑小柴胡湯來運轉樞機、和解表里。小柴胡湯中既有祛邪清熱的藥物,也有扶正補虛之藥。方中重用柴胡,正如《神農本草經》中云:“柴胡味苦平,主治心腹腸胃中結氣,飲食積聚,寒熱邪氣,推陳致新。”從而發揮推陳致新、疏通郁結、透熱外出之功效。黃芩清中上焦熱邪;姜半夏和胃降逆;人參、炙甘草扶助正氣抵抗病邪;生姜、大棗和胃生津,運轉輸機,利三焦通暢。諸藥合用,共奏開郁散結之功,上焦得通,津液得下,則便結自除。二診時加生白術健脾益氣,大劑量兼有潤腸作用。
3 小承氣湯—瀉下通便法
小承氣湯為熱結峻下之良方。陽明病里熱熾盛,迫津外泄,以致胃腸內津虧干燥而結實,故大便必硬,臨床常見譫語潮熱,大便秘結,胸腹痞滿,舌苔黃,脈滑數。痢疾初起,腹中疼痛,或脘腹脹滿,舌苔黃,脈滑數。《傷寒論》第213條云:“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小承氣湯主之。”
驗案舉隅:患者黃某,女,55歲,2014年12月21日初診,主訴:便秘伴腹脹腹痛3日。診時癥見:大便干,排便不暢,進食后胃脘脹滿,口干,飲食一般,睡眠可,舌淡紅,苔薄黃,脈沉弦。中醫診斷:便秘病(實熱證),治法:通腑泄熱,方用小承氣湯加減,處方:枳實10g、厚樸20g、酒軍15g、當歸15g、生地20g、大腹皮10g、杏仁10g、石膏30g、炙甘草10g、木瓜15g、香附10g、火麻仁20g、地龍15g、川牛膝15g,7劑。水煎服,每日1劑。2015年1月1日二診:服藥后大便1次/2d,便后軟,排便通暢,胃脘脹滿緩解,舌淡紅,苔薄黃,脈沉弦。處方改枳實為枳殼,加丹皮、太子參各10g,14劑。三診:大便通暢,諸癥減輕,續以補氣養血調理3月,體質好轉,隨訪1年未復發。
按:患者為中老年女性,平素脾胃虛弱,中氣不足,脾胃運化功能虛弱,致腸中糟粕無以下行,致排便不暢。《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年四十,而陰氣自半矣,起居衰矣。”隨著年齡增長,脾胃虧虛,氣血生化乏源,腸道推動無力,糟粕停滯腸腑,蘊濕生熱而致便秘;口苦、苔黃為腸腑熱結,方用小承氣湯為主。一診時以行氣導滯為主,酒軍、枳實、厚樸為小承氣原方,有行氣導滯之功,佐以石膏泄熱、大腹皮行氣,杏仁、火麻仁潤腸通便,全方配伍,能解便秘之苦。二診時,將枳實易為枳殼,以減其破氣之功,加丹皮、太子參以養陰潤腸通便。三診時則以補養氣血為主,以復其本。導師認為治療便秘時不能一味攻下,應與滋補潤燥相結合,還應辨清其標本緩急。
4 四逆散—行氣導滯法
《傷寒論》中記載四逆散治療泄利下重,導師認為便秘與泄利下重同為胃腸之病,所涉及臟腑相同,病機均為升降失調、氣機不暢、傳導失司。《傷寒論·辨少陰病脈證并治》云:“少陰病,四逆,其人或咳或悸,或小便不利,或滑利下重者,四逆散主之。”大便的排泄正常與否既與大腸的傳導密不可分,又與肝的調達疏泄息息相關。情志不暢則肝氣郁滯,大腸之氣不得肝之疏泄,則傳導失司,糟粕蓄而不下引起便秘。
驗案舉隅:患者章某,女,49歲,2016年2月1日初診。主訴:便秘10d。就診時癥見:素往便秘,成羊屎狀,數日一行,無便意,有明顯腹脹,月經不規律,舌質紅,苔薄白,脈細弦。中醫診斷:便秘(氣秘),治則:行氣導滯,方以四逆散加減治療,處方:柴胡10g、枳實10g、白芍15g、厚樸15g、桔梗10g、杏仁15g、火麻仁15g、郁李仁15g、炙甘草10g。7劑,每日1劑,水煎服。二診時,癥狀明顯好轉,效不更方,14劑。
按:患者為中年女性,處于絕經期前后,肝氣不疏,氣滯不行而致便秘。肝主疏泄上下一身之氣機,胃腸道氣機通暢,則燥屎自除。《醫學入門》最早提出了肝與大腸相通的理論。方中柴胡、芍藥配伍為肝膽藥,枳實、甘草同為脾胃藥,此二組能疏肝理氣、調和脾胃,芍藥與甘草相伍可除血痹緩攣痛;枳實與芍藥配伍,一氣一血,有行氣活血之功,柴胡與枳實配伍,一升一降,升清降濁。縱觀此方,其主要功效為暢達氣機、疏肝理氣、調和脾胃,其作用部位為肝膽、脾胃、大腸。
5 芍藥甘草湯—滋陰通便法
芍藥甘草湯在《傷寒論》中主治腳攣急,其病機為血脈凝滯、痹阻不通,但《傷寒論》中并未提及芍藥及甘草有養陰血之功效。《名醫別錄》中指出:“腳及伸,陰血行也。”《傷寒論》第29條云:“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作甘草干姜湯主之。若厥愈足溫者,芍藥甘草湯主之。”《傷寒論》中滋陰通便法多用麻子仁丸,而導師認為治療脾陰不足、腸燥津乏的便秘應首選芍藥甘草湯。脾為陰中之至陰,至者大也,其陰液充滿全身;至者達也,而散精于全身。脾陰不足,則全身津液匱乏,胃腸道津液不足,故可見燥屎難下。
驗案舉隅:患者劇某,男,4歲,2017年1月5日初診。主訴:大便干,3日未解。病史:患者平素大便干,3~5日一行,3日前無明顯誘因,大便干結,腹部脹滿,飲食一般,睡眠安,舌淡紅,苔薄白,有剝脫,脈平。中醫診斷:便秘(陰虛證),治則:滋陰潤腸通便,以芍藥甘草湯加減,處方:白芍30g、甘草10g、玄參15g、生地20g、麥冬20g、萊菔子30g。14劑,每日1劑,水煎服。二診時,癥狀明顯緩解,便軟。處方:上方加厚樸20g,繼服14劑。
按:患者為小兒,其生理特點為脾常虛。患兒平素便秘,辨證為脾陰虛證,遂用芍藥甘草湯加減以滋脾陰,又佐以增液湯以滋陰潤腸通便;大量萊菔子可增其胃腸動力。全方配伍能促進胃腸道蠕動,滋陰通便。
6 結語
導師根據多年臨床經驗總結出經方對便秘的一些治法,如溫陽通便、表里雙解、泄下通便、行氣導滯、滋陰通便等法,認為臨床上單獨腑實熱秘者少見,虛型及虛實夾雜者較常見[2]。仲景對便秘的論治分為清下法、溫下法、順氣導滯法、逐飲瀉下法、陽明三急下、少陰三急下、增水行舟等,其治療便秘立論全面,辨證靈活,治法多樣,而并非實熱陰虛等概之,總之以通便為主,更應辨清寒熱虛實,采用峻下、溫下、和下、潤下等多種方法[3]。《傷寒論》中的經方在臨床中應用廣泛,只有緊扣病機,注重辨證,才能保證臨床療效;只有充分理解其含義,經方運用的思路才能進一步拓寬,應用范圍才能進一步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