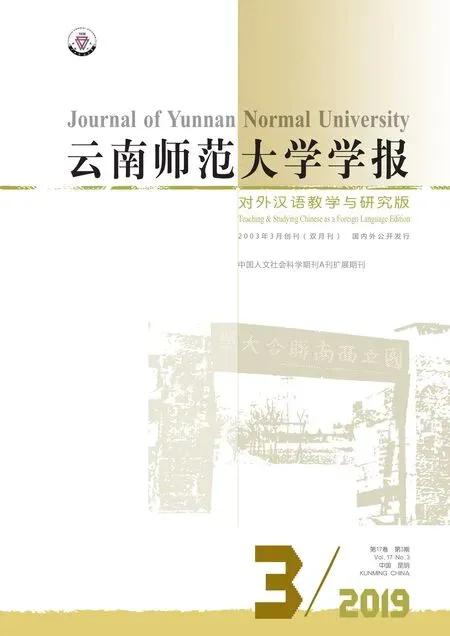從語言學三問看各流派的語言觀*
俞勇連
(北京師范大學 漢語文化學院,北京 100875)
一、引 言
關于語言學流派的研究,目前學界主要從分析該學派形成的社會背景,介紹代表人物、學術著作以及基本的語言學理論等宏觀角度描寫流派的發展變化。這些方面的研究以專著居多,主要有《現代語言學流派》[注]馮志偉.現代語言學流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現代語言學流派概論》[注]封守信.現代語言學流派概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西方語言學流派》[注]劉潤清.西方語言學流派[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4.。此外也有少量期刊論文對語言學流派的基本情況進行過探討,如《西方語言學流派發展歷程與特征分析》[注]陳子悠.西方語言學流派發展歷程與特征分析[J].和田師范專科學校學報,2007,(2).、《簡述現代語言學流派代表人物》[注]楊靜.簡述現代語言學流派代表人物[J].科技信息,2013,(13).。
除了對語言學流派進行宏觀的歷時研究之外,部分學者也從哲學觀的角度出發對語言學流派的學術淵源進行過探索:《語言學的淵源、流派及其學科性質的變遷》[注]李葆嘉.語言學的淵源、流派及其學科性質的變遷[J].江蘇社會科學,2002,(5).、《語言學與哲學:歷史發展與學派溯源》[注]趙蓉暉.語言學與哲學:歷史發展與學派溯源[J].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2,(1).、《現代語言學流派哲學觀的對立與融合》[注]高秀雪,付天軍.現代語言學流派哲學觀的對立與融合[J].河北學刊,2012,(4).。
以上研究既有對語言學流派萌芽、發展的全面描寫,也有對語言流派內部哲學基礎的詳細分析。本文嘗試從另一個角度,即語言學最基本的三個問題入手看各個流派的語言觀念。
二、語言學三問
在探討“人的語言何以獲得”這一問題時,喬姆斯基否定了行為主義心理學者把語言學習看成是一種“刺激—反應”的觀點并引入羅素晚期著作中所說的“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人與世界的接觸是如此短暫、狹隘、有限,為什么能知道那么多事情呢?[注]喬姆斯基.喬姆斯基語言哲學文選[M].徐烈炯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236.這是喬姆斯基首次將哲學中的柏拉圖問題引入語言研究,同時他把人類知識和經驗關系的問題分解成以下三個方面:
(1)什么是人的語言知識?
(2)人的語言知識是怎樣獲得的?
(3)人的語言知識是如何運用的?[注]寧春巖.什么是生成語法[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11:10.
我們可以將喬姆斯基對語言學三個方面的討論歸結為語言學三問,分別是:語言本質是什么?——“洪堡特之問”;語言來源為何?——“柏拉圖之問”;語言如何使用?——“笛卡兒之問”。
關于人類語言的本質、來源以及使用這三個問題是討論語言學不可避免的話題。而語言研究中最重要同時也極易被我們忽略的就是各個流派背后的語言觀。因此本文打算以語言學的三問為出發點,探討語言學流派背后的語言觀念,從而更好地理解這些語言學流派關于語言的基本看法。
三、語言的本質問題——洪堡特之問
德國政治家和語言學家洪堡特(W.Humboldt)曾提出“語言絕不是產品(Ergon),而是一種創造性活動(Energeria)”,他認為“一個民族的語言就是它們的精神,一個民族的精神就是它們的語言”。[注]馮志偉.現代語言學流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5.喬姆斯基把對語言知識本質的探討叫作“洪堡特之問”。
縱觀語言學的發展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不同時期的學者都曾對語言本質問題進行過探討。
(一)古代語言學時期語言與宗教神話
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的出現以及后來普通語言學的興起,語言學才逐漸成為一門獨立的學科。根據岑麒祥先生的劃分,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歷史比較語言學出現之前的語言研究都屬于古代語言學。雖然古代語言學時期的語言學研究并沒形成統一的流派,但這段時期人們對語言本質的看法有著鮮明的時代特色。因此我們主要從古印度、古希臘以及古代中國這三大語言學傳統來探討古代語言學時期人們對語言本質的看法。
古印度語言學最初是從研究口頭相傳的婆羅門教義《吠陀》中產生。因此古印度人對于語言文字的探討最初起源于研究婆羅門教經典的需要。古印度人的任務是去研究這種神所特有語言,力求正確表達及解釋古代圣典。婆羅門教圣典《梨俱吠陀》中,“語言”是作為人間和天上秩序的維護者、一個威力巨大的神——婆柯而存在。實際上在古印度人看來,語言的本質是神地位的象征和標志,它為神所特有。就像當時的梵語就是一種神的語言,神圣不可侵犯,誰都無法任意改變。
古希臘宗教故事中關于人類語言的看法流傳最廣。根據圣經舊約的《創世紀》第二章記載:“耶和華上帝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種走獸和空中各樣飛鳥,都帶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樣叫各樣的活物,那就是它的名字,那人便給一切牲畜和空中飛鳥、野地走獸都起了名”。從中可以看出亞當最初不會說話,后來上帝教會了他,并且當時自然界只有一種語言。可是之后人類何以會有多種語言,圣經的解釋是這是上帝譴責人類罪過和妄行的結果。由于亞當聽從蛇的教唆偷吃智慧之果,后來子孫繁衍,耶和華變亂天下人的口音,使眾人分散在地球上,從此世界上就分成了多種語言。雖然圣經里并沒有明說“語言”到底是一個什么東西,但從圣經的故事中我們可以發現當時的語言是上帝賜予人類的工具,用來給萬物命名。
古代中國人對于語言文字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文字形成的傳說中。關于文字起源最古的記載可以追溯到《易·系傳》:伏羲畫八卦、上古結繩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書契。種種傳說中,為一般人所接受的是倉頡造字這一說法。倉頡造字獲得較廣泛認可的原因在于我們普遍認為文字是在集體勞動的過程中創造出來以適應社會生產發展的需要。此外古代中國關于語言本質的探討還涉及春秋戰國時期先秦諸子對“名”“實”問題的討論,即名稱與事物之間的關系問題。其中荀子的“名無固宜,約之以命”體現了社會群體的約定俗成的自由選擇對名、實之間的聯系所起的作用。
正如德國哲學家卡西爾在《人論》中所說的那樣:“語言與神話乃是近親。在人類文化的早期階段,它們二者的聯系是如此密切,它們的協作是如此明顯,以致幾乎不可能把它們彼此分離開來。”[注]吳學國.境界與言詮——唯識的存有論向語言層面的轉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對語言本質的理解與神話故事及宗教傳統相結合是這一時期的鮮明特色。縱觀人類歷史,幾乎每個民族傳統都有一段與語言相關的神話傳說,古代語言學史的三大傳統也不例外。
古印度、古希臘對語言本質的看法都起源于原始神話傳說及宗教故事,認為語言的本質是神圣宗教所特有的東西或是上帝賦予的產物。雖然古代中國傳統沒有正式提出“語言”這一說法,但他們最看重的“文字”之起源同樣涉及古書記載的神話傳說。此外從古人對文字、名實問題的討論中我們還可以看出,古代中國對語言文字的看法與古印度、古希臘傳統很大的一點不同在于前者更加注重社會群體以及大眾的作用。
(二)歷史比較語言學認為語言是具備生命活力的有機體
文藝復興帶來的思想解放運動使學者們由中世紀注重神學轉向注重客觀世界和客觀規律本身,近代科學的發現也使人們逐漸探索語言背后的普遍性和聯系性。18世紀末印度梵語語法被歐洲學者發現,古印度學者在發音部位和方法中的準確描寫使其在語音學方面研究取得輝煌成就。19世紀初,西方語言學家繼承了印度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他們開始把比較法運用于確定語言的親屬關系,力圖重建原始印歐語,從此揭開了歷史比較語言學的新局面。歷史比較語言學的產生宣告語言學真正進入科學時代。它是人們以新的方法和視角研究語言的開始,目的是揭示具體語言的特點和規律,研究的是語言的歷史分類和發生分類的問題。歷史比較語言學建立之后人們懂得跨出本民族語言的范圍去尋找其親屬語言。
總體而言,歷史比較語言學家們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已從披著神學和宗教的外衣中解放出來。他們認為語言并非上帝創造也非上層宗教獨有,它作為一種獨立的存在,像地球上的生物一樣有萌芽、發展、興盛、衰亡的自然過程。顯然這種對語言本質的認識與達爾文《物種起源》中的進化論相一致。洪堡特指出:“我們可以把語言比作一幅巨大的織物,其中的每個部分都與其余部分、所有部分都與整體有著或多或少清晰可辨的內在聯系。無論從哪個方面觀察,人在講話時始終只能接觸到這幅織物的一個孤立的部分,然而他卻總是本能地從整體出發去把握這個部分,仿佛在他面前同時呈現著與個別、具體的部分有著必然聯系的所有組成部分。”[注]姚小平.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語言研究[M].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95:105.因此他認為,語言是一個系統,各部分相互牽制。格里姆曾說“語言不可能是別的任何東西;他是我們的歷史,是我們繼承下來的遺產。”[注]J·格里姆( J·Grimm) .論語言的起源[J].張會森譯.語言學譯叢,1960,(2).因此歷史比較語言學家認為語言的本質是一種獨立的有生命活力的有機體,它具有鮮明的歷史性,我們可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去研究這各個要素成分相互聯系的整體,從而構擬出語言的始源語。
(三)結構主義認為語言是一套符號系統
結構主義語言學由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發展而來,主要包括:布拉格學派、哥本哈根學派以及美國描寫語言學。探討結構主義的語言觀我們可以回到結構主義語言學的鼻祖——索緒爾的語言學理論中去。索緒爾的理論集中在《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索緒爾提出的語言學說,是語言學史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對于現代語言學的發展有著深遠的意義。[注]馮志偉.現代語言學流派[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12.索緒爾因此也被稱為現代語言學奠基人。
關于“語言是什么”這一語言本質的問題,索緒爾指出“語言是一種表達觀念的符號系統,因此可以比之于文字、聾啞人的字母、象征儀式、禮節形式、軍用信號,等等。它只是這些系統中最重要的”。[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41.他認為語言本質是一個符號系統,與字母、禮節儀式、信號等的作用一致,是表達思想觀念的方式之一。索緒爾認為:“語言符號連結的不是事物的名稱,而是概念和音響形象,后者不是物質的聲音,純粹物理的東西,而是這聲音的心理印記,我們的感覺給我們證明的聲音形象”。[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01.實際上,索緒爾所認為的語言是一個具有概念(即所指)和音響形象(即能指)的符號系統。這個系統中的所有要素構成一個統一整體,他用棋盤和棋子來比喻語言系統與要素之間的關系。“下棋的狀態與語言的狀態相當。棋子的各自價值是由他們在棋盤上的位置決定的,同樣,在語言里,每項要素都由于其他各項要素對立才能有他的價值”。[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28.從索緒爾的符號系統以及價值體系中可以看出語言的本質是一個符號系統,各種元素在共時狀態下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其價值由他們在系統中的相互關系所決定。
(四)轉換生成語言學認為語言本質是天賦能力
如果說索緒爾語言學說的提出是語言學史上哥白尼式的革命,那么喬姆斯基轉換生成語法的提出,則是語言學史上又一次劃時代的革命即喬姆斯基革命。喬姆斯基的語言學說影響巨大,若要探討轉換生成語言學派的語言觀必需回到喬姆斯基的理論中去。
喬姆斯基雖然師從結構主義語言學家哈里斯,但后來他意識到無論是傳統語法還是一味對語言現象進行描寫的結構主義都不能很好地回答“語言是什么”這一問題,歸根結底是由于沒有真正了解語言的本質。喬姆斯基認為語言本質是一種天賦能力,兒童一出生就具有這種獨特的才能。這種才能是存在于人腦中的一種裝置,喬姆斯基稱之為“語言習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因此兒童可以用接觸到的有限語言材料生成無限的句子。
實際上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把語言看成人腦中的一種特殊機制或者是一種語言藍圖。因此生成語言學派中所說的語言并不是實際存在的句子,而是生成句子的裝置。從這個角度看當我們說學會一種語言時,實際上學會的是其背后的生成機制。
(五)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本質是認知活動
認知語言學對語言本質的認識完全不同于轉化生成語法。在喬姆斯基的轉換生成語言學派認為語言是一套自治的系統裝置。而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是一種認知活動,是人對客觀世界認知的結果。語言運用和理解的過程也是認知處理的過程。因此語言能力不是獨立于其他認知能力的一個自治的符號系統,而是人類整體認知能力的一部分,強調語言與認知的不可分割性。認知語言學者認為隱喻是一種思維方式,他們十分強調思維的隱喻性。實際上隱喻由認知而起,同時又是認知的結果。某種程度上講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的本質其實是一種認知活動。
四、語言的來源問題——柏拉圖之問
對語言知識來源的追問引導我們回到一個古老的認識論問題上,那就是“我們的知識從何而來”。關于這一問題的探討,最先起源于柏拉圖,因此在喬姆斯基的學說中,他把語言知識的來源之問稱為“柏拉圖問題”(Plato’s problem)。
以喬姆斯基的語言學思想為代表的生成語法及其相關理論對語言本質的思考是從對語言知識的“柏拉圖問題”的分析開始的。他們關心的是為什么兒童在與外部世界短暫而有限的接觸下卻能理解并造出他們以前從未聽過的句子。因此“語言知識從何而來”這一來源問題成了語言學中的“柏拉圖之問”。
(一)傳統語言學認為語言由上帝授予
早期的人類在面對他們無法做出合理解釋的種種自然之謎時,往往將其歸因于神靈的力量。面對語言如何獲得這一關于語言的起源問題,傳統語言學家同樣訴諸神靈,認為包括人在內的世間萬物都是某種神力的創造,而人的語言理所當然也是神力的恩賜。因而在大多數宗教中都存在某種神力授予人們語言或者創造語言的描述。比如《舊約·創世紀》中,上帝創造了人類祖先亞當和各種飛禽走獸,而后將這些動物帶到亞當面前由他命名,而古埃及人相信語言是由納布神創造等。
(二)結構主義認為語言源于社會
索緒爾首先認識到語言的復雜性,并做出了“語言”和“言語”的重要區分。他認為“語言是言語能力的社會產物,又是必要的慣例的匯總,這種慣例為社會群體所接受,使每個人能進行言語活動。”[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115.實際上,從中可以看出索緒爾從社會的角度觀察語言問題,認為語言來源于社會,把語言看成是社會的產物,是社會群體必須遵循的慣例集合。語言雖然潛伏于大腦中,但作為一套系統本身不會表現出來,它的完整性必須在一個社會群體中才能體現出來。因此社會成員不能獨自創造語言,也不能改變語言。
繼索緒爾之后,結構主義又一重要人物、美國描寫主義語言學派的代表——布龍菲爾德接受了行為主義心理學的觀點,認為語言習得是外部世界刺激反應的結果。行為主義心理學家斯金納曾用“習慣”來解釋語言的習得。他認為語言是人對外部環境刺激的反映的結果,是通過外部信號的反復刺激、不斷強化而建立起來的“習慣”。因此在行為主義者看來,語言來源于外部世界的刺激反應。
從某種程度上講行為主義者的刺激反應論這一說法,仍然沒有離開語言來源于社會這一基本觀點。
(三)轉換生成語言學認為語言源于天賦機制
喬姆斯基提出的語言習得機制中有著關于世界本質的認識尤其是語言本質的知識。因此生成語法學派認為兒童生來就有基本的語法關系和語法范疇知識,并且這種知識是普遍的。這些語法關系和語法范疇是存在于一切人類語言之中并為人類先天具有的知識。在人類的大腦中,存在著由生物遺傳和天賦決定的認知機制。因此生成語言學關于語言知識來源的理解認為它本身就內嵌于語言官能之中,是人類特有的一種天生的語言能力,并且是自足的系統,獨立于外部世界。
(四)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源于體驗與認知
認知語言學的哲學基礎是體驗哲學,它強調心智的體驗性、認知的無意識性以及思維的隱喻性。體驗主義認為知識并不全然來自人們對外部世界的被動感知,更多的是來源于人體與外部之間互動而產生的范疇和意象圖式。此外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與認知能力不可分割,因此若以此來解釋語言的來源,我們可以說語言是在人的體驗和認知的基礎上形成的。這就形成了認知語言學一個最重要的觀點:對現實的感知是認知的基礎,認知又是語言的基礎。[注]王寅.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8.唯物主義者認為客觀世界是認知形成的基礎,而認知語言學家則在此觀點之上進一步認為語言是對客觀認知的結果,是對現實進行概念化之后的一種表達。實際上認知語言學強調的是人與客觀世界之間的互動,這種概念化表達的重要來源正是人身處于客觀世界的自身體驗以及對外部環境的認知。
五、關于語言的使用問題——笛卡爾之問
20世紀60年代,喬姆斯基發表《笛卡兒語言學》,宣稱自己的轉換生成語法是17世紀至19世紀初的笛卡兒語言學在當代的繼續和發展。笛卡爾指出人類語言不屬于物質科學的范疇之內,尤其是 “語言使用的創造性方面”,其使用范圍無限并且不受刺激制約這一特性更是超出了機械論的物質概念所能夠解釋的范圍。所以,笛卡爾認為是否能對語言進行正常使用,是人類與其他動物或機器的真正區別。而喬姆斯基繼承笛卡爾關于語言使用的核心觀點,認為語言的使用依賴的是人的理性機能,是人腦的天賦機制對有限規則的無限利用。因此生成語言學首先假設了大腦中存在抽象概括的規則來支配語言的運用。喬姆斯基把語言知識的使用問題叫作“笛卡爾問題”。
(一)索緒爾認為語言的使用受社會約定俗成制約
索緒爾提到“言語行為的研究可以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以語言為對象,語言的本質是社會的,離開個人而獨立,這種研究純粹是心理的”,[注]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M].高名凱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37.索緒爾把言語行為分為語言和言語,強調語言是社會的,而言語是個人的。個人的語言使用體現在言語活動中,言語是語言的運用同時也是語言的具體表現。也就是說,言語是每個個體說出來的話語,它是具體的、變化的,而語言是一套完整的規則,由社會群體共同約定。這種具有社會性的語言,受到外部制約,這種制約同社會慣例一樣,是社會群體中一切成員都必須遵守的、約定俗稱的社會規約、制度。從一定程度上講,語言就像是一項社會契約,群體中的成員都必須遵循。因此語言使用訴諸言語,而使用過程中又受社會成員約定俗成的影響。
(二)生成語法認為語言使用依賴天賦能力及轉換規則
喬姆斯基認為若要對語言的使用問題進行有意義的探索必須得先解決語言知識的本質問題和語言知識的來源問題。這是因為他堅持認為,語言機能內在于心智大腦,對語言的研究也就是對心智的研究、對大腦結構的研究。
語言使用首先依賴于每個人天生具有的語言習得的內在能力,這種能力在聽到語言的時候被激活。生成語法在討論語言使用問題時,喬姆斯基試圖解釋語言的創造性,并在公式化、符號化的基礎上引入轉換規則對英語句法進行描寫。在擴充標準理論時期,喬姆斯基區分了語言能力和語言使用。存在人們頭腦中的語法知識是語言能力,而說話、寫文章等使用語言的具體行為是語言使用。很明顯語言使用一方面離不開人類的天賦機制即語言能力,另外一方面也離不開深層結構與表層結構轉換過程中的各種語言規則。
(三)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使用基于語言與客觀世界的象似
喬姆斯基的生成語法強調對語言形式的研究,不重視意義。而認知語言學的觀點認為,語言形式不能離開于意義而獨立存在。因此語言的使用必然首先服務于意義的表達,產生于意義交流的互動過程中。認知語言學強調認知方式在語義形成中的作用,同時也重視社會文化、百科知識對于語義理解的必要性。其次語言使用離不開語境,也就是說語言使用過程中并不局限于語言內部,更主要的是在于人與客觀世界的互動,強調的是使用者對世界理解的結果。 所以認知語言學認為語言不是一個自治的系統,它依賴于客觀現實、生理基礎、身體經驗、認知方式、知識結構等多種因素的共同作用。語言使用離不開語言表達與客觀世界以及認知世界之間的象似關系。
六、小 結
語言觀是語言學者對研究對象——語言的本質和規律的基本看法和根本觀點。語言學史上,語言理論的重大變革、語言學流派體系的建立以及完善都和語言觀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而關于語言是什么、從何而來、如何使用這三個基本問題是語言觀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語言學的歷時發展我們可以看到,每個不同時期的語言流派對于這幾個問題都有著各自的看法。因此,從語言學基本的三問出發可以讓我們更好地了解不同學派對語言學的基本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