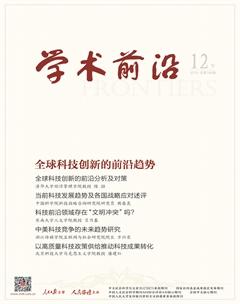對隱瞞境外存款犯罪應予以有效懲治
杜方正
【摘要】隱瞞境外存款罪是貪污賄賂犯罪體系中的一個非典型罪名,相對于其他貪污賄賂罪名,其法律適用頻率較低。還原立法原意,厘清隱瞞境外存款罪的法律適用,探尋其刑事政策本義及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關聯成為新時期反腐敗學術研究和司法實務界共同的期許。厘清隱瞞境外存款罪的法律適用障礙,首要應準確界定境外存款中的“存款”、關聯罪名等交錯之點。寬嚴相濟的反腐敗刑事政策賦予隱瞞境外存款罪延續與堅守的本質要義,并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建立與完善提供刑法根據。因此,提倡懲治隱瞞境外存款犯罪是實現刑法功能、刑事政策以及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等“刑事生態”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隱瞞境外存款罪? 刑事政策?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
【中圖分類號】D924?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19.24.018
近年來,伴隨著高壓反腐持續開展并形成強烈震懾效應,對腐敗犯罪案件的境外追逃追贓也屢見報端。外逃貪官之所以能夠從容出國,與其在案發前秘密將通過貪污、受賄等違法犯罪途徑獲取的錢款,轉移至所在國不無關系。這種非公開方式向國外轉移財產行為,事實上已經觸犯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395條之隱瞞境外存款罪。不同于其他貪污賄賂罪名,隱瞞境外存款罪法律適用頻率較低。目前有經媒體及人民法院裁判文書網公開可查的寥寥數件,且多為數罪并罰案件,單一罪名處罰情形尚未探尋精準案例。[1]近年來,伴隨著個別較高級別官員案涉此罪的影響,隱瞞境外存款犯罪重新引起學術界與司法實務界的關注。[2]刑法的目的是在追求一個沒有利益侵害的生活狀態,為達到此一目的,技術上的做法是對于造成利益侵害的行為的處罰。[3]事實上,法律適用較少并不意味著不存在“犯罪黑數”,也非否定該罪的法益侵害之事實。隱瞞境外存款犯罪既侵犯了國家廉政與廉潔制度之法益,也對國家外匯管理制度造成事實上侵害。
交錯之點:境外存款的法律界定
懲治隱瞞境外存款犯罪首要解決的是條款稀缺性導致的法律概念闡述問題。“境外存款”,在看似簡單的語詞背后卻掩藏著深深的釋義糾結。除《刑法》第102條提及“境外”一詞,《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多部法律法規也有所涉及,但均未給出準確詮釋。一般認為,既可將“境外”理解為國境外,亦可將其看作關境外。對于將其作為國境來理解,范圍要廣于關境外。于我國刑事司法理論與實踐而言,科學理解“境外”含義的難點主要在于對港澳臺地區所屬范疇的認定。根據港澳基本法等相關規定,除《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法》等法律外,包括《刑法》在內的絕大多數法律并未在港澳地區施行。但是,同時,《國家安全法》第40條要求港澳地區應當承擔維護國家安全的責任。至此,在立法層面上,“境外”一詞的區分已十分模糊。然而,即便將“境外”一詞理解為關境外,同樣顯得不甚嚴謹。一方面,《國家安全法》頒布時間較晚,同遇語焉不詳時,對其解釋應著眼于“新法優于舊法”原則,直擊立法者本意之考量。另一方面,應充分考慮港澳基本法的規定以及行政管理權暫未延至臺灣地區的事實。從犯罪事實查處以及立法原意探析,境外存款犯罪中的“境外”應當是指國外以及我國的港澳臺地區。
境外存款準確界定的第二個難點在于交錯識別同屬《刑法》第395條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因條款的特殊性,兩者存在一定關聯及罪名概念界定的必要。從資金來源來看,隱瞞境外存款中的“存款”不區分資金來源合法與否,即便屬于合法財產,一定行政職級范圍的國家工作人員也必須按照黨政干部個人申報事項等規定向單位及組織進行如實報告,其余人員也應按照《刑法》中相關規定對于境外存款情況進行申報。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則將“不能說明合法來源”資產作為犯罪的構成要件,其采用了擴大性解釋對其特殊主體相關行為進行犯罪認定。從立案數額來看,根據《關于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案件立案標準的規定(試行)》的相關規定,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與隱瞞境外存款罪立案數額標準數額一致,均為30萬元。伴隨著監察體制改革,中央紀委國家監委于2018年4月印發了關于《國家監察委員會管轄規定(試行)》,上述兩罪均被納入監察機關辦理案件罪名,但監察機關尚未就相關罪名更新發布有關立案標準。兩者的區別主要在于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規定,雖未達到相關立案標準數額,但其與正常收入來源資金差額部分依舊屬于違法所得,應被依法沒收。隱瞞境外存款犯罪則無相關規定及實務操作,只要相關存款來源合法,違反申報義務的境外存款并不在被科處沒收之行列。
境外存款中的“存款”之非法性除指向資金來源的非法,還包括轉移資金方式的非法性。轉移資金方式的非法性主要體現在近年來出逃貪官的實例中。依據我國外匯管理體制及具體制度,大額境外存款及資金轉移需要嚴格的審核及復雜的流程,將非自用或者投資資金轉移至境外不具有實際可能性。為實現非法目的,犯罪嫌疑人及被告人多通過地下錢莊“洗錢”、違規投資變現以及代為持股等非法手段進行資金轉移。非法途徑轉移的境外存款不僅違反了既定的申報義務,也極大地破壞了我國金融管理秩序和外匯管理體制。當然,我們也應看到,境外存款僅僅是非法手段向境外轉移資金的一種具體形式。準確地說,在金融產品創新視域之下,存款占資金來源比例較低是一種事實性法律存在。不動產、金融等均在資金構成中占據決定性支配性地位。由此可見,基于隱瞞境外存款罪的相關立法已經嚴重滯后于社會事實,應當對期貨、理財、基金進行擴大解釋,以期實現立法原意與犯罪預防目的的融合。
刑事政策之本義:反腐體系構建的內在需求
隱瞞境外存款罪的設立深具反腐體系構建的內在需求。反腐需求不僅是現時數年之劇烈司法表征與實質,更是由刑事政策至立法司法執法環節的躍然展現。刑事政策要求對反腐敗犯罪采取嚴厲刑事處罰同時,更在于從犯罪預防與刑事合規入手實現反腐敗的終極目的。對賄賂犯罪的“嚴而又厲”刑事政策,在立法設置上,嚴密法網和配置相對嚴厲的法定刑是題中應有之義。[4]隱瞞境外存款罪的設立恰恰體現了這一犯罪預防前置與嚴厲刑事政策并合的特征。將懲治隱瞞境外存款行為上升到刑事處罰高度無疑是一種“嚴厲”賄賂犯罪懲治刑事政策立法的表現。其所要保護的法益也絕非僅僅指向國家工作人員廉潔性。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在于對其非法財產的排斥與拒絕,而非對合法財產的“猜測”。不區分財產具體來源而要求對合法財產進行申報,其不僅是刑法強制力的體現,更是嚴厲賄賂刑事政策的內在要求。1997年《刑法》頒布前后,反腐敗犯罪面臨復雜且艱巨形勢,加之當時我國境外金融監管與合作能力的薄弱。出于對國家工作人員廉潔性的考量,設計了申報境外存款的刑事條款。對于違反申報義務的行為不僅可能給予行政處分,更為嚴厲的是需要承擔一定的刑事責任。這種條款設計既反向突出了當時反腐敗形勢的嚴峻性,也充分展示了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嚴厲刑事政策特征。
隱瞞境外存款犯罪并非一味地僅僅強調“嚴厲”,刑事政策中的“寬”也同時得以展現。不同于一般性罪名表述,隱瞞境外存款犯罪條款規定了兩類處理方式,一種是對于數額較大符合立案標準且隱瞞不報的,由司法機關給予刑事處罰。另一種則是基于《刑法》第395條第2款及相關司法解釋規定,對低于30萬元數額等情節較輕的,由其所在單位或者上級主管機關酌情給予行政處分。在《刑法》條款中直接規定給予行政處分立法方式,實際上突破了《刑法》主刑與附加刑的立法范例。隱瞞境外存款罪懲治之寬主要體現在行政處分的設定。刑事與非刑事處罰方法不僅對本人起到了良好的特殊預防目的,也對其所在單位人員及相關群體起到了良好的一般預防作用。目前,雖然尚未有全國性預防法,但各地多有制定地方性條例。立法的目的在于對國家工作人員不依法履行職責和不廉潔的行為進行預防和矯治,同時警示、教育其他國家工作人員,遏止和減少職務犯罪。包括隱瞞境外存款犯罪在內的貪污賄賂犯罪成為其重點預防與警示內容。警示與教育一些存在著和欲實施隱瞞不報境外存款行為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不僅是預防職務犯罪條例應有之義,也充分體現了寬嚴相濟中“寬”的刑事政策。
法律適用之應然:官員財產申報的刑法根據
國家工作人員所持有的合法財產也需要申報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應有之義。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反腐的一劑良藥、猛藥,是反腐的前提與基礎。完善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實現隱瞞境外存款犯罪預防的途徑之一。后者是前者境外存款部分法律適用的刑法根據,對于官員違反財產申報制度而未申報境外存款事項時,在達到一定犯罪構成要件時,必然會觸發隱瞞境外存款罪的啟動。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一種旨在構建廉潔政府而希冀官員審慎用權的制度措施,其意在通過對官員財產的準確掌握并適當范圍的公開使其無法隱蔽非法所得,進而拒絕貪腐。正是因為立意高遠,故而實施難度大且面臨阻力大,直至今日尚未完全建立。一些地區做了有益嘗試,如深圳市頒布的《深圳市領導干部財產申報的暫行規定》,明確要求領導干部要將本人及配偶等人的財產分七類狀況及時上報。
根據2017年頒布的《領導干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規定》(以下簡稱《規定》),雖然適用申報主體稍寬于2010年修訂前的規定,但并未改變主要針對國企中層及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基本主體特征,其遠窄于隱瞞境外存款罪的犯罪主體范疇。兩者在主體上的不同凸顯了對于占絕大多數的一般國家工作人員個人財產申報制度的欠缺與空白。此外,近年來出現的“小官巨貪”現象,身處關鍵崗位的低職級干部和享受待遇的部分國家工作人員并非不存在權力尋租的現象,其同樣具有財產申報的必要性與急迫性。兩者在申報內容上也多有不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涉及范圍更為寬廣,包括但不限于工資收入、勞務所得、房產、持有股票、基金和投資型保險、經商辦企業以及在國(境)外的存款和投資等情況,包含了境外存款申報中的相關內容。《規定》第11條增加了抽查核實的規定,隱瞞境外存款犯罪則無相應的核查機制。線索來源雖從理論上存在舉報、“以事立案”、其他機關移送等多種可能性,但事實上一般屬于并發性案件,多在查處其他職務犯罪案件中一并發現,并無預先發現機制與實際案例發生。官員財產申報抽查核實機制則可成為隱瞞境外存款罪立案與查處的突破口。
由于實踐性制度文件的欠缺,考察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內容也多建立在既有的學術基礎之上。境外存款是一種財產,或是官員自身所有,或是夫妻雙方共同所有,存款名義也存在差異可能性,但官員都具有對其的所有權,故境外存款的范疇要窄于官員財產本身,是典型的包含與被包含關系。實際上,境外存款罪的設立是最為嚴苛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一部分,這種嚴苛性不完全是基于金融秩序的考慮,更多地是出于對國家工作人員廉潔性的擔憂,防止發生貪腐贓款難追回。然而,一個走向腐敗犯罪深淵的人員,非但很難顧及這種法律與制度的擔憂而如實申報境外存款,相反還會變本加厲,意圖將本人擁有財產均變置于境外財產,以實現逃避法律懲處之目的。
此外,刑法教義學與刑事政策一脈相承,將兩者割裂并非明智之舉。將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中重要一環上升至刑法高度并不會侵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對于違反這一制度進行刑事處罰具有法理依據,并不存在“安全刑法”之虞。一方面,由于我國反腐敗立法未實行單行刑法立法例,但其所指涉的主要是國家工作人員。國家工作人員承擔著一定職責與擔當,故其理應承擔相應的責任。另一方面,國家工作人員的進行財產申報是一種內部行政行為,不具有可訴性,是一種明確規定作為方式的制度。當然,由于諸多因素掣肘,國家工作人員全面財產申報制度尚未完全建立。境外存款的申報作為一項刑事責任,成為推動這一項制度落位的切入點。
結語
懲治隱瞞境外存款罪核心在于對該罪構成要件的準確判定,難點在于如何區分刑罰與行政處分的界限。刑法對國家工作人員境外存款事項隱瞞施以重拳,卻鮮見主動發現之實例,究其原因,大抵可歸結為三方面。第一,刑事立法技術水平亟待提高。從犯罪構成要件來看,直接規定國家工作人員義務申報的職責與義務稍顯贅述,也不符合立法簡練之要髓。2010年個人報告事項制度出臺后,刑法歷次修正案對此未作任何修改。該條款本身也存在著語焉不詳的瑕疵。雖然該罪立案數額已有規定,但對于何為“情節較輕”卻未作任何解釋與說明。同時,其遺留的自由裁量空間與《刑法》第37條“犯罪情節輕微”的關系也未厘清。第二,犯罪的界限與競合的影響。基于該罪犯罪主體獲取存款來源的多元化考量,存在與貪污罪、賄賂罪及集資詐騙罪等多種經濟型與職務型犯罪的競合關系,也存在與同屬于一個條款的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之間的界限區分及犯罪競合問題。第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尚未完全建立。隱瞞境外存款罪是典型的故意犯罪,雖然刑法條文中涵蓋了報告的要求,但對于如何報告及報告主體卻未曾明確。只有一個清晰明了的犯罪構成要件和貼合反腐敗實際的立法原意再現,方才是懲治隱瞞境外存款犯罪“刑事生態”的必由之路。在嚴格依照刑法規定對于符合隱瞞境外存款罪構成要件的犯罪行為進行立案查處,既是司法機關的職責所在,也具備反腐敗刑事政策內在所需,同時也是建設廉潔政府的必然選擇。
注釋
[1]2004年,廣東新興縣原縣委書記張國權因受賄、隱瞞境外存款等罪名承擔刑事責任;2006年,上海市嘉定煙草專賣分局原局長張偉民因隱瞞境外存款、貪污等罪名承擔刑事責任;2013年,內蒙古自治區政府原副秘書長武志忠因貪污、隱瞞境外存款等罪名承擔刑事責任。
[2]安徽省原黨組成員、副省長周春雨將412余萬美元存放于境外銀行未按規定進行申報,并因隱瞞境外存款罪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與其他罪名數罪并罰。
[3]黃榮堅:《基礎刑法學》,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36頁。
[4]孫國祥:《賄賂犯罪的學說與案解》,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年,第67頁。
責 編∕張 曉
Punishing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Bank Deposits
Du Fangzheng
Abstract: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bank deposits is an atypical one in the criminal system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Compared with other crime names of corruption and bribery, it is rarely cited. Restoring the original legislative intention, clarifying its legal application, and exploring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the criminal policy behind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official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have become the common expectation of the anti-corruption academics and the judicial practitioners in the new era. To streamline the obstacles to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rovisions on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bank deposits, we should first accurately define the "deposits" and related crimes. The anti-corruption criminal policy of "tempering justice with mercy" gives an essential meaning to the continuation and persistence of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deposits and provides a criminal law basis to the establishment and improvement of the official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Hence, advocating punishing the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deposits is the only way to realize the "criminal ecology" consisting of functions of the criminal law, criminal policy and the official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
Keywords: crime of concealing overseas deposits, criminal policy, official property declaration syst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