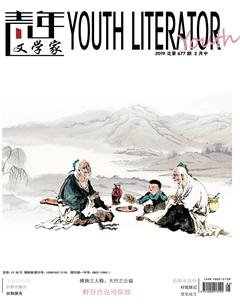不幸者、拯救者、反抗者
摘 要:70后“新一代頑主”作家石一楓,其作品中真正值得注意、帶有光芒的是女性形象,突出塑造了以陳金芳為代表的許多女性人物,呈現出她們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與男性、與生存環境以及與社會的關系。這些女性有的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飽嘗生活的艱辛,是生活的不幸者,有的一改從前小說中女性被男性拯救的形象,而成了男性的拯救者,有的則像陳金芳一樣成了為改變命運的不懈反抗者。這些女性身上承載了石一楓作為一位作家對現實的關注,對大時代里小人物命運的關切,以及深刻的歷史反思。
關鍵詞:不幸者;拯救者;反抗者;女性;歷史反思
作者簡介:高陽(1993-),女,滿族,遼寧義縣人,研究生學歷,沈陽師范大學文學院2016級中國現當代文學專業,研究方向為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5-0-02
以2013年為界,石一楓小說的后期和前期相比漸漸發生了變化,他不再囿于寫大院子弟的青春故事,而是打開了視野,并且將視角下移,關注底層小人物的生存狀態和命運,并嘗試尋找改變命運、反抗命運的可能性,他傾注筆墨較多的是底層女性。
一、底層生活的不幸者
從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女性解放成為了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主題,文學作品中開始關注女性的生存狀態、生命意義和價值,在石一楓的一些作品中,也將關注目光投給了這些底層生活中飽經生活磨難的不幸者。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坐在樓上的清源》中的清源、《芳華的內心戲》中的芳華。
兩部小說的女主人公分別是清源和芳華,都是身處最底層的普通女性,而使他們的命運發生改變、走向人生困境的都是強暴事件。清源來自一個邊遠小鎮,從小父母離異,父親再婚,她又意外致殘,只能坐在閣樓上觀看外面的世界,靠賣草糊為生。父親的定期探視是她內心最大的期盼。由于她自身長得漂亮,遭到鄰居老曹的覬覦,也吸引了外來大學生的關注。通過與大學生的接觸,她內心接受了大學生對她的示好,并且也對大學生心生愛意,可是卻遭到了老曹的強暴而懷孕,最后大學生卻不辭而別,命運的打擊一次又一次地落在這個柔弱的、不幸的女性身上。父親公開擇婿,在眾多鰥夫里為她挑選了一位老實本分的鞋匠。故事到這里就結束了,為讀者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間,孤寂、無助、失望的情緒將會充斥清源未來的生活、未來的命運,而她只能無奈地忍受,無力去改變,石一楓對這樣的女性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清源代表的是生活在邊遠鄉鎮中的底層女性,而芳華轉換了生存空間,代表著外來入城的底層女性,芳華與清源有相同的人生經歷,也在美好的年紀被人強暴,但她還生下了一個先天殘疾的孩子。石一楓在這里對芳華的苦難經歷只是輕描淡寫,著重表現的是她的內心戲。為了謀生,她在城市里開了一家小賣部,小賣部成了她觀察他人、觀察這座城市的窗口,一系列的心理描寫也于此展開。芳華喜歡在她的小賣部秘密地觀察男人,小說描寫了她對三個男人的觀察,一個是好丈夫形象,一個是完美情人形象,另一個是霸氣江湖中人形象。她在內心里分別想象了自己和他們的關系,幻想出各種各樣的愛情故事。但這一切只是虛擬,并非真實,真正與三個男人有情感關系的是一個女樂手,女樂手是別人口中的唾棄對象,卻讓芳華羨慕不已。她之所以只敢沉溺于與男性關系的幻想,是因為身為一個外來務工者,她對于這座城市沒有一種歸屬感,她想通過想象讓自己與這座城市建立聯系,融入這座城市之中。芳華代表的不只是底層女性,更是無數城市務工者的現實處境。在這里,石一楓又將我們引向了對城市“他者”的關注,對他們命運和遭際的思考。
二、男性的拯救者
同樣是從五四新文學運動開始,女性成為文學作品中被啟蒙的對象,而啟蒙者則一直由男性充當,男性一直作為女性的精神導師而引導著女性,像《傷逝》中的涓生和子君即是如此。在石一楓的許多小說里,女性一改原來被男性拯救的形象,成為了男性的拯救者,充滿了人性拯救的力量,這種力量使石一楓的小說散發著一種獨特的光芒。《紅旗下的果兒》里的張紅旗,《戀戀北京》中的姚睫以及小保姆,《我妹》中的小米,都是女性拯救者的形象。
在《我妹》這篇小說中,石一楓講述了渾渾噩噩、得過且過的楊麥重拾道德理想的故事,在這一過程中楊麥的妹妹小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小米這一人物在外形和性格上都有獨特之處,而且外形和性格形成了巨大反差,“她二十出頭,臉很小,顯得眼睛很大,棕黃色頭發極其短,幾乎接近男式的‘板寸了;右耳的耳廓上掛了一排不知是銀的還是鐵的金屬圈,鼻翼上還戴著鼻釘,穿著破洞牛仔服,帽衫上印著大骷髏,多袋褲也又舊又松垮,褲腳處都磨出毛邊來了。”這樣的外形呈現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社會女混混,不學無術,然而妹妹卻是一個熱愛生活、熱愛家庭、能做飯煲湯收拾房間的勤勞女孩兒,外表叛逆、內心卻溫暖。她最感人之處在于,自己本身是一個色盲患者,不適合從事新聞工作,可是她對于新聞始終有自己的理想追求,并為此而執著努力,不曾放棄。 楊麥與母親關系的調和、楊麥與妻子的結合都少不了小米的貢獻。
小米的出現點亮了楊麥原本庸俗、渾噩的生活,在小米潛移默化的影響和感染下,楊麥一步一步實現了精神覺醒,而這覺醒也是他經過自我理性思考的結果。
像陳福民所說“石一楓有一顆不忍之心,他筆下的女性盡管不是那么聲色俱厲,但是仍然保持著她們很獨特的品質。這種對自己的保持,最終成為一種拯救的力量,使男性獲得了正面的道德肯定。在這個地方,石一楓給掙扎在這個時代車輪重壓之下的所有人,開了一個童話式的精神后門。”[1]
三、命運的反抗者
石一楓后期的作品中體現了他深刻的反思精神,他通過刻畫像陳金芳、苗秀華等這樣生動鮮活的女性形象來切入當下的社會問題,反思社會,反思歷史,反思大環境對小人物命運的擠壓,也表現她們為改變命運的反抗精神。
在《世間已無陳金芳》中,石一楓通過陳金芳對命運的不屈抗爭,思考了個人命運與社會環境的關系。小說主要講述了陳金芳初中時從湖南農村老家來到北京,剛去學校上學就遭到了同學們的排斥與嘲笑,從一開始就成了這個城市中的“他者”。為了改變自己貧苦的命運,留在北京,在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下,她從擺地攤開始到后來的集資投資,不斷努力奮斗打拼,最終卻依然失敗入獄的故事,反映了底層普通小人物想要謀求發展和上升的艱辛。在她被警車帶走之前,她說了一句話,“我只是想活得有點人樣”,一個再簡單不過的想法,卻使作為一個底層青年的她卻付出了巨大的代價都沒能實現。不得不讓我們反思,在資本化的大時代,留給個人的機會多么狹窄,個人如何才能突破擠壓,改變命運,實現上升。
在《特別能戰斗》中,女主人公苗秀華的反抗精神更加明顯,在這個特別能戰斗的女性身上,承載了當今社會常見的“鬧”的因子,她身上包含了豐富的歷史記憶和時代內涵。“鬧”的反抗戰斗精神,既保留了文革特殊的歷史遺風,又帶上了新歷史時代“維權”的市民意識。而苗秀華的身份也發生了轉變,從維權變成專權,從民主斗士變成民主敵人,所以苗秀華這樣一位女性反抗者負載著深刻的歷史反思。
陳金芳和苗秀華的反抗雖然都失敗了,但他們卻給了我們質疑時代、抵抗絕望的勇氣和感召力。
結語:
石一楓的小說通過對不幸者、拯救者和反抗者等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來切入當下現實生活,在關注底層女性命運和生存狀態的同時,更揭示社會中存在的問題,將我們引向對社會和時代的總體性思考。
參考文獻:
[1]陳福民.石一楓小說創作:一踏糊涂里的光芒.文學評論[J].2011.11.07第00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