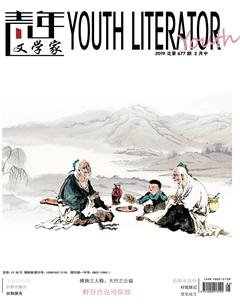“軟埋”的歷史,歷史的訴求
作者簡介:徐婭棋(1988.4-),女,朝鮮族,浙江杭州人,碩士在讀,華北科技學院助教,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國現當代文化與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5-0-02
這是方方根據朋友母親親身經歷而撰寫的一部小說。作者充分發揮想象力,將讀者帶入歷史現場旁觀著早已被時間“軟埋”的一幕幕慘狀。這些慘狀結痂于那些親歷者的身上,他們不愿提及當年,不愿從頭回憶,不想將傷口再次撕裂開來。整部小說,“軟埋”是核心詞,是疑云重重等待讀者解密的“大包袱”。丁子桃是主人公,以自己斷裂的前后兩段人生作為織針,用錐心之痛的記憶片段為讀者編織出了歷史大事件——土地改革背景下的家族及個體悲劇。
一、“雙線索并行,逆時間敘述”[1]
這部小說吸引人之處在于其特別的結構安排,一共十五章七十小節,每一節的標題都像一個“小包袱”,不斷提出疑問。小說并不是根據歷史的時間推移去記錄歷史事件,亦不是單純的倒序回憶般的講述。而是通過女主人公斷裂的命運:丁子桃和胡黛云講述著現實中的疑問與過去的親歷的事實。(如下圖)
以丁子桃的反常舉動以及丁子桃兒子青林偶然開始的關于母親親身經歷的探索作為現實線索,設置重重疑問;以丁子桃前半生地主之女和地主之兒媳身份在十八層地獄拾魂中的每一個階段回憶為歷史線索,做出一一解答。且現實線索按照時間線性正序,而歷史線索則根據黛云回憶逆向倒序,兩者相互交錯并相互呼應。“軟埋”于地下的歷史線索“鑲嵌”在現實線索之中,如破土一般一次次撞擊著地面,牽動著讀者的心,并最終相互結合:一是現實中的植物人丁子桃終于“蘇醒”與記憶中的黛云逃離十八層地獄“復活”相對應,二是植物人丁子桃短暫“蘇醒”后的“最終死去”則是照應了軟埋了全家的黛云,盡管最終從暗道中逃離而生,但活著的她已經是“死人一般”。黛云曾經逃跑的漆黑暗道與沉睡中的十八層地獄相呼應,表現出她當時極其恐懼、求死不得,生亦如死的撕裂心情。
二、如何看待這段歷史?
巧妙的結構呈現的是一個慘烈的故事,說它慘烈,莫過于黛云親自軟埋全家人這一段描寫:“此時的花園一派死寂,到處是坑,到處的坑邊都是堆著新土。這是陸家人自己為自己挖的坑,是他們自己為自己堆的土。他們挖完坑,堆好土,相互之間并無言語,不說再見,只是各自一仰脖,喝下了早已備好的砒霜,然后自己躺進坑里。……她(黛云)開始填土。她瘋狂地把土往坑下堆。”[2]通過這段描寫,讀者才終于明白丁子桃何以在丈夫吳醫生車禍現場看到滿地尸首時,不由地拼命喊出“我不要軟埋!”“經歷了這樣的夜晚,她想,你們以為我還是活著的嗎?”[3]是痛,是恐懼,更是精神的撕裂!小說中清晰地描繪出了黛云極其慘烈的遭遇以及地主家的慘絕人寰的經歷。讀者不禁會同情黛云母家和婆家為代表的地主家族。這樣的書香門第,善良商賈,卻在土改中受到了如此沖擊,分財分地還不夠,一個被批斗導致家破人亡,一個為保尊嚴決絕集體自殺。這一“消滅封建階級制度”的政策何以變得如此血腥與滅絕人性?且土改中合法化的公開掠奪,不僅是死了人,更消亡了不知多少傳統文化。那些傳統文化繼承者鄉紳階層的消亡,其遺留的書籍與精神也最終隨著大火而變為田地的肥料——痛之!惜之!土改政策最終成為了公開燒殺搶掠的借口,成為了公報私仇的機會,成為了人性丑惡嘴臉——不勞而獲的工具。讀者心中嘶喊著“不應該是這樣的!”
但是方方并沒有任由讀者的情緒一直這樣宣泄下去,小說亦站在他人角度,他人之口,訴說了很多無奈。第一點,情況復雜。小說中一位重情義的革命軍人劉晉源說:“矯枉必須過正。不然我們怎么能鎮得住他們?那時候情況多復雜呀!”[4]其部下馬老頭亦說:“以現在的眼光看,你們當然會覺得這也不對那也不對。可是當年的社會狀況又險惡又混亂,我們來川東前,這里幾乎所有縣城都被土匪攻占過。……他們成了攻方,殺了我們多少人?”[5]第二點,沒有經驗。劉晉源說:“這事也不能演習一遍在開始做。當年并沒有人出來分析,窮人為什么窮,哪些富人是好富人,哪些是壞富人。所有的一切,都是現學。而且打完仗剿完匪,殺心還沒有退盡,就覺得鎮壓是最簡單有效的方式。……你也看到那些大宅子了吧?富人有多富,你已經知道了。可是你并不知道窮人有多窮,沒飯吃沒衣穿的人,多的是!”[6]在土改中受益的陸三也說:“難道窮人家破人亡就不算什么,富人家破人亡就更慘痛”[7]讀罷,讀者心中應有判斷,就當時的復雜情況來看,土地改革、剿匪都是必須為之之事。
同一個歷史事件在貧苦農民、地主鄉紳、革命軍人……都有著不同的親身感受和看法,且站在其自身的角度也無不道理。正如陳思和所說“土改這場作為旨在結束封建土地所有制,改變農民自身命運的政治運動,在中國現代史上的意義是毋庸置疑的。”[8]但是在土改過程中,確實有一個干部沒有經過真正理論學習,他們“只是想利用革命運動和混亂局面為自己搶得一點利益”[9],當然也一定有一些知識分子干部,他們“希望按照政策文件,理性地來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10]
即真正的歷史是復雜細微的,每個人都是歷史車輪前進中的滾滾塵埃,每一粒塵埃都有其自身的情感糾葛。歷史的親歷者終究是站在自身的立場敘述“個人歷史”,由于缺乏時間的“距離感”,容易對于歷史事件做匆忙的判斷,尤其是涉及道義問題之時,更是如此。在漫漫歷史長河中,有無數不為道德所接受的事件,從歷史評價尺度出發,其關注點在于“是否”和“能否”的問題,“局限于實然的范圍和經驗可能性的領域,……必須借助于理性才能實現。”[11]而道德尺度則不然,“道德評價則僅僅囿于‘應否的問題,屬于應然的領域,它體現著價值預設。”[12]究竟是應該用歷史發展的眼光,還是道德體系去評價?作為文化學者,如何書寫歷史?
2016年11月22日,《牛津詞典》公布了年度英文詞匯“post-truth”(后真相),即相對于客觀事實,情感及個人信念對于民意影響更大。也就是說情緒的影響力超過事實本身。在閱讀中,遠離歷史的讀者更容易被作者的價值判斷所引導,從而形成強烈的情緒積累。但是《軟埋》的寫作,沒有讓讀者深深陷入“道德批判”的深淵,而是采用比較溫和客觀的不同敘述角度盡可能使讀者了解“真相”的各個層面,告訴讀者,無論是哪個時代,道德的義憤無法代替科學的選擇,雖然它常常是“青面獠牙”,我們當然不能將其“軟埋”,但是最終的發展均取決于歷史的訴求。
注釋:
[1]楊志蘭. 拒絕遺忘被時間“軟埋”的歷史——讀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J]. 雞西大學學報,2016,05:101.
[2]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18-119.
[3]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20.
[4]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10.
[5]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10.
[6]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111.
[7]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259-260.
[8]陳思和. 土改中的小說與小說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學話土改[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04:76.
[9]陳思和. 土改中的小說與小說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學話土改[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04:81.
[10]陳思和. 土改中的小說與小說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學話土改[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04:81.
[11]何中華. 論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超越[J].文史哲,2011,03:57.
[12]何中華. 論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超越[J].文史哲,2011,03:57.
參考文獻:
[1]方方.《軟埋》[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年.
[2]陳思和. 土改中的小說與小說中的土改——六十年文學話土改[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版),2010,04.
[3]何中華. 論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及其超越[J].文史哲,2011,03.
[4]楊志蘭. 拒絕遺忘被時間“軟埋”的歷史——讀方方的長篇小說《軟埋》[J]. 雞西大學學報,2016,05.
[5]陸麗霞. 時間軟埋下的記憶與忘卻——評方方的《軟埋》[J].長江叢刊,2016,13.
[6]楊功順. 如何看待歷史與道德的二律背反現象[J].北方論叢,20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