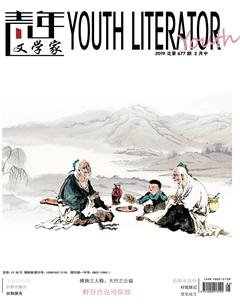淺論后世對李元陽詩歌的評點
摘 要:李元陽是明代云南著名的文學家,“楊門六學士”之一。作為少數民族文學家,李元陽的詩歌不僅展現了滇地的特殊地貌和民族風情,同時也受到當時中原主流文化的影響,呈現出雅正的特點。筆者以《滇南詩略》和《滇詩拾遺》為主,同時查找了與李元陽有交游的楊慎等人對其詩歌的評點。借此一窺李元陽詩歌在流傳過程中的影響,發掘其詩歌的獨特魅力,并探究散見于這些文獻中的評點的價值。
關鍵詞:李元陽;評點;詩歌;價值
作者簡介:熊倩(1994-),女,云南大理人,蘇州大學古代文學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明清詩文。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5--02
一
李元陽,字仁甫,號中谿,太和人(今大理),白族。明嘉靖丙戌進士,曾到很多地方任職過,后“以外艱去任,遂里居不復出”,晚年回到故鄉大理,與朋友游覽山水以寄托情志,在此期間創作了大量詩歌,尤以山水詩為盛。著有《中谿漫稿》、《艷雪臺詩》、《心性圖說》等,后刻為《中谿家傳匯稿十卷》。
李元陽作為明代云南知名文學家,在詩文方面頗有造詣。他的交游極為廣泛,其中既有達官貴人、地方名宦,也有文學名士、理學名家。在與他們的交往唱和過程中,同時代友人對李元陽的詩歌給予了評價,這些都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其詩歌的特征。其中,他與明代謫戍名士楊慎的交游,較引人矚目。據何喬遠《名山藏》載:“慎戍永昌三十五年,與昆明胡廷祿、晉寧唐錡、大理吳懋、李元陽、永昌張含相倡和,放浪湖山間”;楊慎居高峣水莊,“日與交游倡和”,“數與滇之鄉大夫游昆明池”等。與此同時,李元陽和張含、楊士云等本土文士之間亦有唱和,他們對其詩歌同樣給出了零星的評價。
作為云南本土文學家,李元陽積極促進滇南地區的文化學術發展。除卻上述提到的同時期友人的少量評點,后世對其詩歌的評點則更加豐富。其中主要集中于《叢書集成續編》中收錄的《滇南詩略》、《滇詩拾遺》、《中谿家傳匯稿》這些總集或別集中,方志和其他史料中亦有少量記載。其詩文創作數量豐富,題材內容集中在山水游記,也有少量的反映現實之作。李元陽的詩歌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染,也滲透著儒釋道的哲理,從人們對其詩歌的評點或詩文集序言中便可以看出。如《重刊中谿家傳匯稿序》中便有反映:“吾滇則有李中谿先生,先生之學歸本于復性,自明而誠。又頗究心釋典,以參儒理。在無識者,鮮不以為禪學矣。”
二
縱觀同時代的友人以及后世對李元陽詩歌的評點,不難發現,其中以云南地方詩歌總集《滇南詩略》,《滇詩拾遺》和別集《中谿家傳匯稿》中的評點為主。總的來看,這些評點呈現出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個特點是宗唐傾向。從詩歌內部來看,在當時詩壇上,明代詩學的整體風貌是“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這是以“前七子”為代表的文學流派所倡導的詩文創作觀。而中原的主流文學觀對李元陽等滇南詩人同樣產生了影響。這種傾向,從其詩歌內容和他人的評點中便可發現。如在《滇南詩略》中,《采蓮曲》:“五月六月蓮花開,溪邊女兒采蓮來。一葉小舟一竿竹,香風何處沾塵埃。羅裙綠映溪中水,新妝紅照蓮花蕊。玻璃界破一泓秋,螺寰倒浸青山嘴。曲聲驚起雙鴛鴦,相將飛過蓮花塘。”,其中,袁氏兄弟對該詩的評點指出:“風致生新,音節入古。”道出了李元陽詩歌在音節方面追求復古。又如《盤石歌》:“山根盤石陰松涼,日午攜琴坐夕陽。樵人一路下牛羊,吾亦收琴歸草堂。草堂月出穿林影,石瀨聲中發深省。故人今夜來不來,一天風露衣裳冷。”此詩借助清幽寂靜的環境,傳達出詩人恬適自得的心境。與孟浩然的《夜歸鹿門歌》頗有幾分神似,袁文典也評道:“古峭,近夜歸鹿門歌。”可見其宗唐的傾向。
除此而外,許多評點認為,李元陽詩歌在宗唐時更多表現為學杜,不論是詩風還是內容,都受到杜甫詩歌較大影響。在《同諸人渡榆水上雞足山大頂》中呈現了其詩學杜的特征,陳榮昌評為:“老當似少陵。”又《郊野雜賦二首》其二:“客識南村路,風輕白苧涼。山人能釀黍,野衲為焚香。云霽池光碧,煙濃樹色蒼。看來松竹外,別自有仙鄉。”陳榮昌點評為:“似杜”,仔細鑒賞品讀,確有其味。李元陽在宗唐時,雖然有自己的創新或生發,但仍有一些詩文落入窠臼,而這樣的評點對于我們認識李元陽的詩歌更具寶貴價值。
從外部來看,以袁氏兄弟為代表的這些評點者,在評價李元陽詩歌的時候,多次提到唐代詩人和詩作。其中,提到杜甫的次數最多,王、孟也時有提及。如,龔錫瑞(龔錫瑞,字輯五,又字信臣,號簪崖。乾隆拔貢。)評點李元陽道:“中溪先生五、七古體,其古樸處亦得少陵、道州遺意,特少開闔動蕩之致,故雖高潔似宛陵,奇杰如遺山,而終不脫宋元局面。”認為李氏的古體詩雖得杜甫、元結之詩味,但因氣勢不夠,所以最終只能達到宋元的水平,而未臻唐人境界。
其二,詩歌滲透儒釋道的佛老思想,極具性情。李元陽早年曾在外省做官,后因丁外艱而不復出。他在云南大理的自然山水中棲居,頤養性情,又因交游之廣泛,因而文學創作理念也受到當時友人的影響,呈現出超然物外的心境。據《重刊中谿家傳匯稿序》:“吾滇李中谿先生理學巨儒也,先生之學,以佛入,以儒出。……中年著《心性圖說》,亦頗參用佛旨。實則與周子太極圖說相為表里。當時羅念庵、王龍溪、唐荊川、楊升庵諸君子皆極推服。”其有一部分詩歌便如此,如《夢游仙》:“覺來啟戶再拜謝,星辰錯落霜空晴。”,詩歌描繪的是一種不同世俗生活的情景,增添了一絲神秘色彩。其中有評語:“公詩多此等語,至今太和人相傳公乃仙去,其蒼山麓葬處乃衣冠墓云”李元陽晚年潛心于研究理學,自創《心性圖說》,對“性”、“心”、“意”、“情”之間的關系有著獨到體悟,這種追求性情的超脫同樣能在詩歌中尋覓到。如,《別金陵泛舟懷南臺諸君子》:“秋月雁空度,寒江舟自閑。……何處是鐘山。”詩中如此評價:“詩本諸性情,即祧宋宗唐亦只依人門戶已耳。讀中谿詩應看其體,認性情長處。”順遂性情是一種處世態度,更滲透了一種通透的哲思。
在《滇詩拾遺》卷三開頭,陳榮昌指出:“……觀其文集,乃知中谿之講學合佛老而言之者也,其詩亦然。”從這些內部的評點觀察可知,李元陽詩歌的內容中確實滲透著儒釋道的思想。在《滇詩拾遺》中具體的詩作評點中,不乏此類評價。如《訪正山人寫經寺中》:“先生去官后歸,頗究心于佛書道藏。讀其詩自現。”再如《溪山逢道士》:“別廬近溪水,白石不藏魚。空把一釣竿,山下送居諸。道人忽見訪,貽我一編書。上篇闡黃蘊,下部演真如。拋竿迷出處,居然返太初。”詩歌描寫了奇特的一次遭遇,通過合理的想象,恰到好處地彰顯了自身的心志。詩評為:“公學兼老佛,于茲信矣。”
第三個特點是雅正,新警。雅正的特點表現在詩歌中,通常在于追求“溫柔敦厚”的詩風。這種特點,也可以引申理解為詩歌內容要展現內心情志。《尚書·堯典》中就已有闡發:“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這一詩學觀也在后世得到不斷闡發,此不贅述。
李元陽在給好友張含(張含,明代詩文家,字愈光,號禺山。云南保山人。)寫的《〈禹山癸卯詩〉序》中說:“仕以行志也,未必得志;詩以言志,而志卒信。”在李元陽看來,從政不一定能使自己的心志得以充分袒露,但詩歌卻可以彌補這樣的缺憾,盡情抒發胸懷和心境,達到卒章顯志的目的。據趙藩(1851—1927)(趙藩,白族作家,字樾村,一字介庵,別號瑗仙,晚號石禪老人。云南劍川人。)《重刊中谿家傳匯稿序》所言:“……先生所為詩文根抵磅礴,涂軌雅正。”不論是李元陽本人,亦或是后世的評價,都凸顯了其詩歌的雅正特點。詩人的這一特點是貫穿在其創作理念中,無形間影響其詩作的風格。
李元陽詩歌還有新警的特點。所謂“新”,是指遣詞造句,語詞新穎,給人耳目一新之感,具有新奇之意。劉勰《文心雕龍·知音》曰:“慷慨者逆聲而擊節,醞籍者見密而高蹈,浮慧者觀綺而躍心,愛奇者聞詭而驚聽。”劉勰認為,不同的鑒賞對象對于詩文所呈現的內容關注點不同,各有偏重。又如另一首詩作《感通寺》:“渺渺寒山獨自游,松青云白卻相留。數聲長笛知何處,吹落江門一派秋。”通過描寫幽寂山林和青松、白云,營造一種高蹈、超然物外的心緒。原詩后給出如下點評:“故雖高潔似宛陵,奇杰如遺山,而終不脫宋元局面。五七律多似北宋,其矜貴疑鋉處,竟非大歷以后語。此愚山所以言風流惟其李中谿也。”
李元陽詩歌的“警”,著重指詩句的深刻意蘊。偏重“警”的詩歌有《冬夜》:“漫漫冬夜長,熒熒孤燭光。……千古在須臾,安得不悲傷。”陳榮昌評曰:“望道未見,來日苦短,得古人短歌行之意。”在《郊野雜賦二首》其一的結句中:“但把一竿釣,藻深魚有無。”將富含哲思的深意蘊藏在平常的生活意趣中,陳榮昌:“結句耐人尋味。”
讀李元陽的詩文,字里行間散發著一股郁博的情志,使得他的詩文一方面能真切刻畫現實,另一方面又可以將精神世界的追求以律動的美感呈現。正應如此,后世對其詩歌的評點里往往能抓住這些特點,加以闡發出來。
三
后世對李元陽詩歌的有意識搜集和整理,對于文獻的保存和詩人作品的流傳都有重要意義。與此同時,其中還增加了很多的評點,這對于研究云南地方文學則尤顯寶貴。這些評點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其一,具有充實地方文獻史料與開拓研究視野的價值。通過這些評點,我們可以深入了解詩人李元陽的詩風,補充方志等文獻中所未收錄或缺乏的。同時,對于研究云南古代文學批評理論也有著補充的作用。《在滇南詩略》中,關于李元陽詩歌的評點多集中在云南本土文士,如袁氏兄弟、張辰照、龔錫瑞都對李元陽詩歌做出過評點,這從側面展現了云南學術文化的發展。其次,文獻中對于這些評點的記錄,對于人們深入細致地了解詩人李元陽的生平和創作風格大有裨益。通過對這些評點進行研究,更讓我們看到了云南本土詩人對漢詩文化的接受過程。這無形中拓寬了我們的研究視域。提供了觀察滇南邊疆文化發展的新角度
其二,無論是《滇南詩略》還是《滇詩拾遺》,附于李元陽詩歌后的評點為我們了解明代云南古代文化發展提供了參考,推動著云南本土文化和詩人影響力的擴散。我們在細致梳理以后發現,這些評價或多或少流露了評點者的詩學傾向。明代云南文學開始發展,這些評點者在受到中原主流文化熏陶的同時,也有對高原本土文化的獨特感悟。孫秋克先生認為:“抒寫熱愛鄉土的情懷和特立獨行的精神,表現對民生疾苦的關注和對社會現實的批判,在兼收并蓄中追求藝術的創新,是云南明代隱逸作家的共同創作傾向。”同理,評點者們對于傳統詩學觀既有吸收,也有自己的生發。這也再次啟示我們,研究滇南少數民族文化時,不僅要關注文學家及其文學文本,更應關注外部的一些史料。唯如此,方能拓寬視野,發掘云南本土文學的獨特性。
參考文獻:
[1]《新纂云南通志》,上海:上海書店,卷一百九十.
[2][清]袁文典,袁文揆,《滇南詩略》,《叢書集成續編》第150冊.
[3]袁枚著,顧學頡校點《隨園詩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
[4][清]陳榮昌,《滇詩拾遺》,《叢書集成續編》第151冊,上海:上海書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