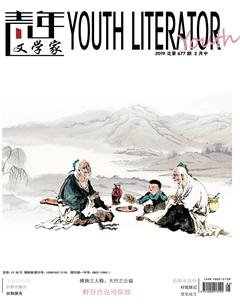雷蒙德·卡佛
摘 要:《大教堂》依舊延續了卡佛對于日常生活的關注與聚焦,將生活在社會底層的蕓蕓眾生對于生命的焦慮、彷徨、不安以及積極渴望得到的一點點的安靜的希冀進行書寫。學術界對于卡佛的寫作風格的界定是“極簡主義”,在我看來,這種寫作方式其實就是“畫框取景”與大量平庸生活的堆積罷了。就如同中國哲學中“大象無形,大音希聲”一個道理,在卡佛的世界中,生活才是推動世界發展的一切的力量與源泉,這些瑣碎的、多元的、去中心化的事件,其實都包含著最為樸素的真理。當然在這些拼貼與縫合的故事里,仿佛可以感受到卡佛對于生活的惴惴不安,畢竟寫作是不能脫離作家的個人生命經歷而存在的。
關鍵詞:社會底層;“極簡主義”;樸素;經歷
作者簡介:付以勒(1989.12-),男,同濟大學藝術設計專業碩士學位。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5--03
1.后現代主義視角下的雷蒙德·卡佛
雷蒙德·卡佛一共持續創作了25年,共出版了5部小說集,收錄了65篇短篇小說。而《大教堂》僅為其中一篇,同時也是相對而言比較有代表性的一篇。雷蒙德·卡佛身處20世紀末的美國的后工業時期,其作品也必然帶有后現代主義的印記,無論是二戰后迷茫一代的空虛,亦或是“機械復制時代”的乏味, 在卡佛身上都是有著濃厚的意味的,并且這種意味也深刻體現在了卡佛作品的人物身上。
從社會學角度而言,20世紀末的美國,社會生產從“人和物的競爭”轉變為“人和人的競爭”,生存不再是人類的期許,而生活才是人作為個體的全部特質,爭奪不再是為了活著,而是為了活得更好,二元斗爭下的弱者便成為了社會邊緣的畸形人物,而以鏡頭一般的語言去窺探這些與絕大多數人相似的底層人物成為了后現代藝術的主流,后現代藝術異化成了某種“吶喊”的聲音,這是由于西方后現代主義就是在物質方面的極大充裕與富足而精神方面極度空虛與無助的現代社會土壤中萌生和發展起來的。[1]英國文學雜志《格蘭塔》編輯布福德于1983年出版了一期美國小說特刊,他在引言中說道:“美國似乎出現了一種新型小說,這是一種怪異的和令人難以釋懷的小說。它不僅與英國當下的小說不同,和通常的美國小說也大相徑庭。”從外表上看這一類小說與現實主義有相似之處, 但其敘事手法與傳統的現實主義有著顯著的差異。評論家給這類小說貼上了各種各樣的標簽,如“新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高度寫實主義”、“照相現實主義”等等,而布福德則稱它為“骯臟現實主義”。[2]這一類小說的共同點就在于失去了小說相對虛構的部分,而決絕的將社會最為骯臟的一面解剖成碎片化的人物特征。這是一種去中心化的寫作手法, 沒有對立的人物,沒有高潮迭起的情節,只有平鋪直敘的語言,甚至于,情節本身都是相互斷裂的幾個遠鏡頭而已。
縱觀卡佛《大教堂》里的“我”,《肥》不斷提到的飯店招待員,還是《嚴肅的談話》中的男主人公,這些人物卑微到甚至在小說中連名字都被省 略,所有的敘事場景也往往被局限在一個狹小并且壓抑的空間中,因而人的落魄被進一步書寫。卡佛與同時代的小說家相比,他所展現的生活,更能以一種客觀、冷靜、從容的角度進行抒寫,這種寫作的方式,并不是拋棄情感,而是將澎湃飽滿的感情降至冰點,讓理性之花升華,這是一種“零度的寫作”。這種寫作方式摒棄了對于故事結局的執念,或者說這種客觀的書寫就如同科學實驗一般,實驗過程和公式推導遠比實驗結果更為重要,因為往往實驗結果僅僅是概率論描述的某種不可捉摸的數據呈現罷了,而過程的可重復性才是實驗本身想要獲得的最終目的。這種后現代主義的小說寫法,是將所有作者的想象力刪除,而僅僅表述冰冷世界所謂的“真實”,這樣的作品絕大多數充滿了悲觀主義的情緒。去裝飾化后的極簡主義,或者說去修辭后的寫作,呈現的往往是被解構后的廢墟,悲傷和壓抑將會無處不在,這一點,卡佛在創作中也無法避免。例如《憤怒的季節》,荒誕的關系:姐姐懷孕了;場面的失控:“他”只能殺了“她”,留下的只有無盡的唏噓和揮之不去的哀傷,又比如《請你安靜些,好嗎?》中的主人公,一開始的失業,酗酒,破產,妻離子散,友人背 棄,墜入人生之谷底,看似晚年文學聲名漸高,卻罹患肺癌,五十歲英年早逝的無奈。卡佛的大多數作品往往都致力于描繪20世紀末美國的藍領生活,是寫失敗者的失敗,酒鬼的酗酒,生活的變質和走投無路的絕望。然而《大教堂》卻成為卡佛眾多的作品中的異類,作品在一種完全被碎片化的單一取景的表述中逐漸獲得了重生,就如同在《平克弗洛伊德之墻》電影的結局中,被推倒后的墻的背后是天真無邪的孩童,小說本身重構了某種人文關懷,這種關懷哪怕連作者本人也許在書寫過程中也未曾預料到。這也是為何,卡佛的所有作品都采用了相似的人物背景,相似的文本空間,卻只有《大教堂》塑造的“我”,讀者能夠看出文本中人性的善意,無序的文本自身卻有序的引導了人們打開自我封閉的出口,讓人與人的交流成為拯救與重生的力量,一個沒有結局的劇 本,卻能以故事的每一個斷點或者說是“分鏡”給人以溫暖,這也是小說受到讀者追捧的原因所在。正如卡佛自己對《大教堂》的評價:“仿佛已耗盡,卻又收拾起勇氣。”
2.雙重敘事下的悖論和反省
雷蒙德·卡佛的短篇小說,在敘事上,極具后現代主義,所有具有裝飾性的詞匯或者言語在卡佛的小說中是不可見的。情節本身的推動來源于雙重敘事所產生的悖論,而對于故事背景的敘述被大量刪除,這可以認為卡佛在故意制造“距離”與“被卡住”的感覺。[3]對于悖論本身的質疑是解答悖論的途徑,讀者的困惑使得簡單敘事變得有張力,卡佛對于確定性的刪除,人為制造了閱讀上的障礙,因此隱喻成為了卡佛書寫小說的主要工具。
《大教堂》的故事情節敘事十分簡單,主要人物也就是三個人,妻子、“我”、盲人,但僅僅是三個人物的書寫卻同時具有雙重敘事性所產生的對 立,我和妻子這兩條或明或暗的線索鋪陳,產生了悖論所賦予的現代主義美 感。盲人是妻子以前的雇主和朋友,他的造訪引出了這個故事。小說的情節依舊平淡如水,我對盲人的“刻板印象”依舊映射出現實社會中的偏見與固執,從妻子與“我”的對話中,仿佛可以體會到這對夫妻面對生活中,已經漸漸失去溫度的愛情,對于他們彼此,這份感情更像是依賴和習慣。但是相反,“盲人”在小說中卻成為全知全能的人,他雖然身為社會的邊緣人士,但是不能阻礙他用另外的“眼光”去觀看這個世界,他擁有很多的朋友,這一點和“我”形成了強烈的對比,而“我”卻仍安于現狀,不做任何的改變,這樣的寫作策略也隱含著作者對于個體生命、社會,乃至國家的某種憂思——堅持著某種固有的方式去考慮問題,勢必會形成定向的思維模式,進而導致一個永遠無法逃離的“二元論迷宮”,越討厭就越發憎惡,越發的要成為這樣的人。其實相對于“我”而言,妻子是一個相對勇敢的人,她的生命歷程中充滿了抗爭的精神,她本來和自己青梅竹馬的軍官戀人結婚,其實過上了很多人羨慕的生活,但是長久的離散的生活方式,并不能讓她覺得生活的美好,就在這樣的情況下,她毅然地選擇了“我”一起生活,離開了應許之地,這樣的選擇明顯是具有非常強烈的主體意識的,但是妻子的行為在閱讀者看來,其實就是一個現實版的“娜拉”走出去了一個家庭,進入另外一個家庭的窘迫。文中的女性形象“妻子”,無論是內化的身體(精神,性格)還是外化的身體(衣著,利益)都是在一個完全封閉的空間中進行[4],可見,女性要在這個社會中取得獨立的人格、美滿的婚姻,依舊離不開男性的參與,一切脫離了男性參與、支持的女性權利運動,必將會走向失敗或徘徊。
悖論的產生在于妻子穿著性感睡衣在盲人身邊睡著后,是何種原因“我”會拖著不適的身體尋找紙和筆,這是有違邏輯的銜接,卻在全文起到了轉折作用,逆轉了“我”和盲人之間的距離,然而這種銜接卻毫無理由和原因。顯然,作為丈夫的“我”對于妻子的身份認知是自卑的,甚至于認為自己的妻子哪怕不是僅僅屬于自己,也是無可奈何的事情,這是一種極度不自信的表現。參考卡佛的其他作品,煙酒和電視往往是卡佛展現悖論的重要工具,在可觸及的放松迷醉和電視觀賞的遲滯之中,有些更為復雜的感受突然變得清晰。電視和人物觀看電視的場景其實有著特殊的藝術目的和指涉意義[5],社會底層人物往往和電視機的接觸時間遠遠大于上層社會人群,這是一種害怕與外界接觸的抵觸情緒產生的自卑感,然而卻強烈地希望通過電視這道狹窄的窗口來了解自己所忌憚又期許的現實世界。實際上對于溝通本身而言“我”是排斥的,但內心深處卻希望與盲人獲得溝通。也許是酒精和大麻的刺激,或者是內心的妒忌,甚至可能是希望展示自己了解盲人所不能夠了解的電視中教堂的造型這一些許的優越感,無論出于何種原由,這種類似于歇斯底里的溝通,在這個因為各種莫名因素的堆砌下發生了。
凝視和溝通是回望自身的一種方式,回歸本我,對個人生存狀態的質疑,才讓這些看似冷硬的文字具有社會關懷。“我”在小說中,是一個頹廢的個體,是一個在時代洪流中,被遺忘的個體。也正是因為“在場的缺席”,我對一切都抱著“無所謂”的態度,質疑一切,同時也否定一切。但是伴隨著“盲人”的來訪,在幫助他人的過程中,漸漸地找到了失去的主體,感知到了真正的“自由”。卡佛截取了普通人生活中十分平凡的畫面,以小說的鏡像語言, 展現出了人與人之間最為彌足珍貴的情感。
在這部小說中,“盲人”與妻子是關系非常親密的朋友,他們都愿意為彼此付出時間,去傾聽與理解對方,“我”對于這樣的行為,顯然是非常不理解的,在小說中卡佛不厭其煩的將這樣的段落盡量的詳盡化,這樣的寫作模式更加突出了“我”的不厭其煩,原因也非常簡單,因為“我”不想和一個“盲人”成為朋友,他會讓我投入更多的時間與經歷,而不確定有“結果”,這是現實中很多人都會有的思考,也正是因為如此,才會行成“刻板印象”,因為這個有色眼鏡,我們看不到實物本身的顏色,造就了一種隔離與誤解。而與 “我”的情況相反,妻子因為做過盲人的雇工工作,妻子幫助盲人理解與“看到”世界,也是因為有過這樣的經歷,他們能夠理解彼此,可見,打破“刻板印象”的重要方式就是去融入與理解,進入對方的文化系統去感知、體會,正如這部小說的結尾,“我”閉上了眼睛,去感知一個盲人的世界。同時,還帶上了“我”的朋友。個體生命關懷伴隨著生命的連接,徹底的走出了孤立無 援,走向了聯合。
3.《大教堂》的空間指涉
空間最初是作為物理學概念存在的,工業革命和文藝復興帶來的社會變革使得布爾喬亞式的思維模式迅速崛起并逐漸成為主流,這種社會主流觀念的改變導致了社會實踐和生存體驗的改變,菲利普·韋格納(Phillip E. Wegner)指出:當代西方“正在出現的跨學科格局正在把中心放到‘空間、‘場所和‘文化地理學的問題上,從以前對時間和歷史、社會和社會關系的重視,轉向對空間的青睞”。
妻子作為“不是公然帶有情欲加以注視的對象”[6],卻在我的懷疑和猜忌下,構建了我和盲人之間的某種聯系,這種自卑者斗爭性的聯系,具有某種社會反思情緒,然而這種聯系是需要契機和過程的,更需要一個合適的空間或者說場所來承載這種嬗變。如果有人硬拉他走上坡道直到拉出洞穴見到外面的陽光,當他來到陽光下時,會覺得眼前金星亂蹦,以致無法看見任何被稱為真實的東西。[7]“大教堂”對于普通人意味著什么,它對于一個無宗教的人來說只是一個建筑物;對于一個基督教徒來說,是一個神圣的宗教場所;對一個盲人而言,它卻只能是一個想象,一個不可解釋的符號,它是一個完全被建構的, 而且不能夠觸摸到的未知存在(因為這么巨大空間的東西對于盲人而言感知太難了),對于盲人,大教堂成為了不可感知之物,當然,盲人可以變化途徑去感知,就是通過繪畫,這是也“我”所做的,我通過與盲人的一起作畫,讓他感知到了從未感知的實物,同時,我閉上眼睛作畫,也感受到了我從未感受到的自由,這種“共生式”的感覺,映射出作者渴望突破社會中種種巴別塔式的藩籬的愿望。“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個解放與自由之地,它的外表代表著一種宗教意義上的美,它的內核是心靈的詩意的棲居,“大教堂”對于“我”和盲人的關系,猶如妻子與盲人間一盒盒“磁帶”,傳遞著互相交流的信息。從文本的另外一個層面,卡佛也在傳遞,對于不同個體,獲得通融式的交流,每個個體都有差異性的方式存在。“大教堂”隱喻空間,它包含著復雜的情感肌理,代表著圓融和理解,在這個空間中,權利失去了存在的意義,取而代之的是理解、包容、寬恕的宗教式的情感。這應該也是作者的期許,他渴望人與人之間,消除種族、異質、性別、代際的鴻溝,實現情感的交流,這一刻的“大教堂”的空間屬性或許異化成了福柯筆下的“異托邦”。
卡佛作為一個當代作家,他經歷了美國最為動蕩發展的半個世紀,在此期間,二戰勝利、美蘇爭霸、越戰、迷惘的一代,在這些歷史的縫隙中成長的卡佛,以文學小說的形式,不斷的窺視生活的真諦。在《大教堂》中,關于情感的敘述,是緩慢又從容的,“我”對于妻子與盲人之間的感情在剛開始是表示懷疑的,因為我不知道他們發生了什么,但是情感卻如此真摯甚至于有這些許曖昧。小說中,“我”對于妻子的情感歷程仍然是以第一人稱敘事表述的,還是站著主觀的層面去表達,因此,“我”其實并不了解她,只知道結果,并不知道她為何去選擇。盲人雇主則不同,在他和“妻子”共處期間,他所知道的資訊都是來源于“妻子”,因此,這樣的信息傳遞的過程中,還包含著情緒感情的傳遞。盲人同樣也表現出了傾聽者的素質,以“心靈之窗”去幫助“妻子”解決一些她棘手的情感問題,基于這種高親密度的情感信任,他們成為了摯友,并且時間并沒有成為他們的隔閡,在各自重新組建家庭后,他們仍然保持著“情誼”,這種情誼是超越性別、族裔的,認同的實質是通過他人或社會周邊環境對自我身份的尋找和確認,包含了價值、文化和信念的認同。在跨文化交際中,游走于不同文化之間并不是一件輕松的事情。特別是面對強大主流文化的邊緣身份,如何獲得認同是一件困難的事。但是,“妻子”和盲人卻找到了認同,簽訂了心靈的契約。消費社會中,伴隨一切事物的商品化,情感已經變得十分奢侈,雖然盲人和“妻子”之間的感情,也是“消費”的衍生品,但是卻是如此的珍貴。
在《大教堂》的文本空間中,對于妻子、“我”、盲人的描述共同指涉了社會邊緣人物的生存現狀,邊緣化的身份認知,實際上卻是社會中每一個平凡的人的自我認知,這種卑微的認知導致了原初性的自卑情緒和對外部場域的抵抗情緒,所以在每個人剛開始與彼此的接觸中,都是帶有著抵觸心理,相對于卡佛其他作品中的強調孤獨感,這里的“我”卻更多地強調平庸和碌碌無為。也許這樣的我也是孤獨的,但孤獨絕對不是“我”的一切,或者說和我一樣“孤獨”的人是現代社會的多數,因為就和多數普通人一樣,“我”是擁有家庭的,“我”也是或多或少有工作有收入的社會群體中的一部分,而“我”的妻子和盲人,更不可以看作是一個簡單描述孤獨感的人物形象。正因為這三個過著平庸的生活的人,而不是孤立無助的三個人,才有合理的邏輯和機會讓三者在文本中處于同一空間中即盲人的拜訪。“大教堂”在文本中既是電視屏幕中具象的存在,同時也是某種符號化的象征,在卡佛看來,這個世界也如同是大教堂一般,是空間化的,可以容納不同的平庸的個體和平凡的生命,偶發的同一屋檐下的交流,使得脫去偽裝后的偶然的個體成為命運的共同體,而社會本身或許也就是由這些共同體共存下的總體而已,借用導演李安的話——其實,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大教堂。而《大教堂》的溫暖何嘗不是來自于我們對于自己的平庸生活的釋懷。
參考文獻:
[1]王婧,傅亮. 論物質的設計,精神的設計[J]. 藝術與設計理論,2018,(5).
[2]吳珊. 淺析雷蒙德_卡佛的小說的寫作手法[J]. 時代文學,2011,(12).
[3]陶斯明.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的悖論藝術研究[D].
[4]金明. 身體·記憶·認同——女性主義視閾下多重主體的重塑與自我命名[J]. 文藝評
論,2017,(02)
[5]王中強. 雷蒙德·卡佛短篇小說中的“電視意象”研究[J]. 外國文學研究,2013,(03)
[6]Brooks, Peter: Body Work: 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7(3)
[7][古希臘] 柏拉圖著. 《理想國》. 郭斌和,張竹明譯. 商務印書館,1986.08,第七卷
[8]方漢文. 后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 上海:三聯書店,2000: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