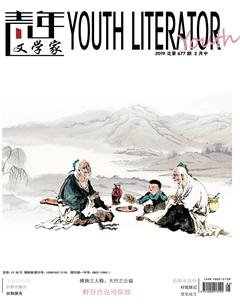《遠山淡影》的女性主義敘事學淺析
作者簡介:吳雙(1994.2-),漢,女,黑龍江綏化人,哈爾濱師范大學文學院2017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為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5--01
《遠山淡影》作為石黑一雄的長篇小說,全書以女性為主要人物,描寫了一位日本女人悅子借“自己的朋友”佐知子隱喻自己,回憶自己的移民到美國之前的經歷。本文擬以女性主義敘事學角度對《遠山淡影》進行解讀。
一、《遠山淡影》的敘述視角
視角是敘述者在敘述時所采用的觀察故事世界的角度。小說從女主人公“我”的視角展開,向讀者講述故事。小說中,主人公悅子在暮年時期通過與二女兒的聊天中開始回憶自己在日本時期的朋友“佐知子”發生的故事,來反思自己逃離日本的對錯。
本書以個人敘述聲音所展開,但聚焦人物卻是“佐知子”。主人公悅子在敘述中將自身的經歷投射到另一個人佐知子的身上,轉而將再婚不久的日本傳統女性時期的自己當做真正的自我,與佐知子對話。在回憶中,以他人身份來看待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既是一種逃避,也是掙扎的表現。
在小說中,故事分成了兩個部分,真實世界中的我和女兒景子的故事,以及回憶中的佐知子與其女兒萬里子的故事。老年的悅子,憑借自己的回憶去衡量自己當時所做的對與錯。對于當時傳統的日本婦女悅子來說,佐知子的選擇無疑是正確的,最初悅子將自我的獨立性壓抑在主婦的身份之下,得不到女性應得的待遇;戰爭之后的佐知子,拒絕了在日本的一切可能,而卻選擇相信一個酒鬼期待著同他去美國。盡管女兒顯示出極度缺乏安全感的樣子,但在佐知子的眼睛里卻依然她覺得美國更適合女孩子成長。在這種觀點背后,是由于戰爭給日本女性帶來的巨大的創傷,導致女性寧愿犧牲親人的幸福也迫切希望逃離當下的意愿,佐知子帶著萬里子離開了日本。但是當我們隨著悅子的講述明白萬里子就是景子的時候,也就知道了景子早在故事的開始就自殺了。在悅子與二女兒妮基回憶的時候說:”可是你瞧,妮基,我一開始就知道。我已開始就知道她在這里不會幸福的。可我還是決定把她帶來。”這種前后的矛盾,正展現出,當代女性為自由所作出的犧牲是巨大的,但又為其意義而感到疑惑。
悅子通過自己的敘述視角,不僅將悅子與佐知子進行比較,也在將萬里子、景子,以及妮基做了比較。悅子離開日本的結果是景子的自殺,以及妮基成為了區別于自由女性。但在書中后半段,妮基未婚同居,她的話語中表露出她認為結婚和家庭主婦是沒有意義的。但悅子卻說“可說到底,妮基,沒什么別的了。”在書中,除了與大衛同居之外,并沒有提到妮基的其他生活,甚至在悅子問起她的打算時顯得很生氣。可是無論是悅子或者是妮基爭取到自己的作為人的自由選擇性之后來說,她們卻又迷失在自己的意義中。
二、《遠山淡影》的性別主體
女性主義批評的一個基本論點是:成為凝視對象是受壓迫的標志。
在悅子的敘述中,首先成為“聚焦者”的是佐知子。佐知子在男性的壓迫下度過了前半生。以至后期即使在藤原太太的店里打工的時候,佐知子也沒有想過在日本安靜順從的生活下去,她在尋找一個不會壓抑自我的地方,為此她和弗蘭克去了小旅館。她不僅做了,還認為這樣弗蘭克一定會帶她去美國的,她可以開始新的人生了,可以給萬里子自由的生活。盡管她成功的離開了日本,但隨著景子的死亡,悅子開始懷疑自己決定的正確性。這種反思并不僅僅屬于悅子一個人,而是所有的女性。
萬里子是第二個“聚焦者”。萬里子的童年是慘淡的,被所有人忽略,佐知子一心要把萬里子帶出國,讓她成為自由的新女性。但是她卻忽略了作為一個母親所應盡到的責任。佐知子不僅沒有履行自己的承諾,而且在唯一能夠讓女兒感到開心的游玩里,選擇將女兒得到的籃子以及小貓一同遺棄在河里,殺死了女兒的天真和對母親的信任。當他們要出發去美國的前一天,萬里子拒絕,但佐知子保證說:“你要是不喜歡那里,我們隨時可以回來。”這種保證當景子在英國自殺的時候,恰恰變成了嘲諷。
妮基是第三個“聚焦者”,在全書人物中,無論是在名字還是生活上,妮基是最接近于新女性的。妮基的名字是悅子和丈夫妥協的結果,悅子想要一個英文的名字,擺脫過去,但她的丈夫正相反。妮基是東西方的產物,她的存在是具有代表性的,這體現在妮基對人生的態度上;不婚、同居、無業、沒有追求。妮基看似脫離了男性的壓制,但被排斥在社會之外,她無法找到自我。
三、結語
石黑一雄在書中所寫的女性形象,敘述著女性追求自由的過程。盡管書中并沒有大量的描寫男性人物,但它卻籠罩著整部書的構成,悅子沒有權利為小女兒取名字,為了出國不得不和酗酒的弗蘭克在一起,景子在家里的不受重視。這些所有的背后都有著男性的影子。本書的意義在于,通過悅子在年老時期的反思,向我們展示究竟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獲得女性自由的道路,具體的進程絕不會像書中人物一樣,但真正如何取得女性的平等地位,石黑一雄與我們女性一樣,都在摸索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