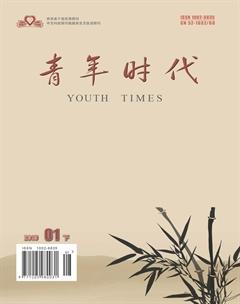先秦至隋唐儒學道德中的感恩思想概述
葛倩 王勇
摘 要:感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作為中華文化主導者的儒家富含豐富的感恩思想。文章從先秦時期儒學思想的興起到漢儒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戰(zhàn),失去封建正統(tǒng)地位這一段歷史時期儒學道德中的感恩思想,旨在回到中國傳統(tǒng)儒學的原點汲取感恩思想,為今天在中國弘揚感恩文化找到歷史的根基,傳承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讓古代感恩思想在當代煥發(fā)新的生機與活力,推進中國傳統(tǒng)文化實現(xiàn)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化、創(chuàng)新性發(fā)展,不斷鑄就中華文化新輝煌,努力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關(guān)鍵詞:傳統(tǒng)儒家;道德;感恩;歷史演進
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要求:“深入挖掘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蘊含的思想觀念、人文精神、道德規(guī)范,結(jié)合時代要求繼承創(chuàng)新,讓中華文化展現(xiàn)出永久魅力和時代風采”。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時,指出,“中華文化源遠流長,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層的精神追求,代表著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fā)展壯大提供了豐厚滋養(yǎng)。中華傳統(tǒng)美德是中華文化精髓,蘊含著豐富的思想道德資源。[1]”
感恩是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美德,表現(xiàn)在忠孝節(jié)義等道德規(guī)范中[2] (p.79-80)。作為中華文化主導者的儒家推崇的“仁義禮智信”五常就是感恩思想的重要體現(xiàn)。傳統(tǒng)儒家道德初始于殷周時期,鼎盛在西漢時期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到東漢時期逐漸衰落。
一、以“仁”為核心的儒學感恩思想嶄露頭角
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我國儒家思想產(chǎn)生與初步發(fā)展時期,作為百家爭鳴之一的儒家,以仁、義為最高的道德理想,成為先秦時期最有影響的學派之一。儒家學派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言:“殺身成仁”,亞圣孟子講“舍生取義”,孔子把“仁”作為人的最高道德原則、道德標準和道德境界,形成以“仁”為核心的倫理思想結(jié)構(gòu),包括孝、悌、忠、恕、禮、知、勇、恭、寬、信、敏、惠等內(nèi)容組成的整體的道德規(guī)范,這些道德規(guī)范無不體現(xiàn)出感恩的思想。在這套感恩的道德規(guī)范體系中,孔子把孝、悌作為人之本,視孝悌為基本的感恩道德品質(zhì),在《論語.學而》中孔子說,“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孝敬父母要做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身體發(fā)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于后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可以看出儒家文化認為從愛惜身體到揚名天下都是為了感恩父母。除“孝”的這種本義外,先秦時期的“孝”之思想還推延至尊敬老師,所謂:“一日為師,終身為父”,將老師的恩情比同父母,《荀子.禮論》:“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師,是利之三本也。”把教師納入了天、地、君、親的行列。孟子從性善論的基礎(chǔ)上推而廣之,衍生出大愛,“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3](p.111)”,將孝觀念輻射至“仁”,要求人們博愛眾人,子曰:“仁者,己欲立而先立人,己欲達而達人[4](p.850),強調(diào)推己及人,學會考慮他人,感念他人對自己的恩惠。孟子曰:“君子所以異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感恩的對象進一步擴大,強調(diào)施恩方和受恩方的平等互愛,即使在對立的階級關(guān)系中,孟子主張“民為貴”、“君為輕”,過分突出小農(nóng)利益,儒學不但沒有得到當時統(tǒng)治者的贊賞,還在秦始皇時"焚書坑儒"受到重創(chuàng),加之當時漢字尚處于雛形,不具備準確表達的功能,正統(tǒng)的儒家思想已基本消失。
二、以孝為核心的感恩思想經(jīng)歷盛衰跌宕
西漢初年,漢高祖總結(jié)秦亡教訓,選擇以儒家思想為主干同時兼采各家思想的適用部分作為自己的統(tǒng)治思想,其中“以孝治天下”的思想是其重要的組成部分。隨著《孝經(jīng)》經(jīng)學地位的確立,漢初以孝為核心的感恩思想在理論上的變化[5](p.84)表現(xiàn)在兩個方面:其一,實現(xiàn)了孝觀念從家庭道德觀念向社會道德觀念的理論轉(zhuǎn)變。《孝經(jīng)》第一章《開宗明義》說,孝是先王的“至德要道,以順天下,民用和睦,上下無怨”,明確提出宣揚和推行孝道的目的在于把孝作為建立新型社會秩序的指導思想,以孝治理天下;其二,忠孝一體,孝父與忠君一理。《孝經(jīng)》把家庭關(guān)系和社會關(guān)系混為一理,認為家是縮小了的國,國是擴大了的家,家庭是治國平天下的出發(fā)點,從而將君主與社會成員的關(guān)系說成是父子關(guān)系。這就使孝的意義有了新的引伸。而真正能反映西漢人對孝道予以理論深化的代表性觀點,當首推董仲舒的“三綱五常說”,他根據(jù)陰陽五行說中的“陽尊陰卑”的理論,把人間的尊卑關(guān)系和自然界的秩序統(tǒng)一起來。《孝經(jīng)》上說:“夫孝,天之經(jīng)也,地之義也。”孝是天經(jīng)地義,并提出了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的“三綱說”和“仁義禮智信”的“五常”說。在張錫勤先生看來,三綱是五常的前提、依據(jù),而五常又是對三綱的必要補充,是三綱得以實行的道德保證。至此,由三代而來的處理人倫關(guān)系的以孝德為核心的感恩思想被正式定為封建綱常,成為助長封建專制主義的工具。東漢儒學繼承董仲舒的思想,《白虎通義》指出,五行的行,體現(xiàn)著天意。“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為天行氣之義也。”五行體現(xiàn)于倫理,則是君臣父子的關(guān)系。“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順天也。”漢代儒學借助陰陽五行學說,增強封建倫理綱常的說服力,以維護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利益。這樣的以孝德為核心的感恩思想,不同主體感恩的對象、方式各不相同,且主體之間是單向的。天子感恩天地,“愛敬盡于事親,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諸侯感念君恩,“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jié)謹度,滿而不溢,富貴不離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卿大夫感念君恩,宗族之恩,“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士人“資于事父以事母而愛同,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故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庶人之孝:“用天之道。分天地之利,謹身節(jié)用以養(yǎng)父母”[6](p.27)。這就是說,天子當以治理好國家為回報天恩,諸侯要能保住自己的國家社稷為己任,報答君恩,卿大夫的孝要保住自己的宗廟祭祀,士人孝敬父母,但還要順從君主、官長,漢代及其以后的社會,用得最廣泛最普遍的還是士人之孝。
漢朝以后,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戰(zhàn),加上傳統(tǒng)儒學過于注重感恩形式,忽略感恩的本意,而受到來自王充的天道自然觀念的駁斥,強調(diào)“孝不以誠,慈不任實”就不是感恩的本意,傳統(tǒng)儒學發(fā)展出現(xiàn)衰落現(xiàn)象,難以與當時興盛的玄、道、佛爭鋒。晉時名士荀崧說“自喪亂以來,儒學尤寡”(卷75《荀崧傳》),特別是到西晉末,玄學熾熱,形成“仁義幽淪,儒雅蒙塵,禮崩樂壞”(卷75《范寧傳》)的局面。盡管整個時期儒學發(fā)展低迷,但仍然有潁川荀氏、汝南袁氏、瑯琊王氏、太原王氏等家族對儒學的堅守與傳播,他們努力傳播儒學傳統(tǒng)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及孝親、祭祀祖先等感恩觀念,并以此教導自己的子孫后代。其中尤以顏之推的《顏氏家訓》,他以儒家思想為標準,“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卷1《序致》)[7](p.154),他不僅教導孩子感恩父母,還提出父母感恩孩子的方式,“父母威嚴而有慈,則子女畏慎而生孝矣”,“骨柔之愛,不可以簡。簡則慈孝不接”,在《終制》篇強調(diào),“四時祭祀,周、孔所教,欲人勿死其親,不忘孝道也”。在感恩君主方面,顏之推提出因時因世選擇感恩忠君的方式,所謂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卷3《勉學》),同時還將忠君世俗化,“誠臣徇主而棄親,孝子安家而忘國,各有行也”(卷5《歸心》)。顏之推還教導人時時處處應心存感恩之心, “窮鳥入懷,仁人所憫,況死士歸我,當棄之乎?”顏之推及其后人對儒學的傳播,影響范圍畢竟有限,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猶如滄海一粟,終不能改變?nèi)鍖W的衰落的時代趨勢。
這一階段可以說是感恩思想伴隨著漢代儒學的興衰經(jīng)歷的跌宕起伏,一方面繼承了先秦儒學的仁義的感恩思想精華,另一方面也兼容吸收了陰陽五行之說,成就了以董仲舒為代表的大一統(tǒng)的儒學理論,儒學因此達到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shù)”的巔峰,峰回路轉(zhuǎn),漢以后儒學的正統(tǒng)地位受到佛教、道教的挑戰(zhàn),逐漸走向衰落,而感恩思想也在這個過程中得到融合和豐富。
參考文獻:
[1]2014年2月2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的講話.
[2]羅國杰.“孝”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和傳統(tǒng)道德[J].道德與文明,2003(3).
[3]孔子等.《論語.中庸.大學》[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年版.
[4]孔子等.《論語.中庸.大學》[M]北京:中國畫報出版社,2013年版.
[5]鄒效維,解保軍.孝觀念的歷史演進及其現(xiàn)代意義[J]學術(shù)交流,1997年第四期.
[6]李申.簡明儒學史[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6(6).
[7]洪衛(wèi)中.顏之推對儒家思想的堅守與世俗化傳播——以《顏氏家訓》為中心的考察[J]鄭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5,4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