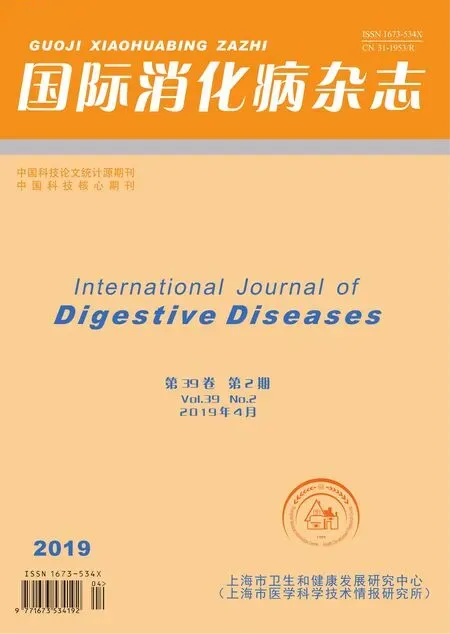細胞外囊泡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中的研究進展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指無過量飲酒史和其他明確的肝損傷因素、以肝細胞內脂肪過度沉積為主要特征的臨床病理綜合征,包括輕度脂肪變性、非酒精性脂肪肝(NAFL)、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炎(NASH)和伴纖維化的小葉壞死性炎性反應。NASH可進展成肝硬化、門靜脈高壓、肝衰竭甚至肝細胞癌(HCC)[1]。目前NAFLD被認為是疾病晚期肝衰竭的主要危險因素,預計到2020年其將成為美國肝移植的首要病因[2]。NAFLD的病因尚未完全闡明,其發病機制學說已由經典的“二次打擊”學說發展為“多次打擊”學說。近年來,生物醫學領域的研究熱點細胞外囊泡(EV)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其被認為是真核生物和原核生物細胞間通訊的有力工具[3]。
1 EV的概述
1.1 EV的定義與分類
20世紀下半葉,細胞外囊泡(EV)被認為是細胞降解時從細胞膜脫落的無關緊要的副產品。然而,近幾十年的研究發現,EV是生理和病理條件下細胞間通訊的重要媒介[4]。EV是由脂質雙分子層包裹的細胞衍生囊泡,直徑在30~2 000 nm。按細胞起源和生物學功能分類,EV又可以分為外泌體、微泡和凋亡小體。外泌體直徑一般為40~120 nm,起源于內溶酶體途徑、多泡體的腔內出芽以及多泡體與細胞膜的融合;微泡直徑一般為50~1 000 nm,起源于細胞表面,由細胞膜向外萌芽;凋亡小體一般為500~2 000 nm,經凋亡細胞大規模的質膜泡化而成,是細胞發生凋亡時伴隨的一種形式[5]。EV作為一種幾乎所有細胞都可以分泌的生物囊泡狀微小結構,廣泛穩定地存在于多種人體體液中,包括血漿、惡性腹水、羊水、尿液和唾液等[6]。EV的內容物和膜表面成分均攜帶有來源細胞的信息,其數量和內容物隨來源細胞的狀態和接受的刺激而變化,同一種細胞在不同狀態下可釋放出內容物完全不同的EV[7]。然而,由于分離方法的技術有限,導致這些亞型的區分較為困難。
1.2 EV的組成
EV攜帶各種脂質、蛋白質、RNA和DNA,脂質組學分析顯示,囊泡膜上含有豐富的膽固醇、鞘磷脂、神經酰胺、飽和脂肪酸、磷脂酰絲氨酸。此外,所有的EV都攜帶一些共同的標記蛋白,如熱休克蛋白(HSP70和HSP90)、內體特異性的四跨膜蛋白(CD9、CD63、CD81、CD82)、MVB生物發生相關蛋白(Alix 和 TSG101)以及膜運輸和融合蛋白(GTPases、flotillin、annexins)[8-9]。一些供體細胞的EV也含有獨特的蛋白,如來自B淋巴細胞和樹突狀細胞的EV包含主要組織相容性復合體Ⅰ和Ⅱ分子[10]。除了蛋白質外,EV還攜帶大量的信使RNA(mRNA)、DNA、長鏈非編碼RNA(IncRNA)、微RNA(microRNA)[7]。目前認為,這些EV攜帶的腫瘤特異性的miRNA或蛋白質可作為有臨床應用前景的生物標志物,用于疾病的診斷并指導治療,如肺癌、前列腺癌、乳腺癌等腫瘤和急性缺血性中風、腎臟疾病、阿爾茲海默癥、骨關節炎、炎癥性腸病等[11]。
1.3 EV的生理功能
EV的主要生理功能是細胞間通訊。通過直接膜融合、受體介導的融合或內吞作用,EV將攜帶的生物活性物質傳遞給受體細胞,并調節受體細胞功能。由于其表面攜帶多種黏附蛋白,EV可提供一種專有的途徑向治療靶點運送治療藥物。此外,EV可通過其親本細胞被修飾,在其表面表達或補充靶向部分所需的生物活性[12]。EV這種可以攜帶生物活性分子和定向向靶向器官傳遞的特性,為其成為藥物載體和潛在的治療劑提供了可行性。由免疫細胞和非免疫細胞產生的EV在免疫調節中也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可以介導或抑制免疫反應,并誘導炎性反應、免疫性疾病和感染性疾病的病理過程。因此,EV也有可能被用作調節免疫系統的治療劑[13]。
2 EV在NAFLD發生發展中的作用
2.1 肝臟分泌EV的特征
肝臟中的大多數細胞類型在體外條件下都可以分泌EV,包括肝細胞、膽管細胞、肝星狀細胞(HSC)、竇狀內皮細胞(SEC)、庫普弗細胞和其他免疫細胞(如巨噬細胞)[14]。蛋白質組學分析顯示,從原代大鼠肝細胞衍生的EV中分離出了251種蛋白質。除四跨膜蛋白(如CD63、CD81和CD82)、脫唾液酸糖蛋白受體1(ASGR1)外,在肝細胞衍生的EV中也發現了肝細胞特異性受體的富集。肝細胞來源的EV攜帶參與細胞內通路和解毒的蛋白質、細胞色素的胞質蛋白和分泌蛋白(如凝固相關蛋白和載脂蛋白)。這些發現表明肝細胞來源的EV攜帶的蛋白質和核酸可以隨細胞壓力和刺激而改變,即在疾病狀態下的細胞和組織相比于正常組,釋放出的EV會有所不同,這使得EV有成為肝臟生物標志物的潛力[15]。EV參與了許多肝臟疾病的發生、發展,包括丙型肝炎病毒(HCV)感染、乙型肝炎病毒(HBV)感染、HCC、肝纖維化、肝硬化、NAFLD和酒精性肝病(ALD)[16]。
2.2 EV與NAFLD之炎性反應
近年來在NAFLD的發病機制研究中,EV參與細胞間應激信號轉導這一作用被提出。飲食誘導的NASH小鼠血液中可檢測到肝細胞衍生的EV,并且EV的數量與疾病的嚴重程度相關[17]。動物模型研究發現,受損肝細胞來源的外泌體通過激活非實質性細胞(如內皮細胞、HSC、巨噬細胞)參與了NAFLD的發展,如多次打擊學說中血管生成、纖維化、炎性反應[17-18]。Heinrich等[19]的研究發現,喂食高脂飲食的大鼠血液中EV數量顯著增加;血漿中衍生的EV可顯著刺激活性氧(ROS)的產生,并誘導原代大鼠血管內皮細胞中血管細胞黏附分子1(VCAM1)表達,顯示其具有促炎特性。Hirsova等[20]的實驗發現,溶血性磷脂酰膽堿(LPC)模擬脂毒性誘導人類和小鼠肝細胞中EV的釋放,發現這些EV能以一種死亡受體5(DR5)的信號通路激活巨噬細胞。巨噬細胞的配體依賴性激活意味著死亡受體5的配體——腫瘤壞死因子相關凋亡誘導配體(TRAIL)存在于脂質處理后從肝細胞釋放的EV中,并作用于巨噬細胞上的DR5;棕櫚酸鹽處理的肝細胞釋放的EV上的TRAIL不誘導巨噬細胞凋亡,而是以受體相互作用蛋白1和核因子-κB(NF-κB)依賴性方式引起炎性反應應答,這表明脂毒性肝細胞誘導的EV具有促炎特性。實驗中采用Rho相關卷曲螺旋形成蛋白激酶1(ROCK1)抑制劑法舒地爾作用于小鼠肝細胞,顯著降低了LPC誘導肝細胞釋放的EV數量。這些發現表明脂毒性肝細胞釋放的EV在NAFLD進展中起到促炎和纖維化的作用。
2.3 EV與NAFLD之纖維化
EV不僅具有促炎特性,它在肝臟纖維化中也起著作用。肝臟由肝細胞、肝竇內皮細胞、庫普弗細胞、淋巴細胞、膽管細胞、HSC組成[21]。肝臟中的纖維化途徑主要受HSC調節,其產生并由纖維化介質如結締組織生長因子調控。Charrier等[22]的實驗證明,活化的HSC包裹的EV中存在一種多功能肝素結合糖蛋白,即促纖維化結締組織因子(CCN2),可穿梭至其他靜止或活化的HSC,肝臟在受到損傷時,以旁分泌的形式激活促纖維化作用。與此研究一致,Huang等[23]的研究發現,CCN2分子能夠聯合其他分子如纖連蛋白和轉化生長因子-β(TGF-β),促進活化的HSC增殖、存活、遷移、黏附和產生細胞外基質,從而促進肝纖維化途徑。Koeck等[24]的研究也發現,內臟脂肪組織中的EV可通過誘導肝細胞和HSC中TGF-β途徑的異常來參與NAFLD的進展。這些研究結果均表明,EV可能在NAFLD的纖維化過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2.4 EV內容物與NAFLD的診療前景
EV中攜帶的物質在NAFLD的發生、發展和診斷中起著作用。Povero等[25]的體外實驗研究顯示,使用膽堿缺乏型L-氨基酸(CDAA)和高脂飲食構建NAFLD小鼠模型,相比于對照組,NAFLD組血液循環中的EV數量增加,且蛋白質組學分析揭示了NAFLD組與對照組之間EV蛋白組分的差別。NAFLD組血液循環中EV攜帶的miR-122水平顯著升高,并證明了NAFLD中的miR-122主要封裝在EV中,提示在NAFLD進展中肝細胞特異性miRNA通過血液循環中EV釋放。肝臟是miR-122的主要來源[26]。此外,Csak等[27]發現血液循環中EV的miR-122水平升高伴隨著肝臟中miR-122水平降低,肝臟中下降的miR-122水平有利于組織重構調節劑上調,且在NASH的肝臟纖維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Yamada等[28]采用NAFLD的大鼠模型觀測了血液循環中miR-122的水平,發現血清miR-122水平確實可用于評估早期NAFLD,并可能優于傳統的臨床檢測肝臟情況的標志物。這些動物研究為了解EV在NAFLD中的作用奠定了基礎。
Kornek等[29]首次在人類受試者中建立了免疫細胞衍生的EV的豐度與疾病嚴重程度、肝臟氨基轉移酶的水平、活組織檢查分級和NAFLD活動評分之間的相關性,也就是說可以用來自血清的免疫細胞微粒的量化來評估慢性肝病患者的肝臟炎性反應程度和特征。該研究指出,慢性丙型肝炎(CHC)患者的血液循環中CD4+CD8+T細胞來源的微粒數量明顯增加,而NAFLD患者血液循環中來源于自然殺傷T細胞和巨噬細胞的微粒明顯增加。另一項轉錄組學分析通過檢測EV中的miRNA,可區分NAFLD和CHC,且揭示了可通過miRNA來區分肝臟疾病的分級和階段[30]。
綜上所述,EV參與了NAFLD發病機制中的關鍵部分,如炎性反應、血管生成、肝纖維化,并且其在NAFLD的診斷和治療中的作用也很重要。
3 小結與展望
EV在NAFLD的發生、發展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在疾病診斷方面,作為納米級生物膜結構,EV可以很好地確保內容物和生物活性的完整性,其具有作為NAFLD生物標志物的巨大潛力。在治療應用方面,EV因其穩定性和生物安全性可作為遺傳物質或藥物遞送的載體,基于改變EV分泌的策略可能有助于NAFLD的治療。此外,來源于間充質干細胞(MSC)的EV可能在一些肝臟疾病的治療中形成新的療法。但由于EV在生理條件下的重要作用,需要更多的研究來全面了解EV在NAFLD的生理和病理中的作用以及其在NAFLD診斷和治療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