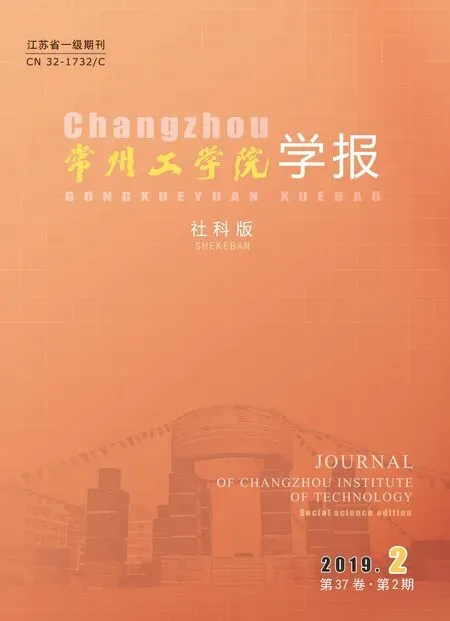霍桑短篇小說中的價值錯位結構
儲修友
(蚌埠醫學院外文教研室,安徽 蚌埠 233030)
小說文本中的“虛構的世界”與真實的世界,都是“可能的世界”。不僅如此,傅修延認為,“‘虛構的世界’是所有未實現的‘可能世界’中的佼佼者,它訴諸美”[1]52。文學敘述是一個建構“虛構的世界”的過程,由于它屬于一種藝術創作活動,因此文學虛構世界應該按照具有美感和藝術感染力的方式去建構。
孫紹振、孫彥君認為,對文學文本的解讀與批評要注重文學文本的審美價值。他們在借鑒、吸收中外文藝美學理論的基礎上,創造性地提出了“錯位”這一重要的文學審美批評范疇。具體而言,他們認為:文學藝術中的真、善、美三者都是價值判斷,分屬于不同的范疇體系,它們之間既不是完全統一的關系,也不是相互脫離的關系,“而是交錯的三個圓圈,部分重合,部分分離。在不完全脫離的前提下,錯位的幅度越大,審美價值越高,反之錯位幅度越小,則審美價值越低”[2]190。對文學虛構世界里的藝術形象而言,其“審美價值要超越功利的善和科學的真才能構成形象”[2]191。這一點對于分析、解讀中外的經典文學文本,判斷其審美價值、藝術價值,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本文將使用孫紹振提出的文學文本解讀方法,分析納撒尼爾·霍桑(1804—1864)短篇小說的代表性作品,探討他作為一位美國經典作家的審美理想、審美價值取向,以及相關作品的審美價值結構和藝術感染力的生成過程。
霍桑在其代表作之一《七角樓》(TheHouseoftheSevenGables,1851)的序言中指出,傳奇小說“在很大程度上賦予作者自行取舍、靈活虛構的權利,以表現特定環境下的真實”[3]83。傳奇小說具有的審美規范賦予了作家“自行取舍、靈活虛構”的文學創作權利,他們可以在小說文本的虛構世界里實現審美價值對實用功利價值和科學理性價值的超越,創造出鮮明生動的人物形象,充分展現人物內心情感世界的變化和獨特的精神價值追求。
一、《美之藝術家》中的美與善錯位結構
在短篇小說《美之藝術家》(TheArtistoftheBeautiful,1844)中,主人公歐文·沃蘭的審美價值追求與文本現實世界①中其他人物的實用功利價值取向發生了沖突,使得主人公和其他人物在情感關系和價值取向等方面形成了錯位的結構。
在這篇小說的文本現實世界里,退休的老鐘表匠彼得·霍文登是小鎮居民的典型代表,他長期為生計辛勞,講求實際。例如,彼得·霍文登在女兒擇婿的問題上頗費思量,最終督促女兒安妮選擇了體格健壯、干活踏實的鐵匠羅伯特·丹福斯,而不是徒弟歐文·沃蘭。在文本現實世界里,老鐘表匠的行動遵循著實用功利的理性邏輯,他鄙夷歐文·沃蘭對“美的理想”的追求,并直接干預了女兒安妮的婚嫁選擇。
歐文在小鎮居民中被視為異類,他身為鐘表匠,卻不務“正業”,反而熱衷于追求“美的理想”。例如,他為了讓店里待修的鐘表能發出和諧悅耳的聲音,“把音樂效能與手表的運轉部分聯系起來”[4]106,自作主張改造顧客的鐘表,使自己的信譽受損,導致顧客迅速減少。即使對審美理想的追求影響了店里的生意,他也毫不在意。由此可見,在小說的虛構世界里,歐文遵循著非功利的、非理性的情感邏輯。
由于歐文醉心于成為一名“美的藝術家”,即使遭遇挫折,他對美的追求依然如故。孫紹振把小說人物所具有的這種情感特點稱為“一點著迷”,“找到了這個癡迷的一點,人物的情感邏輯就不難自由地展現”[5]404。例如,為了向女友安妮表達情意,他竟然接連好幾個月埋頭于將“美的精神”做成有形的東西,并試圖讓它運動起來。正當此時,歐文的競爭者鐵匠羅伯特·丹福斯登門造訪。歐文的這位老同學肌肉發達,孔武有力。而歐文有著個性化的情感邏輯,對體格健碩的羅伯特予以否定性的情感判斷。歐文甚至覺得“他那無窮的野蠻力量使我的精神因素變得暗淡無光,把我弄得稀里糊涂的”[4]109。羅伯特·丹福斯和彼得·霍文登都欣賞“鋼筋鐵骨、肌肉發達”的人,因為他們是以實用功利主義的眼光來看待生活中的取舍與得失。然而,主人公歐文卻擁有自己作為“美的藝術家”獨特的情感邏輯。他對“美的理想”如癡如醉,即使身邊有一位愛情競爭者,他也毫不在意;即使“在世人以懷疑的目光看待他、攻擊他的時候”,他還是要求自己“必須堅定自己的信念”,“做自己唯一的信徒”[4]109。可見,情感邏輯不僅對人物的行動有強大的推動力,而且起到了推動情節發展的作用。
當師傅彼得·霍文登探望歐文時,歐文覺得自己與師傅個性不同,祈求上帝把自己從師傅的手里拯救出來。由于老鐘表匠“帶著世俗的非難、諷刺的目光”看待徒弟,而且嚴詞指責歐文追求“美”的努力是百無一用的,因此,兩個人矛盾激化,爭吵不斷。小說家在塑造人物時,分別賦予了雙方求善的實用理性邏輯和追求美的情感邏輯,從而導致矛盾和沖突事件出現。
朱光潛先生曾指出:“實用的態度以善為最高目的,科學的態度以真為最高目的,美感的態度以美為最高目的。”[6]451在《美之藝術家》中,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逐步分化為兩個擁有不同價值取向的陣營。這主要是因為霍桑對美的價值與善的價值的不同之處有清楚的認識。該小說原著中的關鍵詞語,如“utilitarian purposes”“sense of beauty”“passion for the beautiful”“the practical”等,有著清晰的內涵、外延以及價值指向,起著標示人物的價值取向、拉開人物之間的情感距離,以及塑造人物形象的重要作用。
不僅如此,作家為了塑造生動的人物形象、設計富有藝術價值的情節,讓主人公的審美價值取向超越其他人物的實用功利價值取向。霍桑通過虛擬、假定等文學手法,不僅讓歐文與師友發生沖突,友情破裂,而且還讓有情人發生齟齬,最終難成眷屬。女友安妮的來訪在歐文的愿望世界②里掀起了波瀾。正當這位“美的藝術家”要向安妮傾吐他的審美理想時,安妮不小心損壞了歐文微小的機械裝置。盛怒之下,歐文趕走了安妮。這個偶然事件使得歐文·沃蘭在愿望世界受挫,又失去了愛情。在人物自身情感邏輯的作用下,歐文與自己為敵,他的幻想世界③中出現了飄忽不定的幻覺,他的生命被罩上陰影,“陰影中充滿了嘲弄他的幽靈”[4]115。當師傅彼得·霍文登親自登門向他宣布女兒安妮與丹福斯訂婚的消息時,歐文受到強烈的刺激,他行動失常,失手將自己數月才完成的藝術品敲得粉碎。
不過,從情節布局來看,這是歐文的精神追求“破繭化蝶”之前最后的蟄伏期。當歐文在追求“美的理想”的路上經歷了勞苦、疾痛之后,小說情節發生了戲劇性的“突轉”。
在情節的高潮處,霍桑“選擇了一塊介于現實和想象的‘中間地帶’作為自己的創作空間”[7]334,在小說文本所建構的可能世界里創造了“蝴蝶”這一核心審美意象。它不僅具有豐富的藝術蘊涵,而且在文本虛構的世界里,起到了進一步拉開人物之間情感距離的作用,從而能夠以審美價值超越實用功利價值,形成美與善錯位結構,最終提升小說的藝術價值。
一只“超越世俗”的蝴蝶,象征著歐文對理想美的追求。他帶著裝在烏檀木盒子里的蝴蝶去看望安妮,把它作為送給安妮的結婚禮物。當木盒打開,一只光輝璀璨、艷麗奪目的蝴蝶在眾人面前振翅欲飛時,小說人物的情感立刻發生了分化。安妮以理智的而非藝術的眼光來觀看它,一邊驚詫于它的美麗,一邊很認真地反復追問,它是否為一個“活物”。同樣,她的丈夫羅伯特·丹福斯也以實用理性的態度去觀看那只蝴蝶。他還避重就輕、略帶醋意地說:“無論哪個小孩,在夏天的一個下午就能捕捉到幾十只蝴蝶!活的?當然啰!不過這個漂亮的小禮盒毫無疑問是我們的朋友歐文的杰作……”[4]124丹福斯避“蝴蝶”而談“小禮盒”,以“買櫝還珠”的方式看待歐文的藝術作品,反映了他審美能力的貧乏和對藝術價值的輕視。
然而,歐文認為,這只富有藝術美的蝴蝶“完全可以說它具有生命,因為它已經把我的生命吸收進去了。在這只蝴蝶的秘密中,在它的美中……智力、想象力、敏感性、美的藝術家的靈魂等等都得到體現了!”[4]124,這表明,歐文已經把這只蝴蝶視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這只蝴蝶有了他的靈魂,融入了他的審美情感。歐文在追尋理想、成長為真正藝術家的過程中,逐步超越了世俗生活的苦痛,已經達到了用藝術家審美的態度和眼光看待事物的人生境界。
相形之下,羅伯特·丹福斯則成了文本現實世界中實用功利價值觀的代表。他聲稱:“我一錘子下去的實用價值,比我們的朋友歐文在這只蝴蝶身上耗費五年青春所花的心血都要大。”[4]125鐵匠囿于世俗生活,即使面對美的事物,也不能把自身從世俗功利的泥淖和實用理性的桎梏中解脫出來。在歐文想了解安妮是否同意丹福斯的觀點時,卻發現安妮的目光帶有“一種隱秘的輕蔑”[4]125,這表明安妮也是現實世界中過著庸常生活的一員。他們只會從實用功利的角度看待藝術和審美,都是缺乏審美意識的人,因而他們對歐文這樣的熟人缺乏真摯的情感關懷。
歐文雖受到丹福斯的嘲弄和安妮的蔑視,卻并未有挫敗感,他在后來的藝術追求中已經無視別人的漠視與嘲弄。由于藝術中的審美創造擺脫了實際功利目的的糾纏,因而具有其獨立的意義和價值。藝術審美創造不僅具有深厚的人性根基,而且是人類的一種重要的自我超越方式——審美超越。劉旭光認為:“所謂審美的超越,主要是指以審美的非功利性讓人從功利生活解脫出來,以審美的精神性讓人的心靈暫時到達精神的彼岸,同時,借審美的非功利性、情感性與精神性,讓審美成為精神救贖的一種手段。”[8]21
處在文本現實世界中的歐文,正是以這種審美超越精神,逐步走向他所追求的超越性價值目標。在此過程中,他擺脫了現實社會功名利祿的羈絆,拋開了世俗的是非之爭,心靈受到美的陶冶,精神境界獲得了提升,實現了自身的成長。
在小說的結尾處,“蝴蝶”這一意象再次起到了凸顯人物價值取向的差異、拉開人物之間心理距離、形成美與善錯位結構的重要作用。正當這只蝴蝶在丹福斯一家人中間輕盈飛舞時,安妮的幼兒一把將它抓住,攥在手中。孩子的家長都為蝴蝶被毀而慌亂,而蝴蝶的主人卻并不為藝術品被毀而動容。他也不以為那是“毀滅”,因為在他的心中,藝術品蝴蝶的客觀物質性存在已經虛化了,他追求的是美的內蘊和意義。德國哲學家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指出,“人必須完全不對這事物的存在存有偏愛,而是在這方面純然淡漠,以便在欣賞中,能夠做個評判者”[9]41。所以,故事的敘述者告訴讀者,歐文早已捕捉到比這只蝴蝶更崇高的東西,即藝術家的審美理想與追求。誠如劉旭光所言,“美是永恒之物,藝術是為了捕捉永恒與創造永恒。美和藝術因此成為人們思考和追求永恒的一種手段,而不是娛樂的工具”[10]97。霍桑賦予了歐文以獨特的情感邏輯和超越性的審美價值追求,歐文成為文本現實世界中一位具有形而上藝術理想的主人公。
二、《胎記》中的美與真錯位結構
在霍桑的另一短篇小說《胎記》(TheBirth-mark,1843)所創造的文本現實世界里,青年科學家艾爾默的知識世界與其妻子喬治亞娜的情感世界產生了沖突,形成了科學理性價值和審美情感價值的錯位結構。
艾爾默是一位青年化學家,他矢志獻身于科學研究事業。婚后他發現美麗善良的妻子喬治亞娜的左臉頰上有個小手形的胎記。他越是端詳,越是難以忍受,認為那塊胎記是“凡人的不完善”的象征,必欲先除之而后快。
艾爾默對妻子臉上胎記的頻繁“凝視”使“胎記”成為該小說的核心意象。由于艾爾默的情感世界受到其知識世界中科學理性的牽制,他對新婚妻子的愛意漸漸減少。英國文學評論家詹姆斯·伍德認為,“許多小說中最生動的人物都是一根筋的偏執狂”[11]94,艾爾默也是如此。
艾爾默在情感上的偏執傾向,導致他的思想發生了變化。例如,他“認定妻子的胎記是罪孽、悲傷、衰敗和死亡的象征”[4]27。妻子喬治亞娜很快發現了丈夫詭異的眼神,“于是在他的目光凝視下顫抖起來”[4]28,她的精神世界產生了波瀾。那塊胎記成為夫婦雙方情感方面的“結”。艾爾默為了解開這個“結”而采取的各種行動,既拉開了雙方的情感距離,也展示了人物的內心世界。
艾爾默選擇通過科學理性的方式解開這一“結”。他甚至已經在夢境中和實驗室助手阿明拉達伯一起給妻子實施手術,毫不留情地把已經和她心臟連在一起的胎記切除掉。喬治亞娜為了消除丈夫的疑慮和恐懼,選擇冒險接受手術,這是她主動做出的犧牲,體現出她看重情感的價值。而此時艾爾默竟然欣喜若狂地喊了起來,“喬治亞娜,你讓我比以前更加深入地進入科學的心臟。我感到自己完全有能力將這親愛的面頰變得像另一邊面頰一樣完美無瑕”[4]29-30。在艾爾默看來,他青年時代深入鉆研過許多自然科學知識,還研究過人體的奧妙,因而可以運用科學知識讓喬治亞娜的臉頰變得如他想象的那般完美。
當喬治亞娜走進實驗室,艾爾默看到妻子臉上的胎記時,“他非常吃驚,不禁打了一個強烈的痙攣性的寒戰”[4]31。艾爾默之所以有這樣的反應,主要是由于其情感世界遭受到理性邏輯的異化,以致當他面對美麗善良的妻子時,竟只能看到那一點若隱若現的胎記。艾爾默非但沒有成為科學知識的主人,反而被它們所控制,成為心理變態的哥特式男主人公。
在看到丈夫異乎尋常的反應后,心理壓力巨大的喬治亞娜當場暈厥。在她蘇醒后,艾爾默不僅沒有意識到自己對妻子情感的傷害,還提出要對她使用一種化學藥劑。而此刻女主人公備受折磨,甚至出現幻覺,“她的內心有一種痛苦和愉快參半的刺痛感覺”[4]35。然而,喬治亞娜的驚恐、暈厥和痛苦感受都沒有改變艾爾默的“科學邏輯推理”[4]33。他對妻子說:“除非我的所有科學知識都讓我上當受騙了,否則它不可能失敗。”[4]40這表明艾爾默對科學理性價值的癡迷已經到了入魔的程度,居然把妻子當成了化學藥劑的實驗對象和“徒具人形的機器”[4]38。
艾爾默慫恿喬治亞娜將藥劑一飲而盡。在妻子昏睡未醒時,這位青年科學家密切關注妻子身體的變化,在實驗記錄上做筆記。妻子醒來后,他除了大聲咒罵其助手還驚呼道:“可憐?不,我是最富有、最幸福、最受天寵的!”[4]42艾爾默的理性邏輯一直主宰著他的思維和行動,因而他認識不到愛的力量和情感的價值。科學知識自有其啟蒙心智、改造自然等重大價值,但艾爾默迷失在科學實驗所代表的科學理性邏輯之中,他對妻子的情感早已異化。從情節結構上來看,這拉開了男女主人公情感的距離,造成了人物心理的錯位。在文本的審美價值上,則形成了美與真的錯位結構,使得這一哥特風格的故事超越了文學史上眾多哥特小說的審美價值。
三、結語
在《美之藝術家》的文本現實世界中,歐文執著于美的價值,不計較世俗的利害得失,勇于追求精神的超越,最終使自己從他人功利的目光中解脫出來,心靈獲得了救贖。而且,在該文本的審美價值結構中,形成了美與善的錯位結構。在《胎記》的文本現實世界里,由于艾爾默對科學知識的價值過度癡迷,導致他漠視愛情,戕害妻子,最終喪失了拯救其愛情、婚姻的機會,走上了毀滅的不歸之路。在文本的審美價值結構中,形成了美與真的錯位結構。霍桑對短篇小說的審美規范進行了大膽創新,讓虛構人物的情感的非功利價值超越理性的功利價值和科學的認識價值,從而塑造了個性鮮明的人物形象,深刻揭示了人物復雜的精神世界。這也是霍桑在短篇小說創作領域取得巨大成就的原因之一。
注釋:
①根據可能世界敘事學的理論,文本現實世界是指文本指涉世界,它“是作為外在于它的一個實體的精確表征而提出的”。關于這一范疇的詳細闡述,參見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24-25。
②美國學者瑪麗-勞爾·瑞安教授在她的文本世界模型里,將虛構人物的私人世界進一步劃分為知識世界、責任世界、愿望世界和幻想世界等。參見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114-119。
③幻想世界由人物的心理創造物構成,如夢想、幻覺、幻想或人物自己編織的虛構故事等。參見Marie-Laure Ryan:Possible worlds,artificial intelligence,and narrative theory,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91,p1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