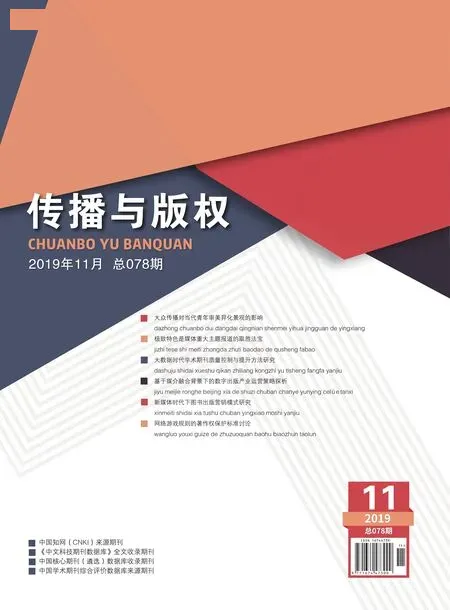應對影視劇本抄襲現象的著作權法思考
鐘玉琴
(華東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江西 南昌 330013)
我國版權法中提到的剽竊行為具體是指未得權利人同意,擅將其作品竊取冒充為自己的作品進行使用以侵害其著作權的違法行為。其特征就在于未經他人允許,切斷作品與作者之間的對應署名關系。由于我國著作權法中有關抄襲的概念規定過于籠統,缺少詳細的界定標準,導致剽竊、合理使用等概念的區別難以明晰。因此,本文結合案例進行討論,尋求懲治抄襲背后的困境,從而為完善著作權法提出建議。
一、劇本抄襲的認定
以抄襲方式與程度為區分標準,著作權領域一般將抄襲分為“低級抄襲”與“高級抄襲”。[1]前者通常原文或基本原文復制他人作品,其認定較為容易,通過感官上的比較即可。此種抄襲雖照搬復制,但由于抄襲的片段涉及較多作品,因此在證據收集上也頗為困難。而后者則將他人的受著作權保護的獨創成份以自己的語言重新加以描述而挪為己用,這往往需要專業性的鑒定才可確定。瓊瑤訴于正案中,雖然大致人物關系與劇情梗概不受保護,但具體人物情節卻將形成受保護的具體表達。《梅花烙》與《宮鎖連城》在“偷龍轉鳳”“道士捉妖”等9個情節上雖少數細節與順序不同,但并不影響觀賞性與整體性的實質一致。此種利用他人在先創作的原創情節,抽取創意重新編排竊為己有的方式便是“高級抄襲”。司法實踐中,用于判定剽竊主要有三大因素:[2]
第一,原告系劇本著作權人。確定所涉劇本系主張侵權者的創作作品是首要前提,主張者應以對作品依法享有的著作權作為權源。
第二,被告作品與原告作品實質性相似。實質性相似判斷規則是在司法實務中形成的一套侵權認定規則,即普通非專業的大眾能夠識別出被訴作品剽竊了原告的版權作品。[3]區分思想與表達區分是前置工作。著作權法中的思想如題材、主題、事實等,被法律劃入公共領域范疇,不屬于任何人的獨創。將不受保護的出場人物與劇情梗概剝離,對詳細人物關系、具體情節及其結合的表達方式進行比對,當在后作品與在先作品已達到一定質或量的相似程度,便可認定為構成侵權。
第三,被告有接觸作品的可能。按照被告接觸原告作品的方式,可將接觸分為直接接觸和間接接觸。實踐中證明侵權人曾接觸作品并非易事,此時可通過客觀理性第三人的視角,以兩部作品構成實質性相似的事實來推定接觸的“合理可能性”。認定被告有曾接觸過原告作品的可能性,只需證實原告作品曾在侵權人所知曉或可能知曉的范圍內以公開方式傳播,侵權人客觀上有接觸作品的可能即可。
司法實踐中著作權往往得不到良好保護,欲從根本上抑制抄襲侵權的頻發,首先需探知著作權法應對該現象的困境所在,方可對癥下藥。
二、著作權法應對抄襲現象之困境
抄襲屢禁不止,很大原因在于我國著作權法存有不足。現就其主要困境進行分析。
(一)維權成本高,耗費時間長
首先,就收集證據而言,被侵權者負有將實質性相似部分一一羅列比對的義務。例如,早前被曝抄襲的《錦繡未央》,據志愿者統計其抄襲作品多達兩百部,因此單單找出被抄作品進行比對就是一項大工程。其次,成本過高、維權耗時過長的訴訟現狀也令原作者望而止步。莊羽訴郭敬明抄襲案中,莊羽維權歷時三年方迎來勝訴。這無不說明我國的版權保護仍有待加強,原作者勝訴難,還可能面臨得不償失的結局。
(二)抄襲借鑒難區分,無明確界定標準
借鑒與抄襲一直是著作權保護上難以區分的兩個概念。我國著作權法不保護主題思想、人物關系線以及情節梗概,這意味著只需抄襲原作者的創意加以潤色,即有很大可能無法被認定為侵權行為,“洗稿”已然成為當下最難以被懲治的抄襲方式。
上文已述,我國在抄襲侵權的構成要件上采用“實質性相似+接觸”的核心標準,比對相似與否首先要“過濾思想”,刨去不受保護的作品主題,再進一步排除事實、情節和公有領域素材等內容,最后再對比剩下的內容是否構成“實質性相似”。法院的判斷標準,一般依靠復制數量在被侵權作品中所占比例進行比較,復制的比例越大越容易被認定為侵權,同時結合具體案情進行個案分析。但著作權客體排除思想的特點導致裁判標準過于抽象籠統,同時縱觀我國學術界和司法界,對實質性相似判斷規則的研究及規定零散而不成體系,因此法院的自主衡量在著作權侵權案件中起到很大的決定作用。瓊瑤訴于正案中只有9個情節被判定為實質性相似,而法院采取的判別標準無從得知。界限不明確給了抄襲者極大的鉆空子機會。
(三)賠償標準過低,懲治力度不夠
著作權第49條系有關賠償的規定,但其看似周全,實踐中卻不易操作。
我國對賠償數額的確定主要分為三大形式:權利人實際損失、侵權人違法所得以及法定賠償。一般優先適用的權利人實際損失以及侵權人違法所得的認定對相關證據要求較高。首先,權利人往往難以證明其實際損失數額,這種損失大多數來自精神、名聲以及潛在締約機會等。其次,因文化傳播平臺的多元化,侵權作品常涉及多行業,證據往往難以完整涵蓋違法所得,且法院在證據的采信上要求極高,因此法院通常采取酌定賠償予以認定,而這種高度自由心證的認定方式在實踐中使得賠償數額只能勉強填平維權者的維權成本,這相較侵權者依靠抄襲作品得到的大量財富簡直是九牛一毛。瓊瑤一案看似賠償高達500萬元,卻是于正與四影視公司連帶賠償,而于正依靠《宮鎖連城》劇本賺取的酬金就已高達千萬元。維權賠償低于侵權得利終將挫傷維權積極性。
三、應對抄襲現象的著作權法完善對策
著作權愈發在國際上占據重要位置,雖然我國對其保護的制度構建較晚,發展速度卻不容小覷,但保護版權仍任重道遠。針對影視圈劇本的保護,筆者有以下幾點建議。
(一)明確抄襲認定數量原則,減少自由裁量余地
司法實踐中,曾有兩個均涉嫌抄襲5000字的類似案件,一個被認定為抄襲,而第二個卻被法院以抄襲文字占被告作品不到1%為由認定為不構成抄襲。
其實,司法實踐中比例原則的適用會滋生許多問題。法律對相似比例并無明確規定,從而加大判決結果的差異性,因此將抄襲認定改以數量原則似會更有效解決此類問題。數量原則,設“量”為衡定根本,同時以兩部作品實質性相似的具體情節的“質”判其“量”,如抄襲他人作品中的經典表達就應當比抄襲普通情節的判定量高,當抄襲總數量突破法律紅線,就應當判其抄襲,而不考慮占全文比例。這樣可在類似案件判決中定以統一標準,從而避免法官認定差異大,解決通過擴大作品規模以規避法律的可能。至于“質”與“量”的具體標準可以通過提取全國類似案件的共同之處,并加以考慮影視圈創作者的行業習慣與共識予以明確規定。
(二)增設劇本集體管理組織,實行登記保護
編劇自薦劇本時,常會出現劇本不被采納創意卻被抄襲的現象,如此正是因為創意并不在我國著作權法保護范圍內。倘若有專門的集體管理組織對劇本進行綜合保護與市場外推,將使創作者的心血得到更好保護。自1992年我國成立了第一家著作權集體保護組織,到2005年相應實施條例才頒布、實施,事實上我國的集體管理制度遠沒有起到其應有作用。
首先,應增設各行業的集體管理組織,使其兼顧非營利性與競爭性,給創作者們自主選擇的機會。其次,劇本一經創作,便應投入劇本集體管理組織。此處可效仿美國編劇工會的做法,將每部劇本予以注冊并進行標記,而劇本在全本交出前均須簽訂保密合同,凡是收到劇本的一方都必須簽署此合同,而這些證據也將在日后可能發生的糾紛中起到巨大作用。創作者的維權能力通常不足,將妨害統一交由專業集體管理組織處理,程序化維權必能更有效保護創作者的勞動成果,且追究責任主體從勢單力薄的個人轉變為專門的集體管理組織,也將更有利于長期對抗制片公司。
(三)完善訴前禁令制度,加責于傳播平臺
《著作權法》第50條系有關訴前禁令的規定,然而實踐中這一制度極少能派上用場。瓊瑤訴于正案中,瓊瑤得知消息主張權利時《宮3》已經播出21集,自瓊瑤收集足夠證據到法院48小時內裁定,等到法院真正執行之日,涉嫌抄襲的影視劇一般已播放完畢,而這將嚴重損害原作者的權益。
維護原作者權益的責任不應全部依賴法院,應當將部分保護任務設立給傳播者。若利害關系人有充足證據支持其主張,而傳播者不在合理時間范圍內停播涉抄劇,那么傳播者應為日后抄襲者的敗訴承擔相應責任。傳播者通常具有實質審查的義務與能力,因此其對抄襲影視的失察與傳播顯然具有過錯。反之,若在控訴時及時下架或停播的傳播者則可視為無過錯,無須承擔責任。設責于傳播平臺可彌補訴前禁令的滯后性,且更有利于抑制抄襲劇的傳播,于更大范圍內保護利害關系人權益。
(四)創立抄襲黑名單,加大執法力度
影視圈抄襲現象屢禁不止很大程度是因為懲治力度不夠。當前我國懲治力度過小并不足以影響抄襲者在市場上的地位。
國家可專門成立一個“抄襲污點檔案”,通過全國聯網將各地區因抄襲而敗訴的剽竊者記錄在案,對達到一定抄襲次數的剽竊者予以行業除名,禁止制片公司再使用其劇本。同時我國的執行也不夠到位,在執行停止侵害上應大力查封各類傳播途徑,賠禮道歉也應有相應格式要求,如親手書寫道歉信在全國刊物上予以公示,不按要求道歉或是拒不道歉的抄襲者應當入檔以示警告,使屢抄不改的剽竊者面臨被逐出行業的重大處罰,才能使得抄襲者心中真正有畏懼感。
四、結語
著作權的發展有效推動了我國精神文化的發展,同時在共用思想與保護表達之間尋求平衡也已成了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明確概念,發現背后困境所在,不斷順應時代對其做出改變與完善,加強對創作者們的保護,嚴懲抄襲者們的不齒行為,必能引百家爭鳴,使得智力創作之花綻放于全國,引領中國社會主義文化走向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