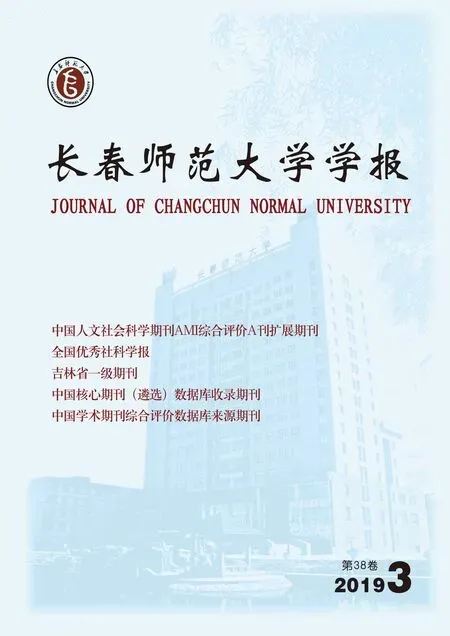三蘇論管仲之評析
管成學,管 恕,荀長春
(1.北大資源學院,北京 100097;2.北京大學 國家軟實力研究中心,北京 100871;3.吉林大學萊姆頓學院,吉林 長春 130012)
管仲作為春秋第一名相,深受孔子的稱頌:“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微管仲,吾被發左衽矣。”(《論語·憲問》)。
蘇洵、蘇軾、蘇轍都寫有《管仲論》,專門論述管仲其人其事。他們所議論的角度不同,表現方法各異,但對管仲都給以高度肯定,并指出他的不足之處。
一、蘇洵論管仲
蘇洵論管仲,主要見于他的《管仲論》(見于《嘉祐集》卷九)。
(一)全面肯定管仲的功績
蘇洵充分肯定了管仲相齊的功績,在《管仲論》開篇就說:“管仲相桓公,霸諸侯,攘戎翟,終其身齊國富強,諸侯不叛。”[1]
蘇洵在《管仲論》中又說:“彼桓公何人也?顧使桓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桓公聲不絕于耳,色不絕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1]蘇洵認為桓公是一個沉湎聲色的君主,因有管仲為賢相,豎刁、易牙、開方這樣三個以聲色討好君主的小人并不能亂政,不能影響齊國之富強;管仲一死,齊國不久就大亂了。
蘇洵看到了管仲輔佐桓公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軍事改革取得的巨大成功,沒有管仲的謀略,齊國是不能走向民富國強、稱霸諸侯、一匡天下的。
(二)尖銳批評管仲不注意培養接班人
蘇洵對管仲的批評有失公允,我們也略作辯析。
蘇轍引用其父蘇洵論管仲之言說:
《傳》曰:“管仲病且死,桓公問誰可以使相者,管仲曰:‘知臣莫若君’。公曰:‘易牙何如?’對曰:‘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何如?’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何如?’對曰‘自宮以適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桓公不用其言,卒近三子,二年而禍作。”“夫世未嘗無小人也,有君子以間之,則小人不能奮其智。《語》曰:‘舜有天下,選于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舉于眾,舉伊尹,不仁者遠 矣。’豈必人人而誅之?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御之,何益于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彼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2]
蘇轍引用蘇洵論管仲之言,批評管仲在病危之際,面對桓公問其逝后何人任相,只說易牙等三人不可用,并沒向桓公推薦良相。批判曰:“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御之,何益于事?”[1]
每讀蘇洵之文,則心生疑惑。以管仲之一世英明,面對他與桓公所創之偉業,怎能不選擇接班人呢?
近讀《諸子集成》,發現兩條史料,可糾正蘇洵所論之偏頗。以就正于致力于蘇學的專家們。
管仲臨終時,齊桓公問鮑叔牙可否任相,管仲作了如下回答(被韓非子記于《十過》):“鮑叔牙為人剛愎而上悍。剛則犯民以暴,愎則不得民心,悍則下不為用,其心不懼。非霸者之佐也。”談到隰朋時說:“其為人也,堅中而廉外,少欲而多信。夫堅中則足以為表;廉外則可以大任;少欲則能臨其眾,多信則能親鄰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3]鮑叔牙對管仲有大恩,但管仲并不任人唯親,而是以國家的利益為重,認為鮑叔牙不可任相。管仲推薦了隰朋,“此霸者之佐也,君其用之”。
管仲對鮑叔牙和隰朋誰可任相的評論,被管仲的后學們記載于《管仲·戒》中,與《韓非子·十過》所論大同小異。在《管仲·戒》中,管仲談到鮑叔牙時說:“鮑叔,君子也。千乘之國,不以其道予之,不受也。雖然,不可以為政。其為人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談到隰朋時說:“朋之為人,好上識而下問。臣聞之:以德予人者,謂之仁。以財予人者,謂之良。以善勝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者,未有不服人者也。于國有所不知政,于家有所不知事,必則朋乎!且朋之為人也,居其家不忘公門,居公門不忘其家,事君不二其心,亦不忘其身。舉齊國之幣,握路家五十室,其人不知也。大仁也哉,其朋乎!”[4]
管仲病危時,桓公問及誰可任相一事,又記于《莊子·徐無鬼》:“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謂)[諱],云至于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也,其于不己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于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以德分人謂之圣,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于國有不聞也,其于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5]
以上三則史料明確告訴我們:管仲不像蘇洵、蘇轍說的那樣,僅僅否定了易牙等三個媚君的小人而沒有推薦賢相。他以國家的前途和命運為重,否定了自己的恩人鮑叔牙,而推薦賢相隰朋。
管仲是春秋時期最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至今福澤著神州大地,弘揚管仲的文化遺產是我們當仁不讓的職責。
二、蘇軾論管仲
蘇軾論管仲不同于蘇洵,蘇洵沒有經歷蘇軾的坎坷。蘇軾像管仲一樣胸懷忠君愛民、致君堯舜的雄心壯志,想使積貧積弱的北宋政權走上富國強軍之路。但是,剛愎自用的宋神宗不肯采納他的意見,又聽信李定、舒亶、賈種民等的誣告,逮捕、貶斥了他。所以,他更能理解管仲讓沉湎聲色的齊桓公接受他的改革,談何容易啊!蘇軾給管仲以更多的理解,對其評價也更加全面和準確。
蘇軾一生仕途坎坷,既不見容于新黨,也不見容于舊黨,飽嘗宦海沉浮之苦。政治上的挫折滋長了他逃避現實和懷才不遇的思想情緒。所以,他的思想比較復雜,把儒、佛、老三家哲學結合起來,對各家各派兼收并蓄、融會貫通。因此,他對管仲的了解和評價是非常全面中肯的。
蘇軾論管仲的文章比較多,除了《論管仲》《管仲分君謗》《管仲無后》等三篇外,還有《學士院試孔子從先進論》《思治論嘉祐八年作》等文章。
(一)蘇軾《管仲論》專論《管子》的軍事思想
管仲輔佐齊桓公,希望剛剛從動亂中穩定的齊國建立一支強大的軍隊。管仲是怎樣組織和培訓這支軍隊的呢?蘇軾研究了《管子》的“七法”“九變”“兵法”等軍事著作,又與《司馬法》、周代軍隊編制相比較,得知管仲的軍隊編制和軍隊訓練的獨特之處。《司馬法》曰:“五人為伍,五伍為隊,萬二千五百人而為軍。二百五十,十取三焉而為奇,其余七以為正。四奇四正,而八陣生焉。”周代兵制和《司馬法》講的是陣法,追求的是守衛和不敗。
蘇軾在《管仲論》中,盛贊管仲“簡而直者”“有所必勝”的戰法。“若夫管仲之制其兵;可謂截然而易曉矣;三分其國,以為三軍。五人為軌,軌有長。十軌為里,里有司。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為鄉,鄉有鄉長人。三鄉一帥。萬人而為一軍。公將其一,高子、國子將其二。三軍三萬人。如貫繩,如畫棋局,舒暢洞達,雖有智者,無所施其巧。故其法令簡一,而民有余力,以致其死。”“由此觀之,不簡而直,不可以決勝。深惟后世不達繁簡之誼,以取得敗亡,而三代什伍之數,與管子所以治齊之兵者,雖不可盡用,而其近于繁而曲者以之固守,近于簡而直者以之決戰,則庶乎其不可敗,而有所必勝矣。”
蘇軾認為管仲改變周代和《司馬法》推崇陣法、用以固守的軍事思想,采用簡而直的“決戰必勝”的策略,是其軍事思想的重大貢獻。
(二)蘇軾《管仲論》闡述道德與史論
1.堅辭子華之請以弘德
蘇軾在《管仲論》一文中引用的第一件史實是管仲勸齊桓公堅辭鄭太子華有違周禮之請求,訓以弘德之辭,以揚周道。
鄭太子華言于齊桓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公將許之,管仲不可。公曰:“諸侯有討于鄭,未捷。茍有釁,從之,不亦可乎?”管仲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總其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乃受盟。
蘇子曰:大哉!管仲之相桓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皆盛德之事也。
2.不違曹沫之盟以守信
曹沫者,魯將也。與齊戰三敗北。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于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曰:“齊強魯弱,請還侵奪之城”。桓公當眾許之,曹沫歸其座。其后,桓公怒,欲違其盟。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于諸侯,失天下之授,不如與之”。于是,桓公聽管仲諫,盡復侵魯之地。
齊桓公讓出的是侵魯之城,而得到的是天下信譽。齊桓公與管仲多次召集諸侯會盟,確立了齊國的霸主地位。
管仲輔佐齊桓公,以道德與誠信征服諸侯的政治理念,得到蘇軾的高度評價,稱贊為“盛德之事”。
3.“七人為萬世法者”言史論重在當世
蘇軾在《管仲論》中說:“吾讀《春秋》以下史,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可以為萬世戒”。
“七人為萬世法者”,乃桓公、管仲不廢田敬仲,欲以為卿;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漢高祖知東南必亂,而不殺吳王濞;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唐玄宗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
這七個可謂萬世法者的歷史人物中,蘇軾首推管仲。蘇軾認為齊景公不用繁刑重賦,雖有實力雄厚、野心勃勃的田氏,也無法取代齊國。所以,后世論史者認為管仲不該以田敬仲為卿的評論是不公平的。其他六人也是一個道理,從吳王濞到安祿山,在沒有他們反叛的證據時,不能以傳言或疑惑殺人,即史論重在當世,懲罪殺人,必須有實證。
4.“八人為萬世戒者”言不以成敗論是非
“八人為萬世戒者”是:“漢景帝以鞅鞅而殺周亞夫,曹操以名重而殺孔融,晉文帝以臥龍而殺嵇康,晉景帝以名重而殺夏侯玄,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齊后主以謠言而殺斛律光,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武后亦以謠言而殺裴炎。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
蘇軾所強調的是史論不能以成敗論是非。成功者依然會做錯事,漢景帝總體上應該是一個好皇帝,但他逼死周亞夫的過錯是不可原諒的,必須受到批判。蘇軾《管仲論》留給我們的史論標準是值得稱頌的。
三、蘇轍論管仲
蘇轍的《管仲論》主要繼承了父親蘇洵的觀點,責怪管仲沒有舉薦賢相。蘇轍在《論語拾遺》《馮道》《策問十六首》等史論中也對管仲多有褒貶,在此擇其精要,給以評析。
(一)欽佩管仲大節無虧
蘇轍與蘇軾都批評管仲的奢靡生活、聚斂財富,認為管仲的品德不符合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標準。但是,蘇軾以忠臣為君“掩過”、“分謗”為由,替管仲辯解。他以自身的經歷深知管仲要改變齊桓公沉湎聲色的享樂是不可能的,所以認為管仲“三歸之家,樹塞門,有反坫”,是為了“分君謗”,以掩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之過。蘇軾在《管仲分君謗》中說:“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分謗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不用而已矣。”[6]
蘇轍與蘇軾不同,認為管仲大節無虧。蘇轍論人大膽立異,能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評價歷史人物,在《馮道》一文中說:齊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從而相之;晏嬰與崔杼俱事齊莊公,杼弒公而立景公,晏嬰伏尸大哭,卒事齊景公。
蘇轍認為,議論馮道的人應該多一些寬恕。他深知仕途的兇險,認為馮道日日與暴君驕將相伴,不僅能夠自保,而且能有益于社稷,確實是不容易的。他甚至把馮道和管仲、晏嬰相比,認為他雖功不過管仲,卻無愧于晏嬰。
(二)以治國論管仲之才
蘇轍在《進策五道·第四道》中高度評價管仲的治國之才。他列舉管仲勸齊桓公忍曹沫持刃之辱、信守退還侵魯之城、贏得諸侯的信譽為證。當齊桓公因為怪罪少姬而攻打蔡國時,管仲“責苞茅不貢于周室”,以尊王之大義代替泄私人之憤,既解決了問題,又使諸侯歸心于齊。
蘇轍在《論語拾遺》中指出:“管仲相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仁人之功也。孔子以其功許之矣。然而三歸反坫,其心猶累于物,此孔、顏之所不為也。使顏子而無死,切而磋之,琢而磨之,將造次顛沛于是,何三月不違而止哉!如管仲生不由禮,死而五公子之禍起,齊遂大亂,君子之為仁,將取其心乎?將取其功乎?二者不可得兼,使天相人,以顏子之心收管仲之功,庶幾無后患也夫!”[7]
蘇轍還稱頌管仲“臣聞管仲治齊,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他認為在非常復雜的歷史環境下進行各種改革時,管仲能夠公平果敢地處事,盡管不能不得罪一些人,但都是為了齊國的強軍富民,所以能使得天下歸心、君臣相得。可見,蘇轍非常肯定管仲的政治才能。
(三)批評管仲沒有考慮到他與桓公死后的齊國興衰
蘇轍對管仲的評價深受其父蘇洵的影響。與蘇洵一樣,蘇轍認為齊國的沒落與管仲不無關系。但是,他認為管仲的失職不僅僅是沒有除去桓公身邊的三個小人,更重要的是沒有精心為桓公作身后計。在《管仲論》中,蘇轍指責道:
管仲身有三歸,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而不以為非,此固適(嫡)庶爭奪之禍所從起也。然桓公之老也,管仲與桓公為身后之計,知諸公子必爭,乃屬世子于宋襄公.夫父子之間,至使他人與焉,智者蓋至此乎于乎,三歸、六嬖之害,溺于淫欲不能自克,無已則人乎!《詩》曰:“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四方且猶順之,而況于家人乎?[8]
蘇轍和蘇洵一樣,都在分析史實方面比較深刻,都看到了歷史發展的必然因素。蘇洵認為功有所由起,禍有所由兆,所以把齊國大治歸功于鮑叔牙,把齊國大亂歸罪于管仲。蘇轍在分析管仲臨終之言后,認為小人存在是齊國后來大亂的主要原因,但更重要的是自身的問題。他認為,管仲和桓公有共同的缺點,那就是“溺于淫欲而不能自克”,所以無法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把自己都解決不了的問題委托給外人宋襄公,怎能不導致齊桓公死后諸子爭權,死而不得葬的悲劇結局呢?
蘇轍嘆息道:“管仲知小人之不可用,而無以御之,何益于事?內既不能治身,外復不能用人,舉易世之憂,而屬之宋襄公,使禍既已成,而后宋人以干戈正之。于乎殆哉!昔先君之論云爾。”[8]
我們已批評了蘇洵論管仲中的偏頗之處。蘇轍再引先君論,而忽視了管仲推薦隰朋的史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