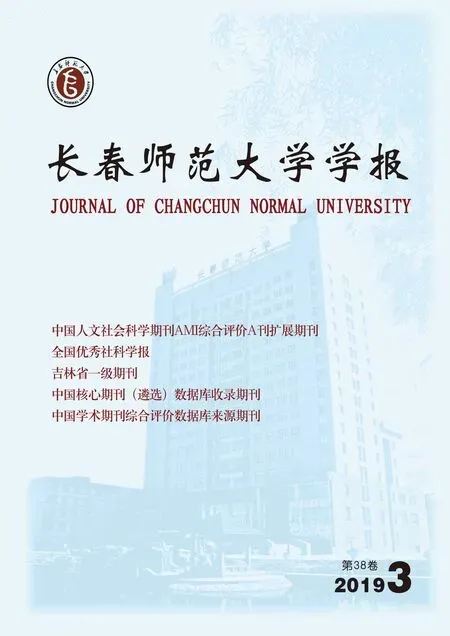精英化與密集型:民國浙江華僑國內捐贈實態
徐華炳
(蘇州大學 社會學院,江蘇 蘇州 215100)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浙江華僑的規模和經濟實力不斷增強,他們在慈善捐贈[1]領域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1979—2009年,“浙江籍僑胞和港澳同胞在全國累計各類物產捐贈折合人民幣135億元,約占全國華僑捐贈總額的六分之一。”[2]而當下海外浙江人秉承濃厚的愛國愛鄉、維系桑梓之精神,是有其歷史基礎的。民國時期的浙江華僑華人就積極關心家鄉發展、關注鄉民福祉,或捐資助學或扶貧賑濟,或海外募捐或在祖籍地設善堂,其慈心善舉有效地助推了浙江乃至全國慈善公益事業。
一、民國浙江華僑捐贈群體
民國時期,旅居世界各地的浙江華僑雖從事職業不同、生活水平不等,但無論自身經濟狀況如何,都盡其所能地為祖國和家鄉做貢獻,積極參與國內捐贈事業。華僑精英、僑團華社和普通僑民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同構成民國浙江華僑捐贈主體。
1.華僑精英:捐贈巨擘
“僑領作為精英人物是時代呼喚的結果,亦是時代造就的結果。”[3]民國時期出國的浙江人雖大多出身貧苦,但也有些創業成功者。旅居日本的吳錦堂、張靜江、林三漁,旅居南洋的胡嘉烈、鄭銘巖、李基中、陳岳書,旅居歐洲的王志南、任巖松等即為僑界精英。這一群體不僅具有海外華僑普遍存有的愛國愛鄉情懷,而且憑借自身的經濟實力以及在華僑中的影響力和號召力,領頭行善,繼而成為民國時期浙江華僑返鄉捐贈的楷模。
民國浙江僑領國內捐贈不但數額較大,而且具有連續性、長期性特點。如旅日僑商吳錦堂一生從事慈善公益事業,“10次救濟長江水災難民,又為東三省、直隸、云南、濰徐、廣東、浙江慈溪等地災荒賑濟”[3],僅1912年就分別向上海軍政府、寧波軍政府、中國紅十字會以及寧波三北沿海嘯災區捐贈白銀2.66萬兩,銀元4.4萬余元;[4]1910—1914年,他先后捐資28萬銀元在家鄉創建錦堂學校。旅巴西僑領周繼文1937年捐資5萬銀元擴建家鄉師范學校校舍,旅新加坡僑領李基中1938年募捐約9萬銀元購置家鄉小學校產。旅新加坡僑商胡嘉烈則不僅在1943—1949年間每年資助家鄉建設兩所小學,更是在祖籍地設立專門慈善機構——片云堂周濟鄰里。為了確保該善堂的運行,他一方面從新加坡寄來外匯確保善款,另一方面將其國內企業——上海立興申莊作為賑濟經費來源。片云堂的扶貧濟困范圍雖局限在寧波一帶,但其開展社會救濟持續20年之久(1941—1962年),一定程度上保障了鄉民的日常生活生產和地方社會穩定,有效地彌補了當時政府社會保障的不足。“至今,胡家墳、花園村兩地40歲以上的人提起此事,都贊不絕口,稱他是故鄉的‘及時雨’”。[5]
2.僑團華社:組織得力
身居海外的華僑為了聯絡鄉誼、團結互助,往往會組建血緣性、地緣性或業緣性僑團華社。近代中國國際地位低下,更促使在異域艱苦創業的華僑結成各類團體,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如日本中華會館(1907年創立)、留日寧波同鄉會(1922年創立)、中華旅日寧紹同鄉會(1922年創立)、浙江溫州旅日同鄉會(1923年創立)、新加坡溫州同鄉會(1923年創立)、新加坡寧波同鄉會(1934年創立)、荷蘭華僑抗日救國后援會(1937年成立)、旅意華僑工商聯合會(1946年創立)、荷蘭甌海同鄉會(1947年創立)等。這些以浙江華僑為主的僑團不僅為華僑社會的利益服務,貢獻當地社會,而且積極參與祖(籍)國發展,開展國內慈善公益事務。
一些浙江籍僑團,如成立于1929年的美東三江公所明確“以慈善事業為主開展各項活動”[6],在號召、動員海外華僑參與國內捐贈過程中更是不遺余力。當獲悉國家遭難時,從負責人到每個成員都會迅速行動起來,借助僑團的社會影響力和個人的社會資源,宣傳鼓動、籌募資金,聯系國內、匯贈財物。在抗戰期間,浙江籍僑團還專設募捐委員會或救國會進行籌賑活動,如“南美洲抗日救國會”及“華僑募捐委員會”。該兩會會長周繼文不但傾己所囊,先后帶頭捐款捐物、購買救國公債券,而且四處奔走宣傳抗日,發動僑胞捐資救國。[7]
3.普通僑民:善小而為
民國浙江華僑除浙北寧波籍華僑屬于較為富裕的僑商,占比居多的浙南青田、瑞安、永嘉籍華僑基本為謀生型僑民。他們沒有充裕錢財或較高社會地位,但始終心系祖國和家鄉變化,在為國為鄉的捐助義舉中同樣不落后。盡管僑界普羅大眾捐贈數額不大,捐贈的影響力亦不如僑領,但在地方史志、僑刊鄉訊和海外華媒中,他們的點滴愛心仍有資可查。
據《青田縣志》記載,1941年“山口鄉石雕外銷中斷,鄉民經濟窘困,糧食奇缺,被迫自縊、投水者不少。山口鄉旅美華僑及旅滬同鄉,應鄉里士紳電請,集資10500元,購番薯干、大麥、大米,急施救濟。”[8]荷蘭華僑手抄辦刊的《抗戰要訊》每期都刊登為祖國抗戰捐款捐衣者名錄,其中有不少來自浙南地區在歐洲各地提籃挈賣的小商小販和從事“三把刀”行業的底層華僑。
二、民國浙江華僑捐贈渠道
民國時期,限于社會發展水平特別是通訊和交通的制約,以及世界的不穩定局勢,浙江華僑開展國內捐贈不可能如當代便捷與多元化。整體來看,他們主要通過官方機構、民間團體和個體自發三種渠道參與祖(籍)國慈善公益事業。
1.個體自發:最直接的捐贈途徑
個體自發捐贈是指華僑以個人名義或委托親屬向受助對象直接捐款捐物。如溫州地區較早捐資興學的代表人物旅新加坡華僑李基中,就是“通過向家鄉的親戚李信甫匯錢,并由其代辦捐贈事宜”[9]。但受制于上文所述社會經濟條件,浙江華僑大多是在回鄉探親時或是從親友來信中獲悉祖籍地的捐贈需求,這使得他們的直接捐贈金額相對較少,并且存在偶然性、隨意性和不連續性等特征,從而影響捐贈對象的受益效果。如旅新加坡的平陽籍華僑王叔旸在20世紀30年代向金鄉一小捐500銀元籌建西樓并贈送圖書,后時隔十余年才又捐資該小學建造一座教室。[9]
2.民間組織:最常態的捐贈途徑
民間團體捐贈是指華僑或僑團將海外募集的善款物資通過同鄉會、宗親會、善堂善會、紅十字會等民間團體組織,轉贈國內的受助對象。晚清民國時期是中國社會由封建形態向近代化轉型的重要階段,傳統的善堂善會和西方嵌入的公益組織交相輝映、異常活躍,成為海外華僑參與國內捐贈的最常用平臺。
民國時期,國內眾多慈善團體和公益組織中都可見浙江華僑的身影。其中,兼具國際性和區域性的中國紅十字會更是浙江華僑捐贈的重要載體。如吳錦堂曾多次通過中國紅十字會、寧波旅滬同鄉會、寧波教育會、盲啞院、孤兒養育院、同仁會、寧紹義賑會以及掖濟會等民間團體機構向國內捐贈款物。周繼文抗戰期間也通過中國抗日紅十字會捐贈救護車一輛[7],長期任新加坡三江會館慈善互助信托人的胡嘉烈更是借助該機構“積極開展會務和慈善活動”[10]。抗戰期間,李基中積極參與陳嘉庚發起成立的南洋華僑籌賑祖國難民總會,“動員僑胞們捐款捐藥,解決了祖國非常時期的許多實際困難,并動員了很多華僑青年歸國浴血戰場,驅逐日寇。”[11]
3.官方機構:最重要的捐贈途徑
官方機構捐贈是指海外華僑或僑團向中國駐外使領館或國內其他黨政機構的海外聯絡部/派駐機構捐款捐物,委托此類官方機構匯款郵寄國內,再轉由國內的黨政機構或民間組織分發捐贈款物。由于近代中國社會長時間動蕩,個人開展捐贈活動非常不易,民間組織捐贈亦難以持久,加之受中國傳統慈善活動多半由官府主持或“官助民辦”模式的影響,借官方力量開展國內捐贈仍然是民國浙江華僑的首選方式。毋庸置疑,浙江華僑采取此途徑實現捐贈,也存在獲取官方認可、表彰和其他政治訴求的心理。如吳錦堂因樂捐而曾先后獲得光緒帝、黎元洪和孫中山的贈匾和嘉獎。[3]
這種捐贈渠道在抗日戰爭時期尤為普遍,一則是出于支援祖國抗戰的需要,二則是為了解決因戰爭而中斷的國內外郵路問題。如旅菲律賓青田籍華僑鄭銘巖1938年將義賣款3018.05元攜帶回國,分別通過浙江省政府、浙江省賑濟會和受傷將士辦事處捐贈,以慰勞前線抗敵將士、救濟難民,浙江省政府亦因此向其頒發“義溢瀛寰”匾額予以嘉獎。周繼文在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欲通過郵政海運匯款給家鄉中學興建校舍,但當時中巴(西)唯一海運通道被阻隔。為此,“每月由他支付給總領館開支費用,再由總領館每月將這筆錢的數目電告中國外交部,外交部再將這筆錢匯給青田阜山中學以資辦校”。
上述三種捐贈渠道各有特色,民國浙江華僑或僑團也沒有固守某種方式,而是以便利、暢達為原則,擇取一種或多種途徑,及時向親友、鄉里、災難民和政府捐輸財物。如“為了支持家鄉抗戰期間的兒童啟蒙教育,李基中多次通過各種渠道給青街小學董事會秘密匯款,幫助積累資金購置田畝,以佃租發放教師工資,作為學校辦公費用。”[11]
三、民國浙江華僑捐贈領域
民國時期浙江華僑既為家鄉的各種社會公益事業出資捐物,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鄰里鄉族的生產生活狀況,也積極參與祖(籍)國因戰亂、災害等引發的難民災民救濟,以減緩當時政府的救助壓力。他們的捐贈主要流向基礎設施、捐資興學、醫療衛生以及各類政治性捐獻方面。
1.基礎設施
無論是造福一方,還是留名地方,出資造橋筑路、建亭修塔、興修水利等是包括民國浙江華僑在內的老一代華僑維慈與善的首選。翻閱浙江各區域志,華僑捐建祖籍地基礎設施的事跡頗為詳贍。如青田籍僑商吳乾奎1927年回國后,“先后助資修建橋3座、路4段和奇云山石廟1座”;1929年還購買“麗、青、溫公路”股券8000塊銀圓,時任青田縣長鄭邁題贈其“惟善為寶”匾額。[12]民國初年,吳錦堂“在家鄉慈溪興修杜湖、白洋湖,疏浚四浦,筑橋設閘,使慈北20萬畝農田受益。”[3]1947—1949年間,胡嘉烈不僅捐資修建妻家所在花園村的兩座危橋和村中道路,而且以前瞻性理念出資購買兩臺機器水龍,分贈胡家墳、花園村,以改善村中消防設備。[13]
2.學校教育
民國浙江華僑尤其是浙南山區華僑,因家境貧困,受教育機會甚少,在海外謀生創業過程中時刻遭遇文化程度低下的窘境。這種切身體悟本能而強烈地驅使他們待機改造鄉村教育,以改變家族子弟命運。日本“高薪聘用大批外國教師,在短期內迅速培養出本國人才的做法,以及民間那種‘雖販夫走卒,無不勤學讀書’的社會風氣”給吳錦堂留下很深印象。[4]他說:“近世列國爭強,要在世界上立足,教養二事很重要,國民失養,就無以為生,國民失教,就難以爭存。”[4]于是,他事業有成后熱心家鄉教育事業,歷時三年耗資23萬多銀元興辦了具有先進教育設施和新穎教學理念的錦堂學校,培養出包括陳之佛、沙孟海等在內的大批優秀人才。1907年,他向寧波府教育會、寧波效實中學捐資3000銀元。同樣,周繼文“深知祖國總是受外國欺侮,是因為教育落后、科學落后,而導致國家落后,以至喪權辱國受挨打。”[7]因此,他于1937年出資五萬銀元擴建青田中學校舍,1941年又捐資興建祖籍地唯一一所中學——阜山中學。
民國浙江華僑興學助教范圍雖受中國傳統觀念影響而集中在祖籍地,但捐資助學的具體形式并不單一。除直接捐資,他們或捐田地置校產或購置教學用具。如陳紀林1927年捐田30畝,重整村校校舍,創辦培本學校。[14]李基中1938年為青街小學購置操場,購買樂器、風琴、運動服以及6張辦公桌和部分學生桌椅等校產。[15]胡嘉烈依據受助學校實際需要,在戰爭紛亂的1943—1949年捐贈15000斤稻谷作為文山小學的開支經費,可謂用心良苦。吳錦堂捐資創辦學校的方式更是獨具特色:一方面,他出資辟地建校舍、購買圖書設備,廣求賢才、重品德教育,以致錦堂學校被時任浙江巡撫稱為“浙江私立學校之冠”;另一方面,他既著眼實業教育,為地方經濟建設服務,又出資選派優秀學生出國留學。因此,吳錦堂與陳嘉庚、聶云臺一并被蔡元培評論為中國“辦學三賢”。民國浙江華僑興學育人的善舉,不僅為貧寒子弟提供了較為完備的教學條件,增進了浙江鄉村文化建設,而且成為當時及其后華僑報效桑梓的良好示范。他們捐資創辦的新式學校既為地方社會培養了更多實用型人才,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浙江教育的近代化。
3.醫療衛生
擁有基本的醫療衛生保障,是生活在跌宕起伏的民國社會的每位民眾最大的訴求甚或奢望。一些浙江華僑耳聞或目睹了國內特別是那些偏遠、閉塞地區的落后醫療狀況后,從關心、呵護族里鄉鄰身體開始,積極扶助、改善家鄉醫療衛生事業。如20世紀20年代,青田華僑林晉卿多次托人樂捐永嘉普安施醫施藥局。1929年,青田籍旅美華僑金美齋資助1000銀圓籌建縣立醫院,獲得時任縣長鄭邁書贈“急公好義”匾額嘉獎。1936年2月,青田旅美華僑林晉南回鄉探親,攜來藥品多種,治病救人。[16]抗日戰爭時期,胡嘉烈也積極捐贈寒衣和醫藥。
4.政治捐輸
民國38年間,政局動蕩不已,革命、內亂、戰爭接連不斷,有識之士上下求索,尋求國家獨立和民族解放。華僑身居海外,更盼革命成功。為實現民族民主革命的勝利,他們竭盡所能地給予支援。民國浙江華僑支援國內革命事業的巔峰,與全體海外華僑支援祖國抗戰的高潮是一致的。
抗戰期間,浙江華僑尤其是僑領們積極響應,組織募捐機構,踴躍捐款捐物,甚至直接回國投身疆場。“青田籍華僑陳則敬,看了保衛上海四行倉庫抗日記錄片后,激于愛國義憤,向中國駐法領事館領取一本100頁的救國捐獻單據,在幾天內動員100人募捐數千元”[17]。旅法青田華僑集居的巴黎里昂車站區和哥魯梅驛區僅在1938年前10個月就捐獻出4.1157萬法郎。浙江華僑不僅以捐資助餉、購買國債、捐獻戰時物資等直接捐贈形式支援祖國抗戰,而且采取義賣義演等方式多渠道籌募抗戰經費。如溫州籍旅新加坡華僑陳時權、陳崇龍和林元山等在僑居地組織賣花隊募集經費,旅捷克華僑朱祥謄寫、義賣《抗日戰》開展抗日募捐,等等。
此外,浙江華僑積極參與各地賑災等其他社會公益活動,并力所能及地為地方社會安定發展獻策獻力。如吳錦堂看到寧波一帶不少村民因沉迷賭博而放棄農業生產甚至傾家蕩產,就捐款支持地方政府禁賭,以安定家鄉生產生活。“1910年到1915年間,吳錦堂多次連續寫狀紙,稟告縣知事,要求嚴禁花會,并出資1600銀元,作為緝捕花會頭子沈阿洪等賞格。”[18]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浙江華僑尤其是在海外行商成功的僑商,出于祈求心理而向地方佛堂寺廟捐贈財物,形成一種特殊的捐贈行為——宗教慈善。如吳乾奎曾捐款給當地的奇云山佛殿、阜山耑堂、垟心佛殿和垟心宮。1938年,旅居馬來亞、新加坡的胡遇仁等83位瑞安籍華僑捐助333.5銀元修建玉壺三港殿前殿,胡遇商等38位華僑捐助68銀元修建后殿等。
四、結語
民國時期雖“國未泰民不安”,浙江華僑在僑居國也多磨難,但依然向祖國表達了拳拳赤子心。1923年,民國政府內政部為16位“辦賑出力暨捐助賑款”的浙江華僑與僑務工作者頒發獎勵。歷史事實證明,民國浙江華僑的國內捐贈對象雖以具有地緣血緣關系的鄉鄰為主,捐贈款物集中流向革命性/政治性捐獻,但仍不失為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特別是民間慈善公益事業發展的有生力量。1949年后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國內政局逐漸平穩,社會日益安定,捐贈已成為浙江華僑的生活常態,華僑慈善公益已成為中國社會進步的有效資源,成為中國形象的重要標志和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