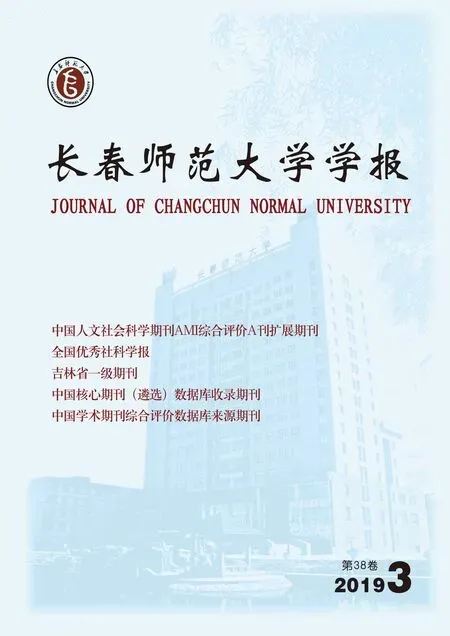清末小說《俠義佳人》的現代女性意識探析
來迪娜·吐爾汗江,劉 釗
(長春師范大學 文學院,吉林 長春 130032)
“啟蒙是清末思想界的主要話語形態”[1],被歷史遮蔽的閨閣女子繼而被推上歷史舞臺,成為“被啟蒙”和先行覺醒的女性群體。1902年,梁啟超以啟蒙民眾為目的,提出“小說界革命”,強調小說的熏、浸、刺、提功能,使小說從“稗官”“小道”登上文學的大雅之堂,成為改造社會、新民救國的有效工具。在“新小說”的帶動下,清末涌現出一批宣傳婦女問題的小說,如頤瑣的《黃繡球》、思琪宅的《女子權》、王妙如的《紅閨淚》(又名《女獄花》)等20余種[2],反映了當時的女權啟蒙思潮。阿英早在1937年出版的《晚清小說史》中就提出清末婦女問題小說這一重要文學現象,新世紀也有學者指出,“晚清民初是‘女性小說’真正興起的時期”[3]。但以男性為主導的清末啟蒙文學大潮中涌現的女性小說作者在以往被忽視,較早引起學術界關注的僅有顧太清、王妙如和邵振華三位[4],如今被挖掘并得到關注的該時期創作小說的女性作者已達60余人[5]。她們從女性情感經驗、身心感受、思維方式與觀察視角出發,記錄清末女子的生活風貌,彰顯出女性小說創作特有的藝術魅力。對她們的小說創作進行深入研究和重新闡釋,必然可以打開清末小說創作的一個新視界。其中,四十回章回小說《俠義佳人》是現存清末女性創作的小說中篇幅最長的一部[6],尤其應該得到重視。
《俠義佳人》的作者為邵振華[4],是一位家庭主婦。小說出版時署名“績溪問漁女史”,分為初集二十回、中集二十回,先后于1909年4月和1911年7月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未見下集。較同時期婦女問題小說傾向于烏托邦想象來說,《俠義佳人》更注重從婦女的切身實際入手,揭示當時婦女真實的生活現狀,是一部難得的由婦女自身發聲的長篇小說。
作者在小說自序中言:“睹黑暗而思文明,觀強暴而思自振”[7]86,其創作目的即為以此喚醒婦女、警省世人。小說以孟迪民在上海創立中國女子曉光會為中心,圍繞參加曉光會的女子在山東、江陰、梧城等鄉間各地興辦女學的事跡,展開啟蒙女界的文學主題敘事。作品揭露民間供大仙、拜佛堂、風水算命等迷信行為,反對婦女纏足,批判買賣婢女以及納妾等陳規陋習,鼓勵婦女走出閨閣接受新式教育,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當時社會 上普遍存在的婦女問題。作品中關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的細膩描寫,顯示出女性作者的感同身受,一系列女性形象的塑造展示了當時進步的女性意識達到的程度。
一、孟迪民:摒棄纏足陋習,組織新女學
邵振華在刻畫人物形象過程中,著重描寫了貫穿整部小說的女性形象——孟迪民。她不僅自幼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且好學不倦、志向宏遠,為人和藹仁慈。她以啟蒙女界為己任,在上海創立婦女會——中國女子曉光會。該會以“愛人為本”“一律平等”為宗旨,這與小說中解釋的會名“曉光一線,漸進光明”[7]120意蘊一脈相承。曉光會中女性具有的共同之處在于:不纏足,不撲粉,接受過良好教育,有志女界振興。她們對興女學有極高的熱情,在各種機緣巧合下相遇相知、志趣相投并結成姐妹,在追求理想的道路上相互扶持、共渡難關,體現出中國傳統的俠義美德。她們有很強的集體意識,將女界振興置于個人幸福之上,即使已經成家的高劍塵、孟澹如二人也沒有脫離團體,反而時時參加會中活動。高劍塵的丈夫林飛白作為留學歸國、思想進步的人士更是融入其中,在曉光會的很多活動和事務上伸出援手,給予莫大支持。
小說詳述了孟迪民及曉光會中女子游走于鄉間各村落,引導農村婦女摒棄纏足陋習之時遭遇的諸多困難。小說中女性人物出場時,往往會對女性外貌服飾、腳描寫的筆墨較多,即“不纏足”“不撲粉”成為辨別“新”“舊”女性的時代標志。作者為了讓讀者感知“女人裹腳的壞處”[7]116,時常將穿洋鞋的“大腳”與三寸金蓮的“小腳”女性進行對比,凸顯出放足女子“腳大有勁兒”“站的穩”“行動便利”“有事幫著姑爺做”等利處。孟迪民、高劍塵等知識女性以身體力行啟蒙女界,積極宣傳天足之利。纏足女子花影憐同孟迪民等放足女子一同外出游玩時,唯有花影憐吃了小腳的虧。“走不上半里路,這位花小姐果然走不動了。那雙小小的弓鞋,在石子路上,左一拐右一拐,一點兒不得勁,連身軀都晃晃蕩蕩的搖擺不定。”[7]555花影憐深刻體會到小腳帶來的痛苦,稱自己“是個沒用人”。孟迪民借此耐心鼓勵和引導影憐放足,“影妹慢慢的放大了,將來走起路來,就輕松了。”[7]556除此之外,孟迪民善于辯論,見江家太太與四位小姐仍以“三寸金蓮”為美時,便與江家姨太太展開了關于放足的紛爭辯論。她從婦女自身感受出發,提議小姐們解除纏足痛苦加入天足會,更從生理學強種角度指出纏足之弊:“據說小腳的人臨產,是很吃虧的。”[7]264她向江家太太強調女子作為“國民之母”不僅要解放雙足,還要擔負起強國保種的重任。由此可見,小說借孟迪民之口,表現了清末維新派思想,以強國保種角度摒棄纏足。金天翮在《女界鐘》“女子之道德”一節也提到過胎教與母儀:“將欲孕出健康順遂、聰明偉大、熱心公德、道德名譽之兒乎,其必以胎教之高尚純潔為之基礎矣。”[8]孟迪民希求讓農村婦女懂得纏足對婦女身體和心靈上的戕害,提倡放足不僅是為了改善女子贏弱的身體,更是強國之根本。
孟迪民在伯父伯容出資捐助下,積極興辦女學,成為教育女性的女界啟蒙者。她基于男女教育應平等的認識,在興辦女學過程中更加重視“中西并重的辦學方針”[9]。為了更好地普及教育,她將自己創辦的光明女學分為初等女學堂和高等女學堂,設有自修室數間、講堂十四間、飯廳五間、藏書閣、教習住所、教習會客所、女學生會親友所,針對女學生開設的科目有國文、歷史、英文、算術、體操、音樂。小說著重刻畫了光明女學堂的操場具體圖景:“迪民同劍塵出了院門,偏東來到總會的大體操場,體操場的西南,墻旁邊有一道回廊,回廊外,種的都是梧桐垂楊之類。迪民等沿著回廊走過去,有一八角門,從門中走進,就是光明女學的大體操場。”[7]284這段描述凸顯出孟迪民對女子體操的重視,她希冀通過加強女子體操教育,幫助她們改造贏弱身體。
高劍塵在曉光會上海總事務所開副會長選舉會上演說指出:“女子為教育根本。”[7]220要想使女性有更廣闊的施展才能的天地,就必須使其接受教育,從而擔負起救國救民的責任。高劍塵說她的丈夫林飛白將來要從軍報國,于是對其好友蕭芷芬、白慧琴表達自己身為女子參軍報效祖國的迫切愿望:“我也想約合同志,聯為一小隊,等他們從軍,我們也跟著他們行軍,一同赴敵,替軍人們裹創侍疾,以盡我們女子一份之能力。幸而國家得勝,我們也可重新聚首,做個強國的自由民。萬一國家不勝,他們戰死,我們也決定死于槍林彈雨,以償我們平生之志,以謝我們女國民之責,不是很痛快的事嗎?”[7]381展示了高劍塵作為新女性的愛國意識及為國家不惜生命的英雄氣概。
二、蕭芷芳:追求經濟獨立,謀得自我解放
梁啟超在著作《論女學》中指出國家積弱的根源在于:“女子二萬萬,全屬分利,而無一生利者”。[9]他提倡女子應該有自身職業和自養精神,不能完全仰仗男性供養。《俠義佳人》的作者塑造的新女性形象大多不是置身于閨閣中的家庭角色,而是能夠擔負起社會責任的職業女性。小說中有不少女性形象從事不同的職業,從而謀求衣食,體現出女性經濟獨立的一面。
小說中,重視婦女職業教育的代表性人物為蕭芷芳。蕭芷芳自幼聰慧,性格豪爽,好論是非,不裹雙足。她不僅讀過諸子百家著作,還留學東洋、西洋數年,作者稱贊其是“最自由的女子”。蕭芷芳作為受過教育的知識女性,基于對養蠶技能的科學認識,從農村婦女的生存實際出發,指出嘉興、杭州、湖州蠶業不興,是由于農村養蠶婦女“倚賴迷信風水”“不努力做事”。她力勸義士顏如容的妻子轉變靠迷信風水養蠶的觀念,為其普及養蠶職業技能,提出“靠本事、智慧、志氣”養蠶新法。由此可見,蕭芷芳在女性職業教育上講究對職業知識、技能的培養,對女性的職業教育社會化起到了積極作用。孟迪民見此情形,在蕭芷芳、高劍塵的啟發和支持下萌生出興辦養蠶學校的意愿:“蠶學館房子造兩所,一為男子學的,一為女子學的。女學生畢業就可教來學的女人,派出去演說的不在此數。”[7]510孟迪民希冀改造農村婦女迷信風水的落后觀念,通過興辦實業解決女子的生計問題。除此之外,孟迪民還提出出資興辦手工傳習所、女醫學校的宏偉理想。小說雖然沒有來得及敘述創辦養蠶學校、手工學校、醫學學校的具體步驟,但對孟迪民、蕭芷芳等人的宏大理想給予了肯定。
值得一提的是,女教習是同時期婦女問題小說中最普遍的一種職業。《俠義佳人》中謀求職業的女性,希求成為女教習,從而保障自身生計。花影憐是一位孤兒,家徒四壁,告貸無門。蕭芷芳見此情形,向孟迪民推薦花影憐做光明女學的圖畫女教習,以改善生活處境。花影憐看出蕭芷芳、孟迪民的仁愛之心,心想“是可憐我的境遇,要把我拯救出去。”[7]546此外,小說中具有自主意識的馬秀貞本是一名學校的手工教習,但為了謀求更高薪水的教習職業,在擔任小學堂教習的男性好友鄒國才的幫助下,成為每月薪資二十元的興華女學校手工教習。馬秀貞在和鄒國才的談話中透露出她十分重視職業薪資,在經濟方面體現出女子通過擔負社會責任獲得相應報酬的期許。
《俠義佳人》中貫徹著“女性自身價值”這個詞,主要表現在女子職業工作范圍的擴大,從女工到女教師、女醫生、辦報者等,都能看到女子的進步軌跡。小說《俠義佳人》中誕生了多種職業角色,最多的女性職業是在女子學校擔任國語、手工、地理等女教習,如白慧琴、黃汝真、汪則古、黎心如、鄧冠亞、木本時、花蓮影、柳飛瓊等。另有經濟完全獨立的擔任曉光會的會長孟迪民、擔任啟明女學堂書記的田芷芳、顧問員高劍塵。小說中還有辦報者、督查員、接待員、庶務員、裁縫等一系列女性職業。小說中最特殊的女性職業是同期小說中未涉及的女性形象,以種植蔬菜、養魚、養羊自食其力的實業家孟澹如。總之,作者借助蕭芷芳、高劍塵、孟迪民等眾多知識女性展示了進步的女性職業觀,表示女性同男性一樣可以走上社會,從事各種職業(教習、醫生、主筆等)來實現自身的價值。
三、柳飛瓊:婚姻自由是婦女人格解放的根本
在封建社會,男女青年幾乎沒有婚姻自由。“清末民初的知識女性是從古代才女‘待字閨中’到五四新女性‘出走尋愛’形象之間的過渡人物,正是‘自由結婚’的漾漾波紋和這些過渡女性,為呼之欲出的五四時期女性倫理建構的黃金時期的到來奠定了基礎。”[11]從邵振華創作的小說來看,生活在家庭和社會中的女性形象自主意識有了初步的覺醒,進而在不幸婚姻和卑微家庭地位中開始了自我抗爭。小說中有部分女子依舊選擇自殺方式結束痛苦的婚姻生活,也有少數女子通過自由戀愛、離婚等方式掙脫封建婚姻制度。
芳顏如玉的柳飛瓊是一位無父無母的孤兒。在女學堂受過教育后,“生得且有滿腔自由血”,向往自由婚姻。柳飛瓊在一次留院閑逛、喝茶賞花之時,邂逅衣著華麗、相貌出眾的男子楚孟實,便對他一見鐘情。飛瓊與楚夢實相識之初,夢實對飛瓊關懷備至,極其殷切,花言巧語騙取了飛瓊的愛慕。兩人很快便私自成婚,在上海同住。結婚三四年后,楚孟實喜新厭舊的惡劣本性慢慢暴露出來,他將飛瓊騙送回湖南老家后,飛瓊才發現他早已娶妻。她在楚家受盡大婦虐待,還險些被賣掉。幸而得到自己妹妹的同學也是楚家親戚的女學生馬憐吾幫助,方得脫離虎口。后得曉光會眾人幫忙,順利與楚夢實離婚。柳飛瓊從大膽追求建立在愛情上的自由戀愛,到為了人格尊嚴“情愿離婚”,展示出女性自主意識的初步覺醒。作者借柳飛瓊形象,一方面倡導“離婚”是女性掙脫不幸封建婚姻束縛的直接有效方法,另一方面警醒女性不要為情所迷,對男子納妾行為予以譴責。
在清末新舊觀念交替的時期,作者描寫了選擇單身婚戀觀的女性形象白慧琴。作為留洋歸國的“女志士”,白慧琴在與已婚的高劍塵閑談時表達了自身對婚姻的看法:“依我說,要想來去自由,還是不嫁的好。我常見有好些不滿意的夫妻,終身怨恨,都是從這專制婚姻上來。弄的做人家一輩子的奴隸,自己一豪樂趣沒有,那才是枉生人世呢。”[9]408持單身婚戀觀首先是對封建婚姻的一種抗拒,其次是為了更好地實現自身的社會價值。同時期小說《女獄花》中“著書醒世”的文洞仁,面對婚姻也持單身態度。而白慧琴見江陰縣城中男學堂居多,女學堂卻無一所,于是堅定“扶持女界”的信念,捐出部分私宅,克服種種苦難,創辦啟黃女學堂,期望女子都能走出閨門接受教育。由此可見,白慧琴身上體現了仁愛濟世的精神特質。文洞仁、白慧琴的女性形象與清末女界人物張竹君極為相似。張竹君不僅持單身婚戀觀,且從事醫生、辦學者、經商多份職業。她更加注重女性自身存在的社會價值,是當時維新人士梁啟超、馬君武推崇的女國民典范。
四、結語
《俠義佳人》發表于民國成立前夕,“表現了近代女性的覺醒,形象地為婦女解放、提高女權指出了前進的路標”[5]4,代表了現代女性意識的萌發。小說中通過描述追求天足、興辦女學的女性感同身受的經歷,突破了男性啟蒙家們空洞的理性說教。然而幾千年來根深蒂固的“男主外女主內”觀念不僅剝奪了婦女參與社會公共領域生活的權利,還潛在地剝奪了婦女在家庭中的自主地位。在西學東漸的文明追求中,戀愛自由與婚姻自主使婦女從精神上求得解放成為可能。邵振華作為一位女性作者能夠接受當時比較“新潮”的婚戀觀念并在創作中表達自己明確的觀點,是難能可貴的。雖然《俠義佳人》中表達的思想觀點并沒有超越時代和當時啟蒙文學的主題,但正因它出自一名家庭主婦之手,才表達了女界啟蒙所到達的程度和婦女主體意識的初步覺醒。這恰恰是一個由傳統走向現代的社會轉型期女性小說文本透露出來的深刻的文學審美價值和社會進步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