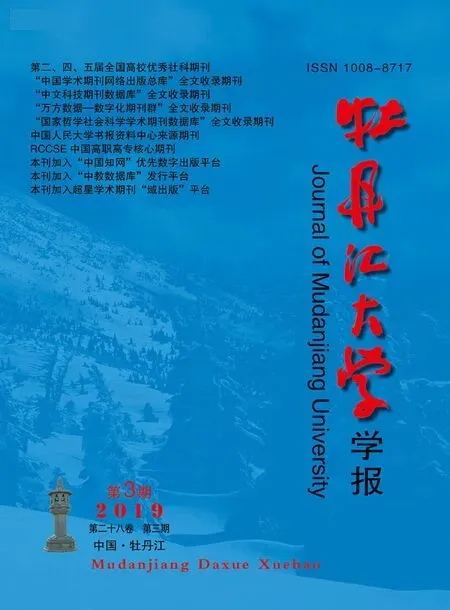文本理解:過程機制與路徑解析
——以詩歌《跳蚤》為例
吳 亞 軍
(1.云南師范大學 外國語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2.西南大學 外國語學院 重慶 400715)
文本理解是篇章教學的核心環節,受多方因素的綜合影響。艾布拉姆斯指出,對作品的釋解要同時考察文本作者、作品、世界和讀者這四個方面的因素。[1]在眾多因素的作用下,不同讀者對同一文本可能會產生不同的經驗感受,體現出文本理解過程中意義釋解所存在的巨大張力。這并不意味著對文本的理解是任意的,相反,這四方面因素所體現出的時空特質對文本意義的釋解同時發揮著一定的導向、規范作用。文本理解過程所關涉到的四因素既體現出異質性又體現出規約性。如何綜合考量這四方面的因素,又該如何解讀四因素體現出的兩種看似矛盾的功能屬性?這是有待深入探討的問題。
心理空間(mental spaces)作為關聯概念的集合,是對意義生成的過程機制進行闡釋的場所。福克納(Fauconnier) 和特納(Turner)提出的概念整合理論[2](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則以心理空間為基本單元,在心理世界層面通過對概念間作用機制的說明來闡釋意義的生成機制。有鑒于此,本文首先回顧概念整合理論的內容及其在意義生成中的解釋功能。其次,探討概念整合理論在文本理解的應用,通過建構文本理解時的概念網絡提出文本理解的一般路徑。最后,以玄學派詩歌《跳蚤》的解析為例,驗證了文本理解是前理解知識、文本信息及概念化主體等三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概念整合理論與意義生成
美國學者福克納在1985年首次提出概念整合理論以來,有關該理論的內容探討及應用研究在越來越多的領域中開展起來。通俗地講,概念整合是指不同的心理空間之間的投射與整合。作為概念整合理論中的核心概念,心理空間是指“人腦感知、想象、記憶或思維時無意識地用來組織后臺認知運作過程的手段”[3]。最典型的概念整合模式包括有四個心理空間:兩個輸入空間(input spaces),一個類屬空間(generic space)和一個合成空間(blended space)。其中,類屬空間內的信息為兩個輸入空間所共享,是兩個輸入空間之間能夠發生映射的動因,而輸入空間發生投射與整合的結果是合成空間的生成。在綜合已有的概念整合理論研究基礎上,本文認為類屬空間內的知識性信息主要體現為在象似、類推等認知過程中所形成的程序性知識(procedural knowledge),在功能上與合成空間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因果關系。同時還需要強調的是,合成空間內的信息內容并非簡單地等價于兩個輸入空間內信息之和,而是格式塔心理學意義上的“整體大于部分之和”。即,兩個輸入空間在合成時有了“新質的實現生成”[4]。

圖1 概念整合理論模型
從認知語言學角度看,概念之間映射的結果所呈現出的語義結構可以用來闡釋意義的生成過程與意義存在方式。概念整合理論模型中,輸入空間的整合過程中發生映射的部分體現為信息的擇取與層創結構(emergent structure)生成。而未被擇取的信息,如圖 1 Input1 中的 c, d 及 Input2 中的 f, e由于未能發生映射而逐步消退。人們正是通過體驗概念的合成過程及結果而形成一定的語義結構,在內容上則表現為對闡釋對象所映現的意義的體認。
二、概念整合理論下的文本意義的釋解模式
(一)文本與文本理解
文本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人工物。有關文本的認識會受到釋解者的語言世界觀影響,因此有必要首先對本文所持的語言認知觀進行交代。人工物(artifact)是指非自然的人類產品,是由人類設計并制造出來的存在。[6]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質意義外,人工物主要是通過引起人類覺知上的變化來體現其意義。語言是在人類的實踐過程中所產生的,是人類社會文化活動的產物。從功能角度看,語言可以被看作是一種特殊的社會人工物。文本是作者作品的實體化表現形式之一,是以語言文字為主要媒介而實現對作者思維活動的表征。在人的大腦中,由于“思維被貼上概念的標簽”,讀者可以將文本看成是啟動人類覺知器官并產生概念意識的刺激物(stimuli)。海德格爾指出“語言是存在的家園”[7],也只有通過語言這一媒介概念世界才能實現語義化表達,這也再次說明了概念的映射只有通過形諸語言事實才能為人們所認知和理解。
文本理解活動應遵循概念認知模式的在線處理(on-line processing)和語義語境的動態建構原則。文本的存在與讀者的鑒賞活動是分不開的,只有通過人們的不斷解讀某一文本才能延續其生命的活力。在文本的理解過程中,由于讀者同時受到作者、文本、特定時空下的世界和本我等四方面因素的影響,不同的人對同一文本的理解會因上述因素的差異而產生不同的認知結果。即使是同一個人在不同的時段對同一文本賞析其意義感知也會不一樣。[8]可以得知,文本的語義內涵遠大于其文本所承載的語詞概念內容。這也要求讀者在文本理解過程中,以實時信息為基礎并結合釋解語境的動態性來實現對文本的綜合理解。
(二)文本理解中的概念網絡構建
文本的理解過程具有突出的動態性特征,體現了語義釋解的無限可能性。首先是在句法層面上對文本中語言信息的把握,同時,連同作者信息、讀者意識中所凸顯的世界知識等內容在釋解者的意識世界里進行整合與呈現。此外,由于人們所解讀的文本意義是以意義表征的形式儲存在記憶中的,在讀第二遍的時候,第一遍閱讀時所形成的意義表征就已經能夠對其意義理解產生影響了。如赫拉克利特在《河流殘篇》中說,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人們對于文本的理解也不可能完全等同,[9]這意味著讀者對文本的認知與理解具有極大的動態性、靈活性。麥克道威爾持類似的觀點,認為主體通過感知獲得的信息狀態(information states)具有自發的概念內容,加之主體對該信息狀態的判斷形成概念性的經驗內容。[10]可以看出,文本理解過程中的意義構建表現出了無限的解讀可能性。
意義是思維過程的產物,以概念網絡的形式體現為系統的語義知識,并通過語言得到顯性的表達。錢冠連提出的語言全息論 (the theory of language holograph)指出,應該從語言單位所承載的信息角度來看待語言系統中的部分與整體之間所體現的全息性,即“一個詞可以推衍出一個數字龐大得驚人的集合體,幾乎是詞庫里所有的詞”[11]。根據語言全息論,文本中的每個語言單位在理論上都可能會形成無界的、復雜的語義網絡(semantic network)。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在對文本的理解過程中主體思維可以以任意的認知模式來釋解文本中語詞意義,因為“思維和語言存在著一個思維無限生成性和語言規則系統的有限性的矛盾”[5]。因此,文本理解在實質上可以看作是思維的無限可能性與線性文本的有限性之間的辯證互動過程。具體體現為,構成文本的各層級語言單位所形成一個個語義網絡在釋解者的大腦中通過概念整合實現了概念的整合或消解,而最后的認知結果則體現為讀者對文本的意義理解。
(三)概念整合理論下文本的范式解讀
范式(paradigm)是科學哲學中的重要概念,是由科學知識社會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庫恩(Thomas S.Kuhn)首先提出的。庫恩認為“科學盡管是由個人進行的,科學知識本質上卻是群體的產物”[12]。在內容層面上,范式實質上是指公認的程序性知識,其功能是在一定的時間內能夠為個體的實踐提供典型的解決思路。[13]從哲學闡釋學的維度看,范式的公認性體現為集體中的精英團體所達成的共識。這部分內容是以“前理解知識”(preunderstanding knowledge)的形態儲備在人們的記憶當中。“前理解知識”為語言釋解活動提供索引,對詩體賞析時基調的選擇發揮導向作用。換句話說,支配并組織文本理解的主體并非僅僅是讀者,在更大程度上受讀者所在特定語言共同體的集體性心理、認知特點的制約。因此,詩歌文本作為客體性存在,只有遵循著一定的范式人們的解讀活動才具有對話性屬性,進而體現出主觀釋解的合理性。
文本的語義信息作為一個輸入空間,范式性質的信息作為另一個輸入空間,那么文本理解過程就體現為這兩個輸入空間的整合。在此過程中文本信息與范式信息進行匹配選擇,兩者能夠匹配即表現為類屬空間的信息內容,而解讀者理解過程結束后在大腦中所產生的意象群(image group)則體現為合成空間中的內容。心理空間之間的相互融合與消解以語義網絡的形態存在,具有無界性(unbounded)或非范疇化性。基于對文本理解過程中的合理性和人文性的雙重考察,本文提出的文本理解模式包括兩個階段:首先,通過了解領域內專家們的研究成果獲得該文本理解的“前理解知識”;然后,結合具體的文本信息實現對文本意義的主觀性認知。在這個過程中,“前理解知識”對釋解者既發揮了規范作用以避免認知主體的任意性又發揮了導向作用有助于認知主體對文本主旨的領悟與把握。
(四)詩歌文本——《跳蚤》的解析
釋解主體的主觀性在詩歌文本的意義釋解過程中能夠得到充分展現,以詩歌為例來驗證本文所提出的文本理解模式具有代表性。以英國玄學派代表人物多恩(John Donne)的代表作《跳蚤》為分析對象,從“前知識理解”、文本信息和概念化主體三個維度展開對文本理解的描寫與闡釋。一方面驗證本文所提出的階段性文本理解模式是否有效,另一方面加深對文本理解中的過程機制的體認。
首先,對文本的理解離不開對作者、詩體風格等“前理解知識”的把握。有關作者生平的研究表明,多恩的人生經歷很“玄”,放蕩不羈的生活中曾因與愛人私奔而獲罪入獄并結束了這段愛情。[14]在詩風上玄學派傾向用隱晦的哲學思辨和奇特的“象喻”(conceit)來解讀多義多變的世界。在文風方面,研究者認為《跳蚤》一詩是以戲劇性獨白(dramatic monologue)的表達形式來呈現的。[15]據此,我們獲得了解讀詩歌文本《跳蚤》的相關范式性信息,即文本理解模式中的“前理解知識”。
其次,對文本信息的分析是文本理解的主體內容。從文本表達上看,全詩共27行,以喻體“跳蚤”為分析視點,每9行構成一節,將全詩劃分為三節。第一節是對愛情中“主體結合”這一意象的表達。詩人以跳蚤為媒介勾勒出一只跳蚤叮咬了詩人之后又叮咬了理想中的愛人,在跳蚤這一媒介體內兩個主體的血液融合在了一起。“前理解知識”的掌握過程中,已有研究主要從喻體選擇這一維度來體現該詩歌文本的玄妙之處。有鑒于此,本文認為該詩歌的“玄”更體現在詩人基于喻體“跳蚤”上的玄妙聯想。本節最后一行“And this, alas,is more than we would do.”(這方面,哎,我們沒做到啊 ),其中的“alas”,“would do”是對通過跳蚤所表達出的“主體結合”意象的否定,流露出作者對在現實中沒能與愛人結合在一起的遺憾,表達了詩人對愛情的自由訴求。第二節是詩人對“跳蚤”這一意象被拍死的不解。在愛情的世界里,詩人自己、對象以及愛情事件本身都將會因“跳蚤”這一意象的毀滅而消失。跳蚤意象是“三位一體”愛情觀的象征,然而卻被理想中的愛人拍死了。懷著這份不解,詩人分析了其中的原因。父母是傳統力量的代表,詩人認為即使父母不同意也可以和理想愛人住在哪怕黝黑的墻院里(cloistered walls),畢竟我們有緣相遇了。在主旨上,詩人鼓勵人們為了愛情敢于同傳統力量作斗爭,勇于為愛情做出犧牲。第三節是詩人對“跳蚤”這一意象被拍死的控訴及吶喊。作為愛情象征的跳蚤被理想愛人拍死了,而非外在因素造成的。當理想中的愛人說到,“Find’ st not thy self nor me the weaker now.” ( 你 我 并沒有因跳蚤的死而虛弱)。這表明這份愛情的破滅并非來自詩人所認為的傳統力量的阻撓,而是理想對象對這份愛情的否定。詩人寫道“Just so much honor, when thou yield’st to me”(接受這份愛,愛情是值得榮耀的)。此時在愛情世界里,愛情本身得到突顯,而詩人及愛情對象的主體性卻消解掉了。鑒于此,詩歌文本的主旨再次得到升華,即使追求愛人無望,我們依舊選擇崇尚愛情。
最后,文本的理解機制體現為概念化主體大腦中發生的概念整合。功能維度上,“前理解知識”對文本理解發揮著規范和導向作用。但“前理解知識”并非一成不變的,而是釋解者通過了解已有研究而不斷整合、建構起來的,體現出“前理解知識”的開放性和建構性特征。在文本理解上,概念化主體一方面受到來自他者的“前理解知識”的規約;同時,概念化主體對文本理解的結果也將進一步地凝結到“前理解知識”當中,對他者的文本理解發揮規范和導向作用。文本的理解中不存在唯一的、科學的解讀方式。不同主體之間的相互制約彰顯出文本理解的合理性,在此基礎上,釋解主體的主觀性又展現出文本理解的人文性。兩者互為條件、不斷融合,進而無限地逼近文本的真實面目。
三、結語
在文本的理解實踐中本文主張從價值評判的兩個維度——合理性和人文性同時進行考察。基于概念整合理論,本文提出文本理解的一般路徑,即釋解者在“前理解知識”的規范和導向作用下發揮釋解主體的主觀性。以詩歌文本《跳蚤》為例闡明,文本理解以“前理解知識”為起點,主體理解的結果將會融入到“前理解知識”中,對他者的文本理解起到規約作用。文本作者與文本釋解者所處的外在時空及內在語境都存在差異性,這決定了并不存在唯一的、客觀的文本理解。本文提出的文本理解路徑重在為解決文本理解中所存在的“失真”現象提供思維進路,即通過不斷超越已有的“前理解知識”,實現對文本“真實面貌”的逼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