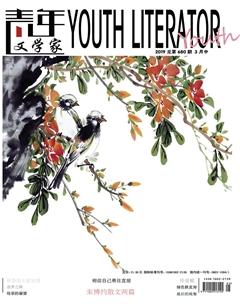小說的“氣味”
摘 要:王安憶無疑是上海文化的名片,事實的陳述,真實的溫暖,真實的殘酷。對自然美和人世美抱有直接的興趣,永遠是心地善良的標志。王安憶筆下的上海使我病了一場,熱勢退盡,還我寂寞的健康。
關鍵詞:簡單;時間;象征
作者簡介:李志軍(1979.2-),男,漢族,遼寧省遼陽市人,中學一級教師,大學本科,研究方向:漢語言文學教育。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08-0-01
最近和學生一起研讀了王安憶女士的代表作《長恨歌》中“圍爐夜話”一節。心緒難平,故寫此文。
有一種恍然的感覺,仿佛迷失在王安憶筆下的時光里。恬淡的不像60年代的上海。讀這篇文章有一種安靜的感覺,仿佛一霎那間時間都靜止了,只有盈滿身邊的溫暖,又從夢境中傳來的細碎的聲音,甜糯的香氣充盈這個安靜的世界。
在老老舊舊的時光里,日子像細沙一樣緩慢地流淌。生活在60年代的上海里,卻又對外面的世界漠不關心,分明是寒冷的冬季,卻又讓人覺得溫暖洋溢。好像屋子的一扇門就能屏蔽掉一整個世界的喧囂。輕言慢語,綿綿不盡,絲絲縷縷的聲音,溫熱,稀薄,凝滯的空氣充斥著舊上海的日子。算好了一日的活計,慢慢地磨著精細的糯米粉,炒曬干的西瓜子,在弄堂里交錯的竹竿上曬起了剛洗好的衣衫。他們聊著最無關緊要的話題,說著對人生太多太多的慨嘆,圍著火爐做著簡單的游戲卻又久久不愿離去。就這樣的簡單如一,干凈如洗。
我為這樣的簡單感動著,又為這樣的閑趣癡迷著。或許生活本就是一場簡單的游戲。這樣的日子空泛而不空洞,沒有所謂的夢想卻有著自己的追求,甘愿平凡卻又不平庸的生活著。像螞蟻一樣每天重復著單調的生活卻又津津樂道。在空虛的日子里深深享受著這樣的空虛。如果說生活是種盲目,那他們樂在其中。
可這樣看似平淡溫馨的日子下應該是一種別樣的憂傷吧!每個人做著自己單調的事,而心里涌出的是無限的惆悵,關于過去和未來。我相信每個喜愛回憶的人都是有故事的人,每個竭力過著平淡日子的人卻是內心最洶涌的人。這樣一種感情,該怎樣去理解?
我不禁想到了王家衛的電影。仔細斟酌著光和影,在明與暗之間尋找著那個年代特有的顏色。想起了《花樣年華》里泛黃的燈光下彌漫開的淡淡的憂傷。記得張曼玉在其中變換的26套上海旗袍,或濃烈或清淺。可是無論旗袍怎樣變,上海永遠是上海,沒有悲劇卻被悲傷籠罩的城市。在梁朝偉轉身走進雨簾的時候,世界靜得只剩下雨聲。那雨滴連串仿佛一串無奈的省略號。張曼玉被松開的手輕微的抽搐了一下,隨即緊緊抓住了另一只手臂。只剩下一句話回蕩在雨中“如果多一張船票,你會不會跟我走”。因為沒有如果,所以沒有回答。
我至終都覺得時間是一個神奇的東西。他能把復雜打磨得簡單,能把棱角打磨得平滑,他能將喜歡變成懷念,能讓味道變成永久。那一份將時間碾碎了過的,讓短暫變長,讓瞬間變為永恒的細膩讓我感動。
我腦海中的舊上海:電車、咖啡館、海報、劇院、牌坊一樣的建筑,街邊的電話亭和墨綠色的郵筒在人來人往,喧囂浮華中靜默著。沉木的地板、斑駁的磚墻、雕花的門窗、里弄里彌漫著豆瓣醬的香氣,城市的細縫中有著最瑣碎的繁雜。
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太真實了,真實的溫暖,真實的殘酷。她的筆觸細膩而不做作,飽滿卻不空洞。每一個字都有靈氣得仿佛能擰出水來一樣。平平淡淡,看似沒有波瀾,卻隱匿著最深的人間滋味,仿佛是一杯清茶,淡淡的滋味過后才是繞齒余香。
長恨歌,在漫漫長夜里,在明亮的日子里,恨,怕是早已變成了無奈與淺淡的傷感了吧!
一切藝術同時既有外觀,又有象征。有人要鉆到外觀底下去,有人要解讀象征的意義,也許這是大勢所趨。但是,在《圍爐夜話》中有什么呢?那些白胖的糯米,綿繡的霓裳羽衣,香氣四溢的芝麻,爐膛中攏起的火,炒栗子,西瓜子,大白果,嫩雞蛋,九連環,一件件,一宗宗,這些都象征著什么呢?
說它們象征著老上海精雕細作的生活?我覺得不是,這一件件,一宗宗,是事實的陳述,并不是象征。而且,生活本身無需被象征,它一直都在。無論怎樣被象征,生活永遠保持同一姿態。
既然摒棄了《圍爐夜話》中的象征意義,那么這篇文章還剩下什么呢?除去象征,當然是外觀。王琦瑤、毛毛娘舅,嚴師母,薩沙,四個人挨過一個庸長而幸福的夜晚,不談人生,不談哲學,只細數那些瑣事,最最閑來無事的話,每一個字都是從心底里吐出來,他們談的,無非是“炒栗子的甜糯,瓜子的香,白果的苦,酒釀的醇厚,”氣味和滋味,勝過一切語言,即使人亡物毀,久遠的往事了無陳跡,唯獨氣味和滋味雖脆弱卻更有生命力,雖虛幻卻更經久不散,忠貞不二,它們仍然對依稀往事寄托著回憶,期待和希望。
時間,空間,都在作家筆下被有意地除去,剩下的,只是這種螺絲殼子里不變的生活。這種生活,是精細,溫暖,平和的。生活的殼,在作家的描寫和我的閱讀中層層剝落,露出它美的一面,它美在何處?像是填滿那個夜晚的縫隙的空氣,這種難言的美,我無法講。就像同冬天講雪花一樣蒼白無力,我又如何向生活在生活中的人,去講生活中一個晚上的美?
在美的作品中發現美的含義的人是有教養的,這種人有希望,認為美的作品僅僅意味著美的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