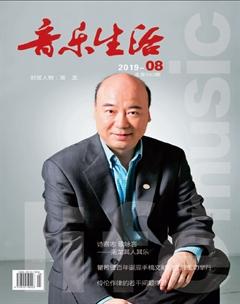“起點”沉靜而精致
鄧姝
2019年6月19日晚,北京當代樂團策劃演出的“‘起點Departure經典室內樂作品音樂會”,與上海音樂學院“國際一流作曲人才培養與實踐”戰略創新團隊項目合作,如期在上海交響樂團演藝廳上演。2018年秋,這支中國最年輕的北京當代樂團起航,著名作曲家秦文琛擔任樂團藝術總監,他的作品極富影響力,他對中國新音樂的發展有著前瞻性的視野,對中國當代音樂的本土與國際化影響充滿人文情懷。樂團策劃人之一青年作曲家王爾清在節目單中提到:音樂會聚焦于“作曲家創作生涯的兩端”的獨特視角,于北京當代樂團及熟悉當代音樂作品的作曲家、演奏家而言,都蘊藏著對當代音樂經典的承接與具有“起點”的意味,也預示著音樂創作值得記憶的歷久彌新的生命力。
音樂會分為上、下兩個半場:上半場演出曲目為作曲家青年時代所寫的作品,【中】郭文景26歲時創作的《巴》(1982)、【英】布萊恩·芬尼豪赫22歲時創作的《四首小品》(1965)、【英】托馬斯·阿德斯20歲時創作的《捕捉》(1991);下半場演出曲目皆為作曲家晚年時光所寫,【美】艾略特·卡特于103歲高齡時創作的《記憶女神》(2011)以及【法】杰拉德·格里塞晚年倉U作的《時間的漩渦I-II》(1994-6)。樂曲體載及樂器組合形式豐富多樣,同時集結了近五十年來中、英、美、法不同風格流派及不同時期的當代音樂標識與經典作品,跨越了20世紀初至今世紀時光里的幾代作曲家。
郭文景的《巴——為大提琴和鋼琴而作》,借“巴”字比喻四川當地的風土鄉俗。大提琴演奏家莫漠的演奏具有用第一人稱敘述的感染力,在與鋼琴的對話中營造出一種主客觀相交融的意境與空間距離。大提琴用撥奏的指觸來模擬具有典型技法標識的古琴演奏及巴蜀吟唱音調,在低音區鋼琴下行旋律的映襯中,彰顯出一種絲弦的質地、聯覺與時間的厚重感。隨著腳步沉緩的進行曲般頓挫掃弦的出現,大提琴與鋼琴的音樂性格發生了巧妙變化,隨后以re-do-la四度框架為核心框架,凝練且熟悉的西南民歌音調在循環往復中被反復記憶,并在緊接模仿的復調織體中勾勒出主題輪廓,通過倒裝變奏和板式變化逐漸出落。在鋼琴明快的節奏牽引中,音樂情緒逐漸向具有歌舞性質的【老六板】主題,產生了較為鮮明的性格轉折,并始終緊扣核心音,在集中凝練的音樂素材中,通過變奏重復的手法獲得不斷向前推進的穩健動力,并在三起三落之后,以五度音程框架塑造出強勁的重力感,營造出豪放灑脫的民間民俗音樂氛圍。
“新復雜派”作曲家芬尼豪赫的《四首小品I為長笛和鋼琴而作》,是本場音樂會中創作時間最早的一部作品。長笛演奏家克拉拉·諾瓦科娃與青年鋼琴演奏家謝子薇默契配合,現場音響流動,可以捕捉到演奏家精湛技藝、情緒化呼吸與整體音響之間的層次分合,偶發性出乎意料的音色音響表達不自覺地吸引和調動起了聽覺神經,但如同機械工程般的深奧譜面是作曲家如何書寫、演奏家又如何將其溶解于具體樂音,其復雜程度使人不得不感嘆其個性化的理念與創造力。充滿豐富想象力與創造活力的作曲家托馬斯·阿德斯,其作品《捕捉——為單簧管、小提琴、大提琴和鋼琴而作》,鋼琴在極端音區古怪作響,隨后在飽滿跳躍的音響顆粒中展開,單簧管在一陣清新的弦樂鋪墊中出現,鋼琴三重奏的演奏家們試圖通過各種不同方式來“捕捉”突然出現又消失,單簧管演奏家克麗斯吹奏聲音極具魅力。詼諧多姿的音響態勢與性格迥然不同的兩組樂器不斷生成新的音樂畫面和語意,使得樂器富于角色化而具有鮮明性格,因而兩組音色的碰撞與相遇妙趣橫生。
《記憶女神——為小提琴獨奏而作》是作曲家為紀念他剛逝去的妻子海倫·卡特而寫,作曲家艾略特·卡特當時已經103歲高齡,沉緩的連弓凝聚了他細膩而深沉的情感表達。這首作品起始如同在深夜里給自己寫信的娓娓道來,隨后情緒在拋物線式的大跨度旋律進行中擴張積累,悠長且呈橄欖形的力度變化貫穿樂音生發、持續、消逝的整個過程,零星點綴兩、三點短弓如句點一般,情態與性格與主題截然不同。“頻譜樂派”創建者之一杰拉德·格里塞《時間的漩渦I—II——為鋼琴和五件樂器而作》選擇了前兩個樂章,可以明顯感覺到兩個樂章一動一靜各異的音樂氣質以及趨于持續變形的生命活力和沉浸氛圍,音樂本質更傾向于一種對聲音自然形態生發的模擬,逐漸蔓延以至停止消逝。第一樂章在點線交織與強弱對比中獲得動能,搖曳的音響順著水流般的情緒堆積打開感官聯覺,單簧管、鋼琴、弦樂的音色層次既肆意生長又暗合統一,隨后滋生出具有蛙鳴般的金屬質地的音色音響,形成了電子音樂的聲場效應,層層擴大。鋼琴強有力的和弦在極端音區高低交替,漸行漸快并間插以風鈴式的旋律線條,形成連斷、快慢、強弱、粗細的對比。第二樂章的音樂材料十分凝練,具有克制簡約的精神品質,樂團指揮及演奏家們對樂器音色的精確追求、對強弱氣息的控制和整體結構與音響層次的漸變式處理,在弦樂、長笛、低音管的對位線條和氛圍營造之際,預制鋼琴在明晰沉穩的節奏下,模仿鐘琴音響,敲擊出具有圣詠氣質的主題,音樂的推動及情緒的舒展全然在聽覺中自然生成,既是逐漸浸淫又清晰可感,最終聚焦于長笛氣若游絲的演繹,在聲場與冥想間嫁接,成為宇宙稀薄空氣中唯一且即將消逝的振動體。
如果從自身對整場音樂會的體會而言,作曲家郭文景的創作經歷及其作品《巴》(1982)中所傳達出的一種堅定的音樂文化自信與民族音樂品格的現代化表達讓人不得不信服。作品中展現和提倡了文人古琴和中國民間的音樂傳統,它們的價值在上世紀幾度遭到被貶抑甚至臨界斷層的時代冰點,從這一層面出發,再重新品味作品產生的時代及其中飽含的精神態勢是令人激動的。以郭文景為代表的一批中國作曲家,重估和重塑對傳統音樂的聆聽方式,同時從自然材質和音色音響的角度尋找音樂結構的存在方式,重視基于以中國樂器為代表的具有沉思性的樂音表述方式及其中所蘊含的有關樂音表達的思想與中西共存的關系。
格里塞《時間的漩渦》第二樂章的結束猶如一種對人類早期和音樂最初自然時空的某種探索和回歸,若有若無、自成生趣,“頻譜音樂”中精確量化的音色音響及其細膩可控的量變,似乎遙相呼應了中國傳統音樂中具有“變與不變”、“漸變發展”的思維邏輯與音樂特質,比如長期以來音響與譜本之間的“和而不同”問題,抑或是小型器樂合奏中樂器與樂器之間音色音響的相互配比與主次關系問題,尤其是作品其中體現出濃厚的、與東方音樂美學相契合的音樂思維與文化思考,如聲場的營造與指向性、對音色的強調、隱喻的表達方式、簡練的結構素材、包羅宇宙諧和的理想以及對自然技巧的模仿與超越等等。這些審美觀念在中國的形成往往因師法自然而起,因而其美學氣質和理念中往往折射出某種高于樂音自身、暗含宇宙和諧統一的哲學標準,或許人類有著共享一種互通的“自然形態”,是相互融合而不是非此即彼,呈現出一種聯覺對等的宇宙觀、美學觀,或許這種被音樂化了的自然,似乎也可以作為法國“頻譜音樂”創作的核心理念之一。
阿德斯20歲所寫的《捕捉》中對傳統室內樂寫作的挑戰與顛覆,以及卡特103歲所寫的《記憶女神》中對人性、人聲的理解以及情緒變幻之深奧、簡練造就了別具一格,從創作生涯的兩端出發,看到了生命經歷的時代與當代室內樂創作之間的思維活力與沉思。如果說英國“新復雜音樂”是對嚴格控制與自由處理的深度思考,那么芬尼豪森《四首小品》中嚴謹譜式下對各式音樂參數的詳盡記錄,何不為今人對古人“音聲關系”探討的一種隔空回應?作曲家對演奏者個性化音樂表達空間的探索又何嘗不是今人對“文本與音響關系”的深層探索?法國著名學者克洛德·列維斯特勞斯曾深刻指出,“所有文明的偉大之處都在于其差異豐富的細節”,北京當代樂團對本場音樂會的策劃與演繹,讓我對中西文化傳統與當代音樂之間的差別進行了比較集中的思考。音樂最為精深的表達與哲思上,兩者之間并非有多么巨大的鴻溝,而是存在一些細微的差別,盡管這種差別常常會反映出完全不同的表現形態。事實上,冷靜來看,自20世紀初起一直討論的東西方文化沖突可能存在或反映在各個不同層面及音樂的方方面面,以作為否定自身傳統的前提條件之一,但若從音樂技術和音色音響的精微與深處出發,我們可以發現這種沖突可能僅僅只是個假設而已。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之上,如何更恰當地表達音樂及其思想、如何運用現代化技術手段進行音樂研究和創作,值得思考與反思,每當此時總是想起周文中先生的“匯流”思想,以及反復提到的這句話:“悠久的東方文化將和發展急速的西方文化共同匯入人類歷史的下一個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