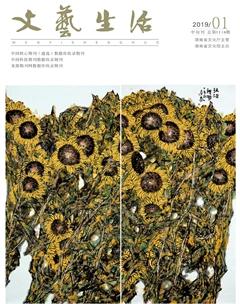中國古代藝術中的借物寓意表達
孫磊
摘要:中國古代藝術中,具有很多帶有象征意義的表達和意蘊,在藝術史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藝術品作為思想和文化的載體,在不同的歷史階段和社會背景下產生了美好的寓意和各種先象征性的表達,本文從玉之禮儀、山水中的意蘊、四君子題材的象征意義三個部分進行了闡釋。
關鍵詞:古代藝術;寓意;禮儀;象征
中圖分類號:K87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02-0011-02
一、玉之禮儀
中華民族具有極為悠久的用玉傳統,現代考古資料證明,至遲到新石器時代,玉已經進入了先民的生活,而且逐漸被賦予了諸多特殊的含義。《孔子家語·問玉》中記:
子貢問于孔子曰:“敢問君子貴玉而賤珉,何也?為玉之寡而珉多歟?”孔子曰:“非為玉之寡,故貴之,珉之多,故賤之。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溫潤而澤,仁也;縝密以粟,智也;廉而不劌,義也;垂之如墜,禮也;叩之,其聲清越而長,其終則詘然,樂矣;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達,信也;氣如白虹,天也;精神見于山川,地也;硅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詩》云:‘言念君子,溫其如玉。故君子貴之也。
孔子在其中泛泛而談了玉有十一種美德,這成為流傳千古的經典論述。玉被孔子喻為道德人文修養的象征,成為一種理想意義上的道德標準。
《論語·雍也》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顏淵》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為?”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蔣。”玉通常用來形容君子,因其具有的“文”和“質”的內在統一。
玉器要通過切、磋、琢、磨等系列的復雜加工才能成器。玉經常用來比喻做學問,《詩經衛風·淇奧》說。“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又例如玉玖象征著決斷,象征著與人決裂,《荀子·大略》:“絕人以塊,反絕以環。”《周禮·春官·大宗伯》說,“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這句話表示玉琮是祭祀天地的禮器。在史前先民的心中,玉琮外方內圓,是天圓地方的象征。玉琮體中心上下穿透的圓孔,當為通天地之通道。所以,玉琮與天地陰陽有關,因此對其崇拜至極。由于玉琮具有祭祀功能,所以它還是中國古代權力和財富的象征,只有達官貴人才可以擁有玉琮。古代早期的玉琮多用陰線刻,晚期玉琮多有浮雕紋飾。琮身均有獸面紋,紋飾以四角線為中心,分為四組隨琮高低不同,以相同的紋飾分數組飾于琮上。部分玉琮在主體獸面紋外,用細陰紋刻細“神人”圖形和云雷紋,陰線用利石刻而成,線條堅挺。玉琮是良渚文化中最具特征的玉器,不僅是形體最大的器件,也是出土較多的玉器品種。此外,古代巫師還常用劣質的玉琮、石琮,或被燒過的玉琮,來鎮墓壓邪、斂尸防腐、避兇驅鬼,這也為玉琮賦予了趨吉避兇的文化內涵。
中華古人佩玉佩,把玉壺,執玉筆,枕玉枕,都是為了借玉觀照自身,檢點自身,高場目身。玉甚至被用來比附一切美好的食物,如成全他人叫“玉成”,堅守氣節叫“玉碎”等。
二、山水中的意蘊
《論語·壅也》:“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孔子以山水比附人的仁智,認為水性就像人的德性、人的仁愛之心:水沒有鋒芒,不會傷人:智慧清明,能夠包容丑惡:永遠持平,不是一頭高低:盈而有度,永不自滿:萬事萬物都受到水的恩澤。因而智慧的人喜愛水,仁義的人喜愛山;智慧的人懂得變通,仁義的人心境平和。智慧的人快樂,仁義的人長壽。《老子》:“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于道。”老子認為人最好的性格就是像水一樣的性格,沒有棱角,以柔克剛應時而變。
中國古代文人畫,多取材于山水、花木,以抒發個人情感,間亦寓有對民族壓迫或腐朽政治的憤懣之情。標榜“士氣”、“逸品”,講求筆墨情趣,脫略形似,強調神韻,并重視書法、文學等修養及畫中意境之表達。文人畫在中國古代繪畫中占據重要的地位,其不僅僅是個畫種,而且是一個從畫家到作品及理論的三位一體的藝術體系。已知的畫史畫論多為文人所作,這些畫論的內容不僅有關于繪畫技法的闡述,而且有相當部分將文人畫的創作思想、審美理想上升到了哲學的高度。古代文人追求“立德”“立功“立言”。“詩為言之余,書為詩之余,畫為書之余”,因此文人畫家其實是一批業余畫家。他們以將個人品行、情操、學識、修養、感受融入畫中為己任,大都借助繪畫入“道”,獲得精神上的解脫和超越。
如元代畫家黃公望創作的紙本繪畫《富春山居圖》,以浙江富春江為背景,畫面用墨淡雅,山和水的布置疏密得當,墨色濃淡干濕并用,極富于變化。元代將人分為四類,依次為蒙古、色目、漢人、南人,黃公望淪為“四等公民”。經歷國破家亡,南宋遺民在鄙視和屈辱中以求生存,表現了亡國后的失落感。山水畫不是簡單的描摹自然的風光,而是畫家的精神的訴求與流露,是畫家人生態度的表達,是畫家人生追求的體現。《富春山居圖》畫的是一個漫長的江水,在一千年的歷史里,流過淺灘、激流、高峰。前面一段是夏天的感覺,到后面一段,出現了秋天的景,樹葉部分淡掉,全部用垂直的皴法,好像繁華落盡的感覺。
三、“四君子”題材的象征意義
(一)菊
陶淵明的《飲酒》詩云:“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寫出了作者那種恬淡閑適、對生活無所求的心境。“采菊”這一動作不是一般的動作,它包含著詩人超脫塵世,熱愛自然的情趣。將“見”改為“望,不好。“見”字表現了詩人看山不是有意之為,而是采菊時,無意間,山入眼簾。
這首詩,尤其是詩中“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二句,歷來被評為“靜穆”、“淡遠”,得到很高的稱譽。然而簡單地以這種美學境界來概括陶淵明的全部創作,又是偏頗的。因為事實上,陶淵明詩文中表現焦慮乃至憤激的情緒還是很多,其濃烈幾乎超過同時代所有的詩人。南宋朱淑真大膽追求愛情,眼睛里的菊花“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南宋·朱淑真《黃花》);唐末農民起義軍領袖黃巢《菊花》:“待到秋來九月八,我花開后百花殺。沖天香陣透長安,滿城盡帶黃金甲。”菊花在不同人的眼中賦予了不同的意義,賦予了個性化的人格。
據《宣和畫譜》所記載,宋代黃簽、趙昌、徐熙、滕昌祐、黃居窠等名家都畫有寒菊圖。到了元代及明清,在菊花的畫法上發展了水墨寫意,豐富了技法的表現。如元代蘇明遠、柯九思,明代的沈周、唐寅、陳淳,都是水墨寫意的畫菊名家。清代畫菊者更是名家輩出
如清代虛谷《菊花圖》,畫中斜寫黃白菊花于矮籬前綻放爭秋。筆墨出神入化,側峰逆運,淡彩焦墨,筆筆送到。黃菊枝葉以水墨暈寫,而白菊卻以青葉相襯,桿加赭色。兩菊雖枝葉交雜,卻密而不亂,層次分明。干筆疾勁,勾出矮籬,白花矮叢使畫面穩定平衡。背景雖無它物,卻充滿空寥寂靜之意。整幅畫冷雋峭秀、傲岸清高,反映了畫家本身的性格和處世原則。
(二)竹
鄭板橋為“揚州八怪”重要代表人物,一生只畫蘭、竹、石,自稱“四時不謝之蘭,百節長青之竹,萬古不敗之石,千秋不變之人”。其詩書畫,世稱“三絕”,是清代比較有代表性的文人畫家。鄭板橋的一生,經歷了坎坷,飽嘗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世態炎涼,他敢于把這一切都糅進他的作品中。鄭板橋的題畫詩己擺脫傳統單純的以詩就畫或以畫就詩的窠臼,他每畫必題以詩,有題必佳,達到“畫狀畫之像”“詩發難畫之意”,詩畫映照,無限拓展畫面的廣度,鄭板橋的題畫詩是關注現實生活的,有著深刻的思想內容,他以如槍似劍的文字,針砭時弊,正如他在《蘭竹石圖》中云:“要有掀天揭地之文,震電驚雷之字,呵神罵鬼之談,無古無今之畫,固不在尋常蹊徑中也。”其一畫竹圖題云:“烏紗擲去不為官,囊囊蕭蕭兩袖寒,寫取一枝清瘦竹,秋風江上竹漁竿”,借竹抒發了他棄官為民、淡泊名利、享受人生的平靜心態,其二《竹石圖》畫幅上三兩枝瘦勁的竹子,從石縫中挺然后立,堅韌不拔,遇風不倒,鄭板橋借竹抒發了自己灑脫、豁達的胸臆,表達了勇敢面對現實,絕不屈服于挫折的人品,竹子被人格化了,此時,“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