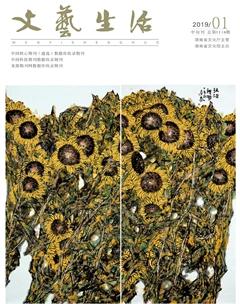先秦重器
傅玉 劉楊莘彧 荊玉坤
摘要:春秋戰國時期是人性張揚的時代,這是一個解除束縛、富于進取和創造的激情時代。周天子一統天下已經名存實亡,各諸侯國的權力之爭已見分曉,各國內部實行變法圖強,一個時勢造英雄的時代到來了,一個空前開放的時代終于到來了。人們對神的膜拜更加理性,個人奮斗進取精神,建功立業強烈欲望,使得審美文化逐漸剝掉了巫神的色彩而賦予了人文色彩。尊象器物的造型、圖飾也一改殷商時代的怪異、神秘、猙獰而趨于樸拙、寫實、平和、溫順,更加生活化,崇文尚實之人文意象占為主流。楚地有崇尚浪漫的情懷,使各種器物都有了一種流動、飛揚的韻致。與以往的凝重、肅穆、莊嚴不同,它們洋溢著一種運動的生命力,升騰著一種舒揚的美感,其中的代表作就是蓮鶴方壺。
關鍵詞:蓮鶴方壺;圖飾;美感
中圖分類號:K876.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02-0026-01
蓮鶴方壺出土自“鄭公大墓”,是新鄭彝器的典型代表,它所表現出的多元文化因素,與鄭國所處的復雜歷史環境分不開。春秋戰國時期,周天子一統天下已經名存實亡,各諸侯國的權力之爭己開始,人們對神的膜拜更加理性,個人奮斗進取精神成為主流,建功立業的強烈欲望使得審美文化逐漸剝掉了巫神的色彩而賦予了人文色彩。
方壺通體布滿了盤曲的龍形裝飾花紋,這些蟠璃紋相互纏繞,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在努力追求一種昂揚的生命意志。方壺最為精彩的部分是雙層鏤雕蓮蓋頂仰起盛開的雙層蓮瓣,上立一只展翅欲飛、引頸高吭的仙鶴,此鶴清新自由、輕松活潑。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贊:“此鶴突破上占時代之鴻蒙,正躊躇滿志睥睨一切,踐踏傳統于腳下,而欲作更高更遠的飛翔。”方壺兩側并鑄有圓雕的龍形細長雙耳鏤空的雙龍耳較大上出器口,下及器腹。壺體四面以蟠龍紋為主體紋飾,并在腹部四角各鑄一飛龍,圈足下以兩只伏虎承器,有蓋,雙耳,圈足,壺身上下遍飾各種附加裝飾,采用了圓雕、淺浮雕、細刻、焊接等多種技法鑄造而成。這是一件巨大的青銅盛酒器,整個壺的造型優美新穎,藝術構思巧妙,與商朝那些厚重而莊嚴的青銅器形成了鮮明對比,在藝術風格上反映出東周時期雕塑藝術發展所帶來的清新氣息。
蓮鶴方壺的圖飾標志著中國的文化審美由殷商的“猙獰美”逐漸向“和諧美”過渡,藝術審美和創作的意象也由“神威”轉向了“中和”。蓮鶴方壺的鶴圖飾是一種象征和寄寓,一種審美空白的創造。“空白意識是在一定的民族文化心理基礎上覺醒的。它受到古代哲學思想的影響,形成于商周時代的《易經》中的“陰”、“陽”理論,認為自然界發展變化的基木規律即為陰陽交替,所謂
“一陰一陽之為道,,是也。到了老子又從論道“自然無為”的觀點出發,更為明確地提出了“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的思想”。它標志著鶴的形象,己登上工藝文化即本原文化的殿堂,有趣的是,那鶴競立于中國人心目中圣潔、高雅的蓮花之中—這是后來觀世音菩薩的位置,鶴在設計者眼中的品格,己不言而喻。其后,復有戰國早期的青銅器鹿角立鶴,以及戰國帛畫《人物御龍》。這些作品主要取材于真實的自然界,盡管古代藝術家的思維已從現實的土壤上升華,賦作品以強烈的浪漫主義氣息,表現出人類自我意識的覺醒。
蓮鶴方壺構思新奇,設計巧妙,富于想象,造型生動,裝飾華麗,鑄造宏偉氣派、器型莊重典雅。物象眾多,雜而不亂,立鶴走獸,動靜相輔。雕文刻畫,各具神情,融清新活潑和凝重神秘為一體,開創了新的藝術風格。的確,此壺就如騰飛其上的仙鶴一樣,正標志著中國藝術風格的一個新的開端。蓮鶴方壺上的鶴是寫實的,不要小看這一次小小的寫實,因為它之前青銅器上的動物都是被神話了的,它之后的戰國寫實成為大流行。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劃時代的藝術巨制,它打破的是禁錮與皇權,引來的是一個開放的時代——諸子百家自此先后登上歷史的大舞臺。
另外,蓮花一向被認為是佛教文化的一部分,這是不準確的,它反映的是中國本土原生文化,因為蓮鶴方壺誕生的時候,佛祖還沒有誕生。蓮鶴方壺代表了鄭州,代表了中原,甚至是代表著整個中國古代那個漫長的青銅時代,是那個時代我們國家與民族命運的一種物化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