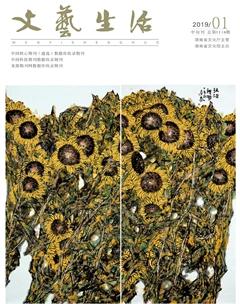道德標準缺憾與福澤渝吉的現代世界觀辨析
閆曉艷
摘要:在相關學者和研究機構的現代社會指標體系中道德標準缺失是一種遺憾。福澤諭吉提出智德并進主張難能可貴,但其智德并進發展觀有自相矛盾之嫌,且專門指向一個國家或民族的內部發展。在國際關系領域,福澤將道德標準缺省,堅持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鼓吹并支持軍國主義侵略,甚至稱霸一方,這不能不說是一大缺憾。
關鍵詞:道德;標準;福澤渝吉;現代;國際社會
中圖分類號:G40-0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02-0066-03
一、前言
近代以來,隨著現代化運動的出現及不斷拓展,許多學者及研究者都對現代社會的定義、內涵及標準問題進行了思考。作為日本現代化的領軍者及推動著,福澤渝吉也對相關問題進行了思考。有關福澤渝吉的研究,國內外都有大量成果,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礎上,結合自己的心得,對福澤渝吉的現代世界觀作辯證性分析。
二、現代化標準中的道德指標缺憾
從廣義相對論的角度看,世界現代化進程開始以后,現代化研究及其理論也應運而生。及至20世紀中后期,隨著現代化浪潮在世界范圍展開,經典現代化理論、依附論、世界體系論、后現代主義、新現代理論等相關理論也接踵而出。在對現代化進程及現代社會進行研究與考察時,首先要回答的一個最基本的問題就是關于現代化的標準與指標問題。對于這個問題,相關學者、研究機構先后給出了多種不同的指標體系。
經典現代化理論的定性比較模型標準認為:(1)政治現代化的主要特征為民主化;(2)經濟現代化特征為工業化、專業化、規模化、非生物能源的廣泛利用、第二和第三產業超過農業;(3)社會現代化的特征為社會階層分化、組織專門化、社會流動、城市化、家庭小型化等;(4)文化現代化的特征為宗教世俗化、觀念理性化、普及正規教育、知識科學化、信息傳播等;(5)個人現代化的特征為參與性公民、具有豐富知識、自信、高度獨立自主、思想解放、愿意接受新經驗和新知識等。
例如1960年日本箱根國際現代化會議提出的箱根模型包括8項標準:(1)城市化;(2)使用非生命能源程度高,商品流通與服務設施增加;(3)社會成員在廣大空間相互作用,廣泛參與經濟、政治事務;(4)傳統的村社與社會群體解體,個人有更大的社會流動性,個人的社會行為具有更廣泛和多種不同的范圍;(5)文化知識得以全面推廣,個人對周圍環境傳播的世俗的、科學化傾向;(6)廣大和深入的大眾交流網絡;(7)政府、工商業等大規模社會機構的存在,以及這些機構中日益增多的官僚組織;(8)在一個大民眾團體控制下,各大民眾團體加強統一(即國家),這些單位之間的相互作用日益增強(即國際關系)。
而定量標準與指標的研究者與制定者更是從容易度量的生產總值、能源消費、就業率、城市人口比例、開支、教育、健康、交流媒介、收入分配等方面制定相關標準和指標體系的。例如世界銀行《1982年世界發展報告》中提出的人均收入標準、聯合國開發計劃署《1990年人文發展報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聯合國成員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人類發展指數、2000年聯合國千年峰會上通過的《千年發展目標》(The Milennium DevelopmentGoals,簡稱MDGS),以及我國現代化研究者及相關機構提出的《中國現代化報告2001》中提出的第一次現代化及第二次現代化評價指標體系等。
上述指標體系都是重視了物質和生活方面的標準,忽略了道德方面的標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因為人類社會有史以來的歷史演進已經昭示,無論人類社會發展進步到何種地步,穩定祥和的生活才是人類生活的幸福所在。而和諧世界的構建需要國際道德水準的提升。
但是,近代以來不爭的現實首先是人類還是經歷了無數次戰爭暴行,尤其是20世紀上半葉史無前例的兩場世界大戰。
其次,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打著先進的近現代文明的旗號,出于一己之私利,鄙視落后民族、種族,推行種族清洗、甚至種族滅絕政策。
例如作為啟蒙理性化身、曾任美國總統的托馬斯·杰斐遜以文明進步的名義宣稱印第安土著“行為粗鄙”,“使根除成為正當”。一個世紀后,西奧多·羅斯福,一個體面的現代人提及印第安人也持同樣的態度,認為“根除最終是有益的”。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及大戰期間,德意日法西斯集團進行了大規模的針對所謂劣等民族、種族的殺戮。即使是在冷戰結束后,美國學者福山描繪的所謂西方式自由民主制度一統天下、人類文明進步任務已經完成的所謂“和諧世界”中,還是出現了1994年的盧旺達種族滅絕暴行等。英國學者邁克爾·曼通過研究得出結論認為種族清洗本質上就是現代現象,盡管并非歷史上從未發生過,但只有到了近代以后它才變得更加多發、更為致命。
上述種種都證明人類在通過現代化構建現代社會,使物質生活質量大大提升的同時,國際道德的進步并沒有取得相應的、應有高度的進步,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而人們在制定現代化標準和指標時,又大多忽略道德標準,這不能不說是一種缺憾。
三、福澤渝吉智德并進發展觀的指向問題及自相矛盾之處
福澤諭吉是日本現代化倡導者與推動者,在日本,乃至世界范圍都享有極高的聲譽。從最初接觸現代歐美社會時起,福澤諭吉就開始思考現代世界的發展問題及標準問題。1860年,福澤諭吉第一次走出國門,隨德川幕府海軍的軍艦咸臨丸訪美,雖然只是在舊金山停留了一個多月,但美國經濟、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發展,以及民風民俗還是給福澤諭吉留下了深刻印象,對其思想造成很大沖擊。1862年1月至1863年1月作為隨團翻譯,跟隨幕府使團訪歐,福澤諭吉首先更深刻地感受了歐洲諸國先進的現代物質文明,其次對創造出這種先進物質文明的制度產生強烈興趣,對相關國家的政治、經濟、教育、醫療、社會福利等制度和體系進行了全方位考察。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開始關心與思考作為現代文明國家的標準問題。福澤諭吉在作為這次訪歐日記的《西行手賬》中,記錄了在英國工作的荷蘭醫生Simon Belinfante的一段講話,其中提及了現代文明政治的5個條件,即尊重自由、法治、宗教信仰自由、擴大學校教育、導入科學技術。1866年,《西洋事情》最初3編刊行。1867年3月至7月問,福澤諭吉第二次訪美,更深入地接觸和了解了美國和西方文明。1868年,《西洋事情》外編3冊刊行,1870年《西洋事情》第2編共4冊刊行。在《西洋事情》中,福澤諭吉在之前的現代文明政治5項條件基礎上又加上了第6條“福利充實”。上述6條構成福澤諭吉最初主張的現代“文明國”的標準。由此可見,福澤諭吉最初并沒有將道德進步視為現代社會的標準。
1875年,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概略》刊行,標志著其現代世界觀的形成。在該書中,福澤諭吉一大創新之處就是認識到了人類精神財富的重要性,將智德水準作為衡量一國現代文明程度高低的標準。他指出“文明就是指人的安樂和精神的進步。但是,人的安樂和精神財富是依靠人的智德而取得的。因此,歸根結蒂,文明可以說是人類智德的進步”。在19世紀末就探討了現代化及現代社會的道德標準,這實在難能可貴。
但是,福澤諭吉所提及的道德標準不是絕對的,且有自相矛盾之處。他指出“有德的善人不一定為善,無德的惡人不一定作惡,從古代西洋各國的歷史中可以看到許多宗教戰爭的例子。其中最嚴重的叫做‘宗教迫害…”。而在日本“在近代因意見紛歧而殘殺無辜人民的,以水戶藩為最多,這又是一個善人作惡的例子”。隨后,福澤諭吉又以德川家康、源賴朝、織田信長為例證明道德方面有缺欠的人也能完成大善事,他指出“(德川家康)違背太閣遺命,有意不守大阪;不僅不遵照遺囑輔佐秀賴,反而養成其放蕩昏庸;應鏟除石田三成而不鏟除,故意留下以為日后打倒大阪的媒介等,都說明他有最大陰謀。從這一點看,家康身上似乎沒有一點道德。然而,由于這種不德卻奠定了三百年太平基業…總之,這些歷史英雄在思德方面雖有缺點,但他們都是以聰明睿智的才能完成了大善事的人物。所以,不能單看一點瑕疵而評論全璧價值”。以福澤諭吉這樣的邏輯,西方近代殖民暴行,以及后來日本通過侵略、殺戮鄰國民眾,建設所謂大東亞共榮圈都是無可厚非,甚至是在做“大善事”。
而接下來,福澤諭吉又進而提出“道德只是個人行為,其功能涉及的范圍是狹窄的,而智慧則傳播迅速,涉及的范圍廣泛。道德規范一開始就已經固定下來,不能再有進步舊。既然道德規范不能再有進步,又何談以智德水準作為衡量現代文明國家形成的標尺呢?
與此同時,福澤諭吉所謂“智德進步觀”中的道德標準的指向主要還是內向性的,指向一個國家或民族自身內部的道德的發展。因為在談及現代世界秩序及國際關系時,福澤諭吉自身就將國際道德標準加以缺省。
四、國際道德缺省的現代世界秩序觀
曾大談特談“天不生上人上,也不生人下人”,倡導自由、平等的福澤諭吉首先將現代世界各國劃分為文明、半開化、野蠻三等,推崇歐美發達國家為所謂“文明”國家,而鄙視欠發達國家為“野蠻”國家,特別是把近鄰的中、朝視為惡鄰。在文明到野蠻的等級劃分基礎上,福澤諭吉將歐美列強對亞非拉地區的殖民侵略美化為文明對落后的戰爭。而將中國反對列強殖民行徑的做法以及戰爭的失敗看作是愚蠢行為、自作自受。例如他在《唐人往來》中提出鴉片戰爭是由于“(中國)出現林則徐那樣沒有頭腦的暴躁之人…把英國運來的鴉片毫不講理地燒毀,英國很生氣,發兵痛擊…這全是因為中國人不了解世界,不懂道理,自己做錯事情,自作自受,中國向世人宣告了自己的愚蠢”。
在持文明野蠻相對的等級秩序觀的同時,福澤諭吉認為現代世界是建立于叢林法則基礎上的弱肉強食的世界,同時主張日本也應躋身列強行列,使用暴力,實施對所謂落后野蠻國家的蠶食。他提出“…他人暴,我亦暴…己無暇顧及正論。在1883年9月的親筆連載社論《外交論》中,福澤一邊介紹旅居歐洲的友人書信一邊寫道:“自古以來,各國相互對峙、相互貪婪,無異于禽獸相殘相食……食人者為文明國人,被食者為不文之國人,若是,我日本國應加入其食者之列,與文明國人共求良餌”
光鼓吹日本應參與殖民侵略還不夠,福澤諭吉還進而鼓動日本應獨霸東亞。1881年,他發表《時事小言》一文,其中指出“方今東洋列國中,作為文明中心,堪為魁首與西洋諸國對抗者,除日本國民而誰。保護亞細亞東方,其責在我”。1882年,福澤諭吉發表《東洋政略果真如何》一文,提出日本應在東洋建立排他性、獨占的勢力范圍,深入地闡述了他的“東洋盟主論”的思想體系。
正是基于上述世界秩序觀,當日本軍國主義發布對外侵略戰爭的時候,福澤諭吉大力加以支持。例如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第一次大規模戰爭一甲午戰爭前的1894年6月6日,福澤諭吉發表《制定周密計劃不如迅速出手》一文,敦促政府迅速出兵。7月25日,日本軍艦襲擊清軍運兵船高升號,戰爭正式爆發后,29日,福澤諭吉發表《日清戰爭是文明與野蠻的戰爭》一文,鼓吹“…為了世界文明進步而排除障礙物,雖然多少有點煞風景,但是不可避免之事…”,將日本發動這場戰爭美化為是順應文明“進步”潮流的正義之舉。并捐款1萬日元。戰爭結束后,又建議明治政府對中國勒索巨額賠款并分割中國。
五、結語
總而言之,現代化考察和研究中忽略道德標準是遺憾之事情,福澤諭吉提出智德進步觀難能可貴,但其自身又自相矛盾,且指向限定為一國或民族的自身內部發展。尤其是在現代世界秩序及國際關系領域主動缺省道德標準,鼓吹推動殖民主義,霸權主義,產生了惡劣影響,是一大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