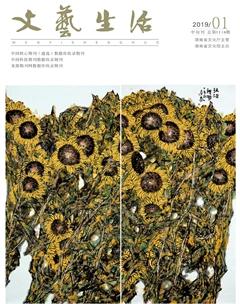傳統(tǒng)戲曲和傳統(tǒng)曲藝的融與通
劉延璐
摘要:戲曲和曲藝是中華民族藝術的的兩大瑰寶,同時也都是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藝術形式。人們都習慣上喜歡將這兩種藝術稱之為姊妹藝術。數百年來,這兩種藝術之間都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曲藝與戲曲之間有著相同的發(fā)源地,并且這兩種藝術在發(fā)展過程中也在相互之間不斷的發(fā)生交流和滲透,進而形成了如今各自之間都具有聯系但是卻又相互獨立的表演藝術。文章主要對戲曲和曲藝區(qū)別,相互借鑒與融合進行了闡述。
關鍵詞:戲曲;曲藝;區(qū)別;融合
中圖分類號:J805;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5312(2019)02-0134-02
一、前言
戲曲與曲藝在表演過程中不斷相互借鑒,進而使得人們對曲藝和戲曲之間的區(qū)別從感性層次提升到了理性的層次,有助于曲藝和戲曲在綜合方面的異同得到界定。融,任何戲曲都可以成為曲藝的題材,通,任何曲藝的形式都可以成為戲曲的借鑒。在對這兩種藝術協調創(chuàng)作、表演、欣賞等關系進行確定過程中,可以針對性的吸收這兩者之間的藝術成果,并且也能夠對其進行參考。
二、曲藝與戲曲的區(qū)別
(一)呈現角色的人稱不同
戲曲有完整的故事情節(jié)和連貫的戲劇沖突,劇中每一個人物角色都是以第一人稱出現的。隨著情節(jié)的展開和戲劇沖突的發(fā)展,觀眾看到的悲歡離合都是每個角色的直觀呈現。《打金枝》里面的皇上、公主、郭子儀、郭愛,每一個人物都是“專職”的第一人稱,“公主挨打”、“郭愛受綁”、“皇上講情”,每一個劇情的發(fā)展也都是這個“專職”角色本人來推進的。而曲藝則大不同,往往是“臺上一人,能演一群”;“臺上哥兒倆,千軍萬馬”。曲藝是以第三人稱敘述為主,人物身份可以跳進跳出,講到什么地方,需要以何種人物身份出現,全由臺上一兩個人表演。側身剛剛還是豬八戒,扭頭己變成了孫悟空;上一句還是岳元帥的語氣,下一句己成了金兀術的聲音。所以一部《楊家將》有名有姓的幾十、上百人,劉蘭芳自己分身有術,均能演繹得栩栩如生。
(二)演員對服裝服飾的要求不同
曲藝不像戲劇那樣由演員裝扮成固定的角色進行表演,而是由不裝扮成角色的演員,以“一人多角”(一個曲藝演員可以模仿多種人物)的方式,通過說、唱,把形形色色的人物和各種各樣的故事,表演出來,告訴給聽眾。曲藝的唱地域性更強,故屬于小眾。戲曲的服裝是直觀的定性,戲曲的唱超越地域性,故屬于大眾。為了更好地表現人物本質,戲典服裝應該正確掌握生活真實與藝術真實的辯證關系,在服裝的穿戴上,服裝的色彩運用上,可以與原來生活中的情況有某些區(qū)別,這種區(qū)別并不意味著可以完全面脫離生活的真實性,而是要在生活真實的基礎上加工改造,使之更典型,更有代表性、能更深刻,更真實的表現人物。為凸顯每一個角色,戲曲表演中對服裝服飾、臉譜化妝以及場景設置的要求是很嚴格很考究的。不同的人物,不同的身份,甚至不同的性格,他們的穿戴裝束都迥然不一。在傳統(tǒng)戲曲中,同為蟒袍,皇上穿的須是黃色且多為盤龍;同為朝服,文官著袍,武將扎靠:同是凈角兒,曹操要煞白,關羽則赤紅。現代戲曲的服裝道具更是具體細化到一副眼鏡一支煙上。因為只有這樣,戲曲才能更好地完成其“情景再現式”的藝術表演。曲藝往往沒有這么繁瑣,對服裝道具的依賴性較小。相聲演員穿一件大褂兒上臺演出,提起苦守寒窯十八載的王寶釧了,把手絹往頭上一扎,這就是女性人物;說到熱火朝天的勞動場面,將紙扇一舉,這就是表現的勞動工具。二人轉演員的著裝算是和戲曲里的“行頭”有些接近了,但它的作用也更主要的只是演員的演出服。因為從上臺到下場,整段兒演出下來,不管中間“跳進”過多少角色,變換過多少身份,演員絕不會因為情節(jié)的變化和人物身份的不同而在裝束上進行改變。
(三)即時性不同
曲藝在即時性上有較明顯的優(yōu)勢。說唱藝術,“說”字當先。體現即時性這一點,也主要在“說口兒”上。人物角色的變換,情節(jié)行進的快慢,主要靠“說”來掌握。由于“說”的時候不需要伴奏、布景等多方面的配合,演員就可以常常根據現時現地的情況靈活地加進或變換一些臨時的新內容,以達到更好的演出效果。相聲表演中的“墊話兒”以及其它許多曲藝曲種中時常出的“現掛”都是演出即時性的表現。戲曲表演講究有板有眼,有固定的程式,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臺詞,從起始到結束都是不能隨意更改的。這是因為作為綜合舞臺藝術,戲曲表演的完成需要眾多人員、多個環(huán)節(jié)的密切配合,每個演員的任何一處表演都關乎到整個劇情的起承轉合,不允許有臨時性的改動,這樣一來,整體的靈活性和即時性自然也就稍弱了一些。
三、戲曲與曲藝表演手段的差異
(一)曲藝的“說”與戲曲的“念”、曲藝的“唱”與戲曲的“唱”
在曲藝中,其中的“說”往往顯得比較口語化一點,也就是說,其在貫口、誦詩方面的發(fā)生比較口語化,只不過在原來基礎上進了適當的加強其節(jié)奏感。戲曲中的“念白”主要可以分成為“韻白”以及“本白”兩種方式。“韻白”用中州韻吟誦,“本白”用地方話表達。戲曲中的“本白”一與曲藝中的“說”相比之下,往往在歸韻以及拖腔調方面需要花費很大力氣。也就是說,與曲藝中的“誦詩”比較而言,“本白”在韻律感方面非常強。
不管在戲曲中還是在曲藝中,其中的“唱對五音四呼有著非常大的講究,并且也在此基礎上形成一種依字襯腔的特點。但是在語音以及旋律方面,戲曲與曲藝比重方面則有著非常大的差別。在對曲藝進行演唱過程中,往往有著字重腔輕的特點,而在戲曲中這種“唱腔”的特點則要顯得比較明顯。
曲藝以及戲曲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在對唱腔的發(fā)展中都是通過咬字發(fā)音的方式,也就是所謂的“依字行腔”的方式。但是如果論道投入的方面。則戲曲的投入遠遠超過曲藝的投入,而曲藝將主要的重心放在了咬文嚼字方面。這也就會使得戲曲給人感覺有一種“似說似唱”的感覺。當然,戲曲在唱的過程中也有著不少差異性。架桂娟認為曲藝在演唱的過程中可以有兩種方式,其中主要包括“唱書調”以及“說書調”。他認為前者屬于“唱著說”而后者則屬于“說著唱”。但是也戲曲中整體的演唱風格相比之下,“說書調”以及“唱書調”之間有著比較明顯的共性,這就體現了一種較為典型的“說”的色彩。
曲藝中的“唱”和戲曲中的“唱”其實都是一種表演的方式,他們在服務的時候,都是具有一定的目的。兩種方式由于目的不同,進而在其手段方面存在著一定的差異。而在曲藝中,“唱”則主要是對講述著進行客觀上的敘述,在這中間也穿插了不少對人物進行摹擬的抒情方式;而在戲曲中“唱”主要的作用是為給角色進行服務,雖然戲曲中在“唱”的過程中,也穿插了一些敘述的成分,但是其主觀色彩并沒有失去。
曲藝與戲曲在這方面的不同之處,表現了出發(fā)點不同則其規(guī)定性也就不一樣。僅僅就拿唱強來說,在相同的地區(qū),曲目以及劇目中共同占有同一個曲牌的現象非常普遍。但是在對曲牌的使用方面,曲藝和戲曲之間還有著比較明顯的差別。這種差別使得他們在敘事以及抒情方面?zhèn)戎攸c不相同。
(二)曲藝的“做”與戲曲的“做”、“打”
在戲曲中,其程式化體系以及行當化體系往往比較龐大。如果將程式化比作是“經線”,將行當比作“維線”,那么他們之間許多交叉的“點”就比作為“做”、“打”等。
戲曲表演程式中一共有9個系統(tǒng),其中包括:基本程式系統(tǒng)、抒情程式系統(tǒng)、生活程式系統(tǒng)、武打程式系統(tǒng)、舞臺調度程式系統(tǒng)、板式唱腔和念白程式系統(tǒng)……這9中系統(tǒng)中,前四種系統(tǒng)主要通過“做”、“打”等方式建成,而后面的5個系統(tǒng),則主要為了給“做”、“打”提供給系統(tǒng)性支持。
中國戲曲里中,舞臺上的每一個角色其實都是行當中人,所以而程式在戲曲中的作用是主要用來塑造每一個角色的基本語匯。在每一個行當中,每一個“本工”在制定喜怒哀樂中都有著自己的一套方式,并且其中的每一個動作甚至每一個招數都有非常明確的規(guī)范。由于不同規(guī)范在行當之間存在比較明顯的差異,所以在動作、表情、造型方面也非常的豐富多彩。所以相比之下,曲藝表演在這些方面有著很大差別。在古時候,藝人們說書時,總要念上一段“西江月”作為定場詞,一世上生意甚多,惟獨說書難習。緊鼓慢板非容易,千言萬語須記”在念的過程中聲音不僅要洪亮有力而且也要抑揚頓挫。雖然,人們普遍認為說書是一門很難學的行業(yè),但是與戲曲的復雜性相比起來,在其形式方面還是簡化了很多,尤其是一個人常衣素面“一臺大戲”,顯得非常淳樸。
四、戲曲與曲藝表演的相互借鑒與融合
以南平的南詞曲藝與南詞戲曲為基礎相互融合的南詞輕喜劇《公民張二狗》為例。在該劇中,不僅將音樂、燈光、舞蹈以及人物造型等融為一體,還增設來南詞曲藝說書人這一特殊的角色,更為重要的是將以南詞作為同一創(chuàng)作基礎的曲藝與戲曲有效融合在一起,取得了相得益彰的文化藝術效果,也為南詞藝術的探索和發(fā)展開創(chuàng)了一條成功之路,具有劃時代的重要意義和作用。
一方面借助南詞說書人的說唱演藝方式,實現南詞戲曲場景變換之間的銜接,并在不閉幕的表現形式基礎上,將說書人設定為該劇整場表演的組織者、事件的解說者和前后場的串聯者,不僅讓受眾在同一時間內同時感受南詞曲藝與南詞戲曲的藝術文化魅麗,還能感受到南詞戲曲與南詞說書人相互融合的別樣藝術表現形式。
另一方面,通過說唱藝人的表演幫唱和表演伴唱或道白等表演形式、方式,不僅彰顯了南詞曲藝的形體表演與唱腔,還充分體現了南詞戲曲在細膩刻畫人物面部表情和心理變化的特殊表演風格,更重要的是同南詞為母體卻以不同表演藝術為表現形式的南詞曲藝和南詞戲,在該劇中以有效嫁接、取長補短的相互融合方式實現了珠聯璧合的效果。
另外,在該劇中,南詞說書人在九段唱腔中除了使用傳統(tǒng)的鼓作為曲藝音樂,還使用了失傳已久的板作為與鼓協作的曲藝音樂,并根據該劇劇情的需要和曲牌的風格,使用了板與鼓的不同伴奏結合方式,或先板后鼓、或板鼓交錯、或強弱倒置。板與鼓的完美配合和精美設計,不僅為南詞說書人的說唱表演增添了顯著的藝術感染力,也為該劇的劇情發(fā)展和人物表演助添了一份別樣的藝術渲染力。
曲藝和戲曲雖然在藝術表演方式各有不同,但兩者在很多方面卻存在很多同氣連枝、相同或相似之處,例如,二人轉的鼓點與京劇的鼓是有共性的,主要樂器也相同,因而可充分借鑒彼此的長處和優(yōu)勢,尋找兩者在表演藝術上的共性和相同點,并在此基礎上,可有效創(chuàng)作出符合人們對藝術審美新需求和高要求的新型表演形式。
五、結語
從上面的情況中我們可以發(fā)現,在對去曲藝進行規(guī)范時,其流程也要比戲曲能簡單很多,并且曲藝中的許多講究都是來源于戲曲。所以正好驗證了前面的觀點:曲藝中與戲曲之間存在非常多的交流和滲透。如果說,戲曲在形成過程中源于曲藝向戲曲中滲透,那么當戲曲變得成熟的時候,則更多的是曲藝對戲曲的元素進行了吸收和借鑒。在清朝,由于揚州地區(qū)在南北方向的交通比較發(fā)達,所以當時民間的活動演出非常頻繁。很多昆曲演員開始棄“戲”從“書”,開始做起了評彈行業(yè),這對當時的說唱行業(yè)起到了非常大的幫助。
但是,曲藝在吸收戲曲元素的過程中需要具備一定的條件,雖然在表面看來,只是把握了其中的“度”,但是從深層次來看,卻體現者這兩種藝術之間存在的區(qū)別。
因為曲藝演演員主要是通過單三人稱的口吻進行講述故事,所以演員在表演過程中主要通過口頭闡述,必要時還會加一些肢體語言。曲藝表演過中,對人物性格的描述更多是建立在客觀講述一個人對生活的態(tài)度。戲曲在表演過程中主要通過表現一個角色的主觀言語以及行動進而展現人物的形象,甚至在刻畫人物的心里活動時,也通過人物的肢體動作來反應。所以對唱、念、做、打過程中的情緒化以及性格話極為重視。曲藝在表演過程中主要對事物展開敘述,在必要的時候也會穿插一些代言,所以很多演員在作“功”過程中具有非常明顯的輔助性,所以其難度系數比較低,同時在對基本功以及日常化的訓練過程中也并不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