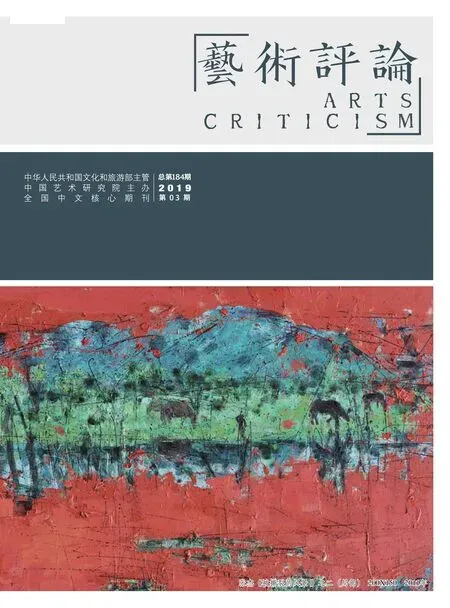攬月的情懷醉吟的天
——大型民族舞劇《李白》觀后
于 平
去看舞劇《李白》,并且是一而再(沒有“再而三”)地去看,是因為它進入了“現象級”的舞劇創作視域——我們舞劇創作對于歷史文化名人的搬演。搬演歷史文化名人,對于中國舞劇創作而言,大約起于上一世紀八十年代中期,首部是由北京舞蹈學院編導進修班(1982—1984)集體創編的《屈原》。按舞劇結構人物關系的規律,創編《屈原》的難題不是“屈原”的形象該如何塑造,而是舞劇該由誰在屈原身旁擔綱女首席!舞劇《屈原》走的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后期郭沫若創作話劇《屈原》的路子,女首席由郭老虛構的“嬋娟”來擔綱——舞劇“屈原”和“嬋娟”的飾演者是那是“青春”得“不要不要”的李恒達和蓋一坤。
其實我們的舞劇創作并不熱衷歷史文化名人——我指的是主要靠自己“文名”行世的歷史人物。就舞劇創作的藝術特性而言,鑒于我們表現的歷史文化名人均為男性,如何為之匹配女首席就是個“難題”——近年來舞劇創作中出現的古代文化名人,如《孔子》《洛神賦》(曹植)、《王羲之》《桃花源記》(陶淵明)、《李白》《杜甫》《東坡海南》《唐寅》等都面臨這個難題,現代文化名人《李叔同》《梅蘭芳》也會與之遭遇。此外,就文藝創作“借他人之酒杯,澆心中之塊壘”的表意模態而言,對歷史文化名人的形象塑造大多在“懷才不遇”“憤世嫉俗”“達則兼濟,不達則獨善”的套路中徘徊——讓人覺得我們舞蹈界的“文化人”怎么也如此“矯情”了。
李白是詩仙。十五年前的2003年,為紀念李白誕辰一千三百周年(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廣東實驗現代舞團創作了大型現代舞劇《夢白》。用時任團長兼該劇總導演高成明的話來說,此舉是想“尋找一個能讓人穿越中國某一文化特質的時空隧道”。筆者在當時的舞評中寫道,“《夢白》的總導演是高成明,和他一起編舞的侯瑩、劉琦、龍云娜都是久經沙場、頗負盛名的中國現代舞者……高成明垂青于《白之仙》,他讓舞者都著白衣,五六名舞者圍繞著站在臺中一小圓臺上的舞者行走,那步態飄飄欲仙的、無休無止的……飄行的舞步加上了胸臂的盤擰,似乎要借助‘自然'來表現一種‘超然'。侯瑩的舞者棄‘白'就‘黑',這是她所理解的《白之狂》,似仙的飄逸在這里轉換成如狂的頓踏……劉琦將《白之醉》帶到了現代酒吧,舞者當然也就‘多彩'起來,只是那‘爵士化'的悸動讓‘李白'莫名其妙。好在李白是醉了,自覺酒吧‘刺青蹦迪者'比自己的‘散發弄扁舟'有更強烈的個性。《白之憤》被龍云娜闡釋為‘上又上不去,下又下不來'的生存狀態,這大概是擺脫了‘我是誰'這類追問的現代人,想選擇‘我成為誰'卻又無從選擇的處境”(《穿越中國文化特質的時空隧道——大型現代舞劇〈夢白〉觀后》,載于《中國文化報》2002年3月20日)。
之所以將大型現代舞劇《夢白》作為參照,是因為它在塑造李白形象時是完全不用考慮“女首席”的;所謂“仙”“狂”“醉”“憤”,是編導對李白形象特征的要素擷取——這可能是“現代舞劇”的表意方式,即它要讓觀眾在各自的期待視野中自由拼貼、自覺引渡。但“民族舞劇”似乎不宜如此,即便是事件相對隔絕的“島嶼”,也要在敘說中凸顯相應的“地緣”,要通過“地緣”延伸的大陸架去聯通“島嶼”之間的陸基。民族舞劇《李白》顯然是尊重這種民族欣賞習慣的。在《仗劍夢》《金鑾別》《九天闊》三個大的幕次中明確了九個節點;此外,還有“序”起于《月夜思》和曲終(尾聲)于《鵬捉月》。這個呼應的首、尾很有意思:《月夜思》是詩意情境中主體的思緒,由此而流淌出李白思緒中的“李白”;而《鵬捉月》是主體思緒中詩意的情境意象,由此而升騰起李白意象中的“李白”——這便是他在《大鵬賦》中所言:“刷渤澥之春流,晞扶桑之朝暾……運逸翰以傍擊,鼓奔飚而長驅……”
由于以《月夜思》為“序”,決定了該劇以“反思”,或者以度盡“人生劫波”的回憶開啟:作為第一幕的《仗劍夢》,已全無“擊筑飲美酒,劍歌易水湄……少年負壯氣,奮烈自有時”(《少年行》)的氣象。這一幕的三個節點,編劇江東名之曰《老驥憤》《囹圄悲》和《夜郎淚》。三個節點的起始之點,是大唐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此時已進入人生暮年的李白,居然又“烈士擊玉壺,壯心惜暮年。三懷拂劍舞秋月,忽然高詠涕泗漣”(《玉壺吟》)。舞臺后區是三排列陳的黑甲兵士,而前區是由上場門向下場門不斷“告急”的信使……不明就里的李白以為“永王幕府”也是“大唐血緣”,誰知站錯了隊,入錯了伙……舞臺處理倒是簡潔:黑甲兵士虎視眈眈,白衣李白驥志勃勃;正當李白揚己之長、高歌“永王東巡”之際,上場了若干錦衣衛士將“幕府一伙”團團圍定……率領錦衣衛士的算是劇中的一個次級主角,被稱為無名無姓的“臣”(似乎是“李林甫”);“臣”指揮錦衣衛士將李白拿下,投入囹圄……

舞劇《李白》劇照
第二個節點《囹圄悲》由此導入,“臣”的趾高氣揚與“白”的忍辱負重構成鮮明的動態反差和形象對比。由《老驥憤》而《囹圄悲》的空間轉換,不僅是由于舞者動態隱喻的情境變化,更是由于天幕上收放自如的矩形“視覺式樣”的變化——作為水墨構圖的舞臺背景,取的是李白《望天門山》的詩歌意象,所謂“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自此回。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在導入《囹圄悲》之時,矩形“視覺式樣”由于四邊黑幕的收縮,最后形成象征“囹圄”的“獄窗”……這種對應情境變化的背景變化很有意思,矩形“視覺式樣”的自如收放,似乎在引領著觀眾的“理解”預期;就這樣,被羈押之后的李白又在矩形“視覺式樣”的擴放中踏上了流放之路——背景擴放后,從上場門橫向走出一列父老鄉親,李白融入后折向后區,又蜿蜒前行……觀眾很明白這便是這一幕的第三個節點《夜郎淚》。
很顯然,由第一幕上述三個節點的自如轉換,已經顯示出舞劇《李白》的敘事風格——這就是不必將其擱置在必要的人物關系中,而是借情境的自如轉換來敘說李白的處境,敘說李白在那些處境中充滿悲情的心境。這與近年來廣受好評的舞劇《杜甫》形成了迥異的敘事風格。我們知道,杜甫與李白齊名,對峙于唐詩之巔峰。說“對峙”,是說二人從詩風到人格都有極為顯著的差異。歷代評說李、杜者不乏其人,但明代胡應麟的《詩藪》卻慧眼獨具,認為:“才超一代者李也。體兼一代者杜也。李如星懸日揭,照耀太虛。杜若地負海涵,包羅萬匯。李唯超出一代,故高華莫并,色相難求。杜唯兼綜一代,故利鈍雜陳,巨細咸蓄。”筆者曾評說由周莉亞、韓真擔任總導演的舞劇《杜甫》,指出:“舞劇《杜甫》‘情境意象'的塊狀結構方式,隱隱對應著杜甫‘情感亂石'的集成、調和方式——如梁啟超所言杜甫:‘他的情感,像一堆亂石,突兀在胸中,斷斷續續地吐出,從無條理中見條理……'”(《情圣的痛苦詩史的根——大型民族舞劇〈杜甫〉觀后》,載于《藝術評論》2016年第7期)
舞劇《杜甫》的總體結構分上、下兩篇。上篇由“求仕行”“麗人行”“兵車行”和“難民行”四大板塊建模,下篇的四大板塊是“亂世行”“長恨行”“別離行”和“農樂行”。雖然總體上也都取自杜甫的“詩意”,但這些“詩意”似乎更關切大唐王朝底層人民的現實,格外聚焦于“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如前所述,由韓寶全擔任總導演的舞劇《李白》,主體部分是三大幕次九個節點,可以說也是具有某種“板塊”結構特征;但舞劇《李白》的板塊建模,居然是由第一板塊李白流放“夜郎”途中的“追憶”,結構了舞劇的第二板塊《金鑾別》。我們的舞劇創作很清楚自己具有“自由時空”的優勢,通過“追憶”或者“暢想”之類的“化出化入”并不乏見;但像舞劇《李白》這樣以全劇三分之一的體量“化出化入”,倒是十分罕見的。這個由第一板塊“化出”的第二板塊也有三個節點,即《金鑾狂》《花想容》和《翰林別》,講的無非也是歷代文人如何因“恃才傲物”出場、并終歸“喪意失寵”那點事。
二幕《金鑾別》的首個節點是《金鑾狂》,這個“節點”的表現有點兒“套路”(想想舞劇《杜甫》的《求仕行》就能明白),無非是殿上群臣人滿為患,但均為酒囊飯袋之屬、阿諛奉承之輩……只所以會有這種“套路”,無非是想反襯李白(也包括前述杜甫)的鶴立雞群、不同凡響。我們注意到,一幕《仗劍夢》使李白“因夢得咎”的那個“臣”,成了“殿上群臣”的“頭領”——我們的編導要為李白的“失意人生”找一個“得志小人”做對頭(這讓我們想起舞劇《孔子》中也有這樣一個“臣”來讓孔子“夢碎金鑾”)。所謂《金鑾狂》是狂在“阿諛”之風盛行,但此時的李白似乎并不能“超然脫俗”。第二節點《花想容》在由“宮女舞”引出“貴妃舞”后,李白也得以用“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來取悅圣上,遠沒有宋代詞人“奉旨填詞柳三變”的柳永那般灑脫。接下來的《翰林別》這一節點,舞臺上呈現的是群臣為“不設防”的李白“下套”,讓其整日醉醺醺、昏沉沉、飄忽忽……說實話,這樣的李白如何能不“下崗”——我想說的是,雖然這一幕次是由李白“追憶”而來,但其實并未表現出編劇在字幕上言說的“家國情懷”;只是在“下崗”后,那段在《將進酒》吟誦相伴下的舞劍,才令人看到李白原本還有“停杯投筋不能食,拔劍擊柱心茫然……長風破浪會有時,直掛云帆濟滄海”的一面。但是,《將進酒》中的李白,其實也無所謂“家國情懷”,他的“鐘鼓饌玉不足貴,但愿長醉不愿醒;古來圣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是李白對圣上“拜拜了,您那!”的自我解脫。
舞劇的第三幕《九天闊》,是李白從“追憶”中回到“流放”的現實中,這個“追憶”的意義是李白終得于“放下”了。我以為,這樣來解讀第二幕——不說他的“家國情懷”而說他的“長醉不醒”,說因他的“放下”而成就了一代“詩仙”或許更有意義!這一幕的三個節點分別是《獨酌月》《歸去來》和《孤云閑》,流放中的李白只能“開懷暢飲”或者說借“暢飲”而“開懷”,當一個“留名后世”的飲者。《獨酌月》這一節點,編導最下功夫的還是情境的營造,舞劇最好看的兩段群舞都在這一情境中——一段是《白纻舞》,另一段是《踏歌》。這兩段都是舞史記載中盛行于魏晉、廣布于江南的舞蹈。史載“《白纻舞》起于吳孫皓時作”,晉代《〈白纻舞〉歌詩》的描繪是:“輕軀徐起何洋洋,高舉兩手白鵠翔,宛若龍轉乍低昂,凝停善睞容儀光,如推若引留且行,隨世而變誠天方。”至南朝(宋)劉爍《〈白纻舞〉詞》,風貌依然是“仙仙徐動何盈盈,玉腕俱凝若云行;佳人舉袖耀青娥,摻摻耀手映鮮羅;狀似明月泛云河,體如清風動流波”。看得出,舞劇編導在著力體現舞詩描繪的風貌。
與女子群舞《白纻舞》的“月泛云河”“風動流波”相比,男子群舞《踏歌》由李白《贈汪倫》詩意起興:“李白乘舟將欲行,忽聞岸上踏歌聲”——民間的“踏歌”為文人關注,在唐代有李白和劉禹錫,后世以明代湯顯祖為最,留下了“醉與踏歌清夢曉,老拼吟眺白云天”“醉里踏歌春欲遍,風光長屬太平人”等佳句。舞劇中的這般《踏歌》似乎也點“醉踏”的味道,但熟悉孫穎先生作品的人,都能看出此間有男子群舞《謝公屐》的典型動態。我由此想到孔德辛編導舞劇《孔子》,被稱為《采薇》的一段女子群舞,也復現著孫穎女子群舞《踏歌》的典型動態——因將《踏歌》舞者綠色舞裙轉換為《采薇》舞者粉色舞裙而被稱為“粉踏歌”。當然,《白纻舞》和《踏歌》這兩段群舞仍然是為李白的心境鋪墊,因為李白本人也留下了《白纻辭》(三首),從“且吟白纻停綠水,長袖拂面為君起”到“郢中白雪且莫吟,子夜吳歌動君心”再到“揚眉轉袖若雪飛,傾城獨立世所稀”……由此而走向李白此時的典型心境《月下獨酌》。關于《月下獨酌》這一主題,李白留下的詩竟有四首。除我們都很熟悉的“花間一壺酒,獨酌無相親”外,還有“天若不愛酒,酒星不在天”等。如果說,“花間一壺酒”的詩眼在于“暫伴月將影,行樂須及春”;那“天若不愛酒”的詩眼則是“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借著這個“酒意”,編導延伸出《獨酌月》的人生理念,將李白的人生旨趣推向了《歸去來》《孤云閑》兩個節點,并最終推向尾聲《鵬捉月》——以一種最浪漫的情懷來化解其沉溺現實的“抑郁”!
李白李太白乃一代詩仙、千古奇人,將其塑造為舞劇形象或許也可以有其他的手法,但眼前的舞劇《李白》應該說也是一個不錯的表達。它的三個幕次也形成了總體結構的A、B、A。我唯一覺得不爽的是,劇中李白“喝酒”太多——特別是第二幕《金鑾別》的“狂飲”,掩蔽了編劇總在強調的“家國情懷”。李白的確曾想“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奮其智能,愿為輔弼……”,但他不愿走科舉考試的道路,想憑自己“日試萬言,倚馬可待”的文才入仕;故他雖有“才高一代”的詩名,但做不了白居易、元稹等參政議政所做“策論”……由是我想,我們做舞劇《李白》是否非要做他的“家國情懷”——這方面他即便有此心也未必有此才!正像我當年評述舞劇《孔子》所言:“怎樣定位孔子,我認同周予同先生的看法,即孔子‘是一位實際的教育家,是一位不得志的政治思想家,是一位鉆研道德問題的倫理學家'。尊奉孔子為‘至圣'的錢穆先生,晚年卻蔽之以一言:‘孔子在中國歷史文化上之主要貢獻,厥在其自為學與其教育思想之兩項',因為‘孔子之政治事業已不足全為現代人所承襲'。”(《舞劇〈孔子〉的文化擔當》,載于《舞蹈》2013年第10期)雖然舞劇《李白》是由李白葬身之地的安徽省馬鞍山市打出的一張地域文化名人牌,但我們還應審慎考量這個“名人”的“文化擔當”和“價值取向”,因為李白不僅是中華引以為豪而且是世界為之矚目的“文化名人”——這無關于他“申管晏之談,謀帝王之術”的臆想!
順帶提一筆,我們舞劇對古代文化名人的表現,從目前來看主要有以下三種方式:一是以某一代表性的文學篇章為底本,比如曹植的《洛神賦》和陶淵明的《桃花源記》;較早也有屈原的《九歌》,遺憾的是并未將屈原融入其中。二是以一系列的文學(主要是詩歌)作品為線索,比如舞劇《杜甫》和舞劇《李白》;但這一類又有注重客觀事件(《杜甫》)和注重主體心境(《李白》)之分,這或許本身是由“詩圣”杜甫的現實主義手法和“詩仙”李白的浪漫主義情調所決定。三是以文化名人的人生(整體人生或片段人生)為敘說對象,比如《孔子》《唐寅》和《東坡海南》,其中也間或會擷取其文化名人的名篇名段。針對這類古代文化名人的創作,我們需要注意三點:一是古代文化名人中女性的缺失,在此姑不詳論;二是文化名人的實指與其對抗力量的虛擬(如王、妃、臣等人物的設置)已有模式化傾向,需要關注;三是所擷取的文化名人似乎都有“從政情結”(美其名曰“家國情懷”)且又“不為政用”,當這成為一種“現象”之時會否有“弦外之音”?值得反思。最后,想談一點這類舞劇創作人物關系構成的看法:其中《孔子》中的孔子、《桃花源記》中的陶淵明、《李白》中的李白,均無與男首席相關的女首席,但這容易造成舞劇人物形象塑造色彩感的不足。因為舞劇的塑造人物,總是要人看到塑造人物之“舞”和色彩豐富之“舞”的魅力,而《孔子》中的“妃”、《李白》中的“貴妃”作為角色之舞總給人“斷片”之感。不過,這類舞劇創作在探索“女首席”之時,也改變了男、女戀人同為“首席”的模式化傾向:除《杜甫》是老夫老妻串聯“情境”外,《屈原》的女首席是屈原理想中的嬋娟,《洛神賦》的女首席是曹植理想中的洛神,都體現為某種“人格”理想的外化;《唐寅》用唐寅的情人沈九娘做女首席,《東坡海南》則用蘇東坡亡妻王弗做女首席,的確體現出別樣的魅力……這樣就給舞劇的人物關系帶來了許多變數(比如《杜甫》中出現杜甫眼中的“杜甫”——第二自我),使得舞劇突破既定模式去塑造人物,拓寬了舞劇塑造人物的限域,也拓寬了大眾對于“舞劇”形態的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