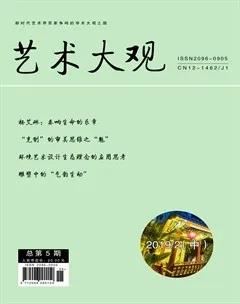20世紀初國畫復活運動中的黃賓虹研究
摘要:20世紀初,以上海為中心的中國畫壇發生了國畫復活運動。以黃賓虹為代表的學者,主動把中國傳統金石學與民學思想介入到西方新知系統,強調國畫對精神的表現功能,提出了“內美”這一概念。通過這一途徑,實了中國繪畫現代轉化的目的。
關鍵詞:國畫復活運動;黃賓虹;民學;現代轉化
二十世紀前半葉,我國社會風云動蕩,社會形態在外部列強的欺壓下和內部民主革命的潮涌中發生了激烈的轉捩。此時的中國,“國粹畫”“國畫”稱謂亦日見流行。與“國畫”一詞相關的概念的提出,亦是在中西文化砥礪的時候。據明人顧起元撰寫的《客座贅語》所載著名傳教士利瑪竇的話:“中國畫但畫陽,不畫陰”[1],這是史料可見最早關于“中國畫”的記載。此時的利瑪竇以一個他者的眼光,觀察了中國傳統人物繪畫,并以歐洲油畫為參照系,對中國人物繪畫的風格特征進行了描述分析。此時的中華,還在“天朝上國,四夷來朝”的歷史軌道上慣性滑動,西方剛剛萌發近代化革命除了對當時的中國上層個別士大夫和少數帝王之外,沒有任何的影響。但隨著歷史車輪向前轉動,三個世紀之后的中國,則被已完成工業革命的西方深深撼動,“天朝上國,四夷來朝”的世界圖景徹底被打破。此時的中國,無論是政治體系與經濟生產,還是思想文化與日常生活都失去了原有的重心,陷入了“三千余年來一大變局”,社會各階層開始尋找救亡圖存之路。20世紀20年代,《新青年》的刊行,揭開了“新文化運動”的帷幕。這場運動高舉“民主”與“科學”兩大旗幟,不僅對傳統政治、倫理進行了批判,也深度影響到了文化藝術領域。“新文化運動”是一場傳統文化全面轉型的現代化變革運動。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指導者陳獨秀提出中國“美術”也要革命,要以寫實主義革“王畫”的命。此時世界畫壇也發生了巨大的變革,歐洲出現了“現代主義”繪畫,日本畫壇也出現了從洋畫、日本畫到南畫的劇烈變革。大量留學歐洲的畫家,以及各種美術期刊的出版,把歐洲與日本畫壇的變革信息帶回了國內。在這中西內外雙重壓力夾擊下,傳統中國繪畫一度陷入了被動的低谷。
一、“國畫”概念的生成與“國畫復活運動”
從現存的資料來看 , 最早使用“國畫”這個詞語的,可能是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時事新報》圣清的《論國畫》(連載)[2],但文章中處處透露出對于國畫的悲觀看法。
正當時人陷入崇拜以歐洲為標桿的“科學萬能”迷思之中,游歷歐洲之后的梁啟超卻觀察到了一戰之后的歐洲社會也存在著各種困頓和沖突,民生艱難。梁啟超認為這是歐洲彰顯物質文明,忽略精神文化之結果。在這樣的觀點影響下,讓國人重拾文化信心,成了當務之急,于是“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在這樣的歷史語境中,國內一些畫家也開始重新審視中國繪畫,從傳統思想(民學)和藝術(金石)內部尋找中國繪畫振興的門徑。
1921年,學者陳衡恪在其專論《文人畫之價值》中論證了傳統繪畫,特別是文人畫重在表現精神的時代價值[3]。與此同時,畫家汪亞塵在《近五十年來西洋畫底趨勢》中對當時中國畫缺乏思想表現和創造的現象進行了抨擊。[4]
1930年,豐子愷發文指出了中國繪畫引導了歐洲現代主義繪畫變革。
1933年,南社成員胡懷琛將其文《上海學藝概要》連續發表在《上海通志館期刊》上,并提出了“國畫”這一概念。在這系列文章中,作者敏銳覺察到了中國畫壇正在發生著的新動向,將其稱之為“國畫復活運動”,將其視為傳統中國繪畫浴火重生的新態勢。
在胡懷琛列舉的眾多“國畫家”中包含了一個為我們熟知的名字——黃賓虹。胡懷琛以跨語境的眼光對這些“國畫家”的作品做出了高度評價:“已能獨創一格,絕對不受舊法的束縛,在國際上曾經得到很好的名譽 ;有這些事實在眼前做證據,更使中國畫家確信中國畫有獨立存在的可能,不必一一模仿西洋。”[5]
二、“國畫復活運動”中的黃賓虹
根據黃賓虹研究專家王中秀先生的研究,20世紀20年代,正好處在黃賓虹繪畫風格的“濃墨法之變”和“虛實之變”時期[6]。西洋日本畫壇的劇變,以及國內畫壇對于傳統繪畫精神表達的復活,給正處在試圖綜合傳統繪畫南北兩宗風格特征以溝通中西繪畫的黃賓虹帶來了新的契機。黃賓虹曾在1912年的《真相畫報》敘中指出了歐洲寫實繪畫與中國北宗繪畫的相通性,展現了他對歐洲繪畫的開放態度,并試圖從中國傳統中尋找到一點與之相通的東西。[7]而劈面而來的新文化思潮,以及歐洲的“現代主義”藝術思潮,給黃賓虹帶打開了新的思考窗戶[8]。黃賓虹對《真相畫報》刊登不同國家繪畫的做法大為贊賞。他認為這樣能夠能拓展國人的視野,發揚國粹的精華,培養國人的品格和行為。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黃賓虹專注于對用筆中的虛實關系進行探求。1925年,黃賓虹在給友人畫的《嘉陵山水圖》上題跋道:“我從何處得粉本,雨淋墻頭月移壁”[9]。同年,他在《古畫微》中借用了清人王原祁之語:“實處轉松,奇中有淡,以意寫之,而真趣乃出。”[10]體現了他對筆墨虛實的思考。
黃賓虹在《藝觀學會征集同人小啟》中拈出國際學術對話的主題,即所謂“緬周圣多藝游藝之言,繹東儒客觀主觀之恉(日本澤村專氏來北京大學論畫謂形似是客觀,氣韻是主觀,卻從客觀的物象事實外表現主義)”[11],對國畫復活運動進行了呼應。
1914年底至1921年,在上海的黃賓虹參與《國粹學報》的編輯,并開始主編《時代》的副刊《美術周刊》。在此時期,黃賓虹開始思考“國畫民學”與國畫現代轉型的問題。“平民主義”是近代資產階級革命的思想基礎。我國明代中葉以后,隨著城市平民階層的壯大,體現這一階層審美趣味的作品和思想不斷涌現,出現了以李贄、湯顯祖等代表的思想家和文藝作家。在近代中國,隨著“新文化運動”席卷全國,用藝術陶冶大眾心智,敦化德育的思想亦開展起來。
1918年10月6日,黃賓虹在江蘇省教育會美術研究會成立大會上作了關于民學與國畫分析發言,他指出我國繪畫在周代之后,就有長久的民學傳統。[12]在這里,黃賓虹主要是指那些保留在平民階層的,尚未進入主流研究者敘事話語中的古代文化遺存,特別是古代金石篆刻。他承接了時人鄧實提出了“亞洲古學復興”[13]的口號,主張以收藏古印為研究的出發點,強調清代金石學運動的現代意義,作為國畫現代性轉化的門徑。他主動將中國古學介入到了西方新知系統之中。
在多數前人研究之中,由于黃賓虹深厚的舊學功底以及他于“折中派”的強烈批判,長期以來,他被視為當時畫壇中的“守舊派”。現在筆者把黃賓虹先生的思想和作用納入到跨語境的范疇中來考察,發現“守舊派”的定位不符合歷史的實際情況。黃賓虹認為學術界對外來的歐、日學術學習借鑒雖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能僅僅停留于對外來思想和藝術形式的借鑒,一定要“返本以求”,對看似“復古”的國畫復活運動,他表示要“鑒古非為復古,知時不欲矯時。”[14]他認為中國繪畫是“由里面生活——精神——產生出來的”,“形似是客觀,氣韻是主觀,卻從客觀的物象外表現主觀”。
這個時期,黃賓虹對于畫學的思考,保留在他與1928-1929年寫的《賓虹論畫》中:“藝襮于外,而道弸于中。綜其要旨,約舉‘虛實’兩字以該之。”對于“虛實”,黃賓虹進一步說道:“筆墨臨摹為實,而氣韻生動即虛矣。”[15]在這里,“虛實”突破了技巧的藩籬,上升到“氣韻”相當的審美判斷,使得千百年來“只可意會,不可言傳”的“氣韻”,變得“可以功力至”。于是,“氣韻”與“主觀”“神似”“虛”“思想”“精神”甚至“抽象”組合成了“內美”這一個大概念。值得注意的是,史料顯示,在他1929年論“五筆法”的《虛與實》中,還把“歐人以不齊弧三角為美術”和“虛”置于同一理念的平臺上,將中國本土“虛”的概念與之相溝通。這個“歐人”的前綴詞,使我們得以推知這一命題除了發自黃賓虹時傳統哲學和畫論“虛”的新認識以外,它還與此際西方方興未艾的格式特心理學的“發現”有著內在聯系。
黃賓虹關于“齊而不齊”中“不齊”的內在魅力,來自人的視知覺的功能。據格式特心理學的實驗發現,視知覺會自發地時刺激物加以組織,通過組織而生成的“形”從原有的結構中突現出來。換言之,對外界的一切,我們的視知覺是具有選擇性的。視知覺關注到信息會凸顯出來,形成“圖”;其他的信息退到后面,形成“底”。在“圖”和“底”之間會產生一種視覺張力,當觀察者把“圖”和“底”之間解讀完成,這種視覺張力就會消退,從而產生一種類似愉悅的感覺。視知覺對形的解讀是按“簡約”“完整”的原則進行的,如整齊而“封閉”的三角形、圓形,如對稱、平衡,等等。如果刺激物接近“簡約”“完整”圖形,解讀過程很快就會完成,這時觀者便會感受到愉悅。反之,如果這過程并不順當,視知覺會自動如將殘缺的缺口補完整,將傾針的圖形扶正,等等,總之將我們看來不舒服的東西改變成為完美簡約的。盡管解讀順當能很快地消除因利激而產生的視覺緊張,給人以愉悅,但伴隨而來著的是視覺的疲乏和注意力的他移,就像生活里看一幅一覽無余的畫面,很快便失去了興味一樣。反之,如果解讀不順當,刺激物的“形”離我們心目中完美的“形”距離太遠,瞬間無從將它或它們簡約為完美的易于接受的“形”,視知覺所產生的緊張使保持得較為持久,這種持久的緊張強化了觀者的好奇心和注意力,令他一探究竟的興趁更加濃厚。比如一種更復雜更不規則甚至顯得有些“丑”的圖形,會給人帶來更強烈的刺激性和更大的吸引力。因此,藝術(尤其是繪畫)要講究變化,要盡可能舍棄或德藏那些人們熟悉的東西,僅讓幾個關鍵的部分凸現出來,讓觀者“摸著石頭過河”,自行去組織成畫面,以便獲取更大的審美愉悅。拿人們熟知陳老蓮的人物畫為例,他有意把人物畫的和正常形態有較大的偏離,而這種偏離恰恰是我們百看不厭的。黃賓虹所說“齊而不齊”中“不齊”的魅力所在。
1948年8月22日,由趙志鈞整理記錄,發表在《民報》副刊《藝風》第33期上黃賓虹的《國畫之民學——在上海美術茶會講詞》可以視為他在國畫復活運動中畫學思想的總結陳詞。他指出:國畫要發揚民學,發揮自我精神,展現“內美”。[16]并用具備世界眼光的語調號召當時的藝術家不要有中西之分,要以主動的姿態進入到世界畫壇之中。[17]
三、結語
當下,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事業已經進行到關鍵時刻,而文化認同和文化自信在復興事業中顯得日益重要。以史為鑒,可以明得失。“國畫復活運動”是五四新文化運動之后,本土文化藝術家以主動的姿態應對時代變革,體現了當時的中國畫家們在反思與調整五四激烈的“反傳統”態度,堅持主張民族藝術的立場,通過積極地與西方藝術對話,努力探索國族藝術與文化新形態的構建,而不是簡單的“回歸傳統”和“堅守傳統”。而黃賓虹先生在融通了中外藝術文化之后,提出了“形似是客觀,氣韻是主觀,卻從客觀的物象外表現主觀”藝術觀點,在此基礎上更提出了“內美”的繪畫觀點。這與當時西方繪畫的主流觀點是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中國繪畫進入現代性,是主動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像之前西方學者費正清等人認為的簡單“刺激——反應”的后果。研究黃賓虹在國畫復活運動中提出觀點以及具體的作用,對于我們當下增強國人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認同大有裨益。
參考文獻:
[1](明)陸粲等.客座贅語[M].北京:中華書局,1987,04:第一九四頁.
[2]洪再新.展開現代藝術空間的跨語境范疇:探尋1920年代初上海的“國畫復活運動”的啟示[J].美術學報,2014(02):5-14.
[3]陳衡恪談道:“文人畫之要素:第一人品,第二學問,第三才情,第四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蓋藝術之為物,以人感人,以精神相應者也。有此感想,有此精神.然后能感人而能自感也。所謂感情移入,近世美學家所推論視為重要者,蓋此之謂也欽?”陳師曾.陳師曾中國繪畫史[M].北京聯合出版有限責任公司,2016,09:255.
[4]汪亞塵在文章中指出:“現在的中國畫,都是一種因襲的東西,絕對說不起創造兩個字,把自家思想的表現,都丟得干干凈凈。”劉海粟美術館,上海市檔案館編.上海美術專科學校檔案史料叢編第6卷美專風云錄上1912年11月-1952年9月[M]. 2013:389.
[5]胡懷琛.上海學藝概要[J].上海通志館期刊第1卷第4期,1933年3月。轉引自洪再新,展開現代藝術空間的跨語境范疇:探尋1920年代初上海的“國畫復活運動”的啟示[J].美術學報,2014(03):5-14.
[6]王中秀.黃賓虹繪畫歷程的時段描述(上)[J].榮寶齋,2009(05):99.
[7]王中秀.黃賓虹繪畫歷程的時段描述(上)[J].榮寶齋,2009(05):96.
[8]西方現代繪畫思潮向中國畫學靠攏,黃賓虹1923年初的《賓虹畫語》中這樣表述:“乃今彼都人士,咸斤斤于東方學術,而于畫事,尤深嘆美,幾欲唾棄其所舊習,而思為之更變,以求合于中國畫家之學說,非必見異思遷”.
[9]黃賓虹著.黃賓虹詩集[M].桂林:漓江出版社,2012,01:25.
[10]黃賓虹著;盧輔圣選編.黃賓虹藝術隨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01:43.
[11]黃賓虹著;盧輔圣選編.黃賓虹藝術隨筆[M].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01:79.
[12]上海圖畫美術學校編《美術》,1918年10月,引自增訂本該年月條目.
[13]《國粹學報》,1905年第9號,第1b頁.
[14]《國畫月刊》,1935年第一卷第4期.
[15]黃賓虹著.虹廬畫談[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01:8.
[16]黃賓虹談到:“君學重在外表,在于迎合人。民學重在精神,在于發揮自己。所以,君學的美術,只講外表整齊好看,民學則在骨子里求精神的美,涵而不露,才有深長的意味。”黃賓虹著.虹廬畫談[M].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2007,01:4.
[17]同上注,黃賓虹指出“現在我們應該自己站起來,發揚我們民學的精神,向世界伸開臂膀,準備著和任何來者握手!……將來的世界,一定無所謂中畫西畫之別的。各人作品盡有不同,精神都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