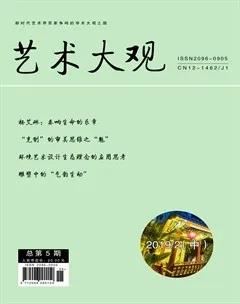失落“天使”

摘要:攝影系列作《天使》是崔岫聞的代表作之一,作品的主角是一名未婚先孕的未成年少女,背景通常是城市景觀。作品呈現(xiàn)了對于女性的脈脈溫情與真誠關(guān)注,飽含著普世性的情懷。本文以《天使,No.13》為例,圍繞女性身份,深入分析“天使”形象的成因與復(fù)雜性。
關(guān)鍵詞:少女;女性;天使;城市
從2006年起,崔岫聞用兩三年時間陸陸續(xù)續(xù)創(chuàng)作了《天使》系列攝影作品。作品的主角是一個未婚先孕的少女,作品背景取材自北京,運用了天安門廣場、紫禁城紅墻、人民大會堂、四合院等文化符號。而在《天使,No.13》(圖1)中,出現(xiàn)的是一片正在施工的工地和連綿的群山,青天白云。如果單獨討論這幅作品而不與系列作聯(lián)系的話,可以將其理解為城市化進程中的某個地域。作品最為搶眼的,是仰臥在畫面中央的少女——她的身軀已經(jīng)占據(jù)了這片“山河”。白色的睡裙透著青春誘人的酮體,與天光交相輝映,呈現(xiàn)出無辜的性感,左手隨意又“刻意”地放在了隆起的腹部上,而右手則奇怪地扣在地面上,似乎睡前經(jīng)歷過一番掙扎,又似乎在睡夢中還在掙扎。側(cè)臉清晰可見精致的妝容——面帶脂粉,淡掃 蛾眉,膚若凝脂,唇比紅桃,頰顯嫩杏。在她的表情中,感受不到一絲即將為人母的喜悅和期待,而是痛苦、無奈、隱忍。表面的單純無辜在一滴淚里轟然倒塌,開始慢慢顯山露水,呈現(xiàn)內(nèi)在的脈絡(luò)和傷痕。
每一幅《天使》都呈現(xiàn)出少女的不同狀態(tài),和《天使》系列的其他作品比起來,躺臥的少女顯得十分安靜,她的煩躁不安、彷徨無助都沉沉入睡,像是暴風(fēng)雨后的寧靜;在放大的身軀中除了綿綿不斷的悲痛和無奈等負面情緒,還有一絲絲神性,或者說是母性的光輝。這讓它區(qū)別于其他的系列作品。
那一滴垂下的眼淚就像蒙娜麗莎的微笑,讓人禁不住琢磨:她為什么哭?
一、父親的消失
背景中的吊車提示我們這是一個正在飛速發(fā)展的城市,環(huán)繞的群山在努力營造安全感的同時又顯得無足輕重。在這個語境中,占據(jù)主導(dǎo)地位的吊車、城市和山,都可以被解讀為男性的象征,具有建設(shè)性和強大的力量。但是顯然,這個環(huán)境并沒有給少女帶來她所期盼的保護,只是冷漠地運行著秩序,事實上他們也隔絕于兩個空間。當我們追問為什么少女只身一人的時候,吊車隆隆作響,間接回答了疑問。她的身邊沒有一個男人可以來保護她,和她的孩子——她是個單親媽媽。這個身份意味著她將承受來自社會的巨大壓力。這塊撕不掉的標簽不僅會讓她未來的學(xué)業(yè)、工作受到影響,并將使之墜落到中國社會婚戀價值體系的底端。而如果她選擇流產(chǎn),則會面臨另外一重痛苦:身體上的痛苦,失去孩子的痛苦。這亦是一種“貶值”。
父親形象為什么會缺失?我們可以猜測一百種可能,但結(jié)果都是同樣的:他不在。父親在作品中缺席,取而代之的是具有父性特征的城市景觀。在冰冷的公共空間中展現(xiàn)柔軟而單薄的肢體,暗示著她所需要的安全感得不到保障。
二、被城市放逐的天使
少女本來應(yīng)該躺在臥室里,但作品中卻以天為被。何故?
在一個陌生的公共空間中睡覺,暴露自我,顯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崔岫聞將原本具有安全感的空間置換成一個流動空間,放大二者之間的矛盾與不協(xié)調(diào),借此表達少女內(nèi)心的孤寂彷徨,并通過“不安”的制造來暗示未來的單親媽媽生活的苦澀與艱辛。父親的缺席使得供應(yīng)物質(zhì)生活的關(guān)鍵角色無人扮演,單親媽媽既要養(yǎng)育幼兒,還要維持家計。
共和時代的政治家徐世昌(1855 年—1939 年)談起自己童年喪父的情景,那是在十九世紀中期:“父歿時,年甫七歲,弟僅五齡,家道中落,賴母氏劉太夫人,支持門戶,撫育成人。”晚清經(jīng)學(xué)家柳詒徵(1880 年—1961年)曾提及父親去世后,他們?nèi)娃讚?jù)的程度,“少時候談不到營養(yǎng)。餐時經(jīng)常只有塊紅醬豆腐,母親姊弟三人賴此下飯”。[1]
而在制度上,也曾經(jīng)存在著對于這個群體的偏見,她們的孩子連上戶口都要頗費周章。來自現(xiàn)實的種種壓力,使還沒有招架之力的她“再也不想看到外面的世界和現(xiàn)實,也不愿意面對或是受到世界的質(zhì)問。”[2]
三、不登大雅之堂,卻占據(jù)山河中心
對于每一個懷抱著傳統(tǒng)價值觀的中國家庭來說,一個未婚先孕且被戀人拋棄的女兒已經(jīng)構(gòu)成讓他們蒙羞的充分理由,從此女兒不登大雅之堂。但又因為無法徹底遺忘而被故意忽略和遮蓋,淪為邊緣人物。家族和社會都因為這個群體太過刺眼而自動為其添加“隱身衣”。但崔岫聞偏讓她像維納斯一樣橫臥在城市之上,置于山河中心,迫使觀者無法躲開視線,不得不觀看和審視。這暗示著:未婚先孕、單親媽媽的問題日益凸顯,已經(jīng)成了具有普遍性的社會問題;即便“聚光燈”曾經(jīng)刻意回避她們的存在,但她們的痛苦依然真真切切地存在著。她們代表著社會的一處傷口。最大的矛盾就在于:當這個城市面貌日新月異的時候,尚殘存著流淌千年的婚戀價值觀。
觀看層面的“迫使”,也是一種對于男性的視覺挑戰(zhàn)。
作品中呈現(xiàn)的她,是一具已經(jīng)性覺醒的女性軀體:她的白色睡裙單薄而不單純,處處精致打理的妝容細節(jié)都透露出少女正在逐漸成熟;她在本應(yīng)美好的年紀,讓自己從少女蛻變成了少婦。也許并不完全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在某種程度上,她是主動將自己交出的。這是可以引誘人犯罪的魅力。在俄裔美國作家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洛麗塔》中,戀童癖亨伯特將“小妖精”定義為“九到十四歲”的少女,他也正是這么稱呼他所迷戀的12歲少女洛麗塔(Lolita)。
崔岫聞就這么“不懷好意”地,將這只“小妖精”推到了中心。這個令人著迷的矛盾體混合了性感與無辜,誘惑與單純,成熟與稚嫩,艷麗與單薄,主動與被動。
現(xiàn)實不堪如此,為什么還要將作品名為“天使”?
(一)通常,我們會將那些自己愛的人,或者具有單純美好品質(zhì)的人稱為“天使”。女孩也許被愛過,也曾經(jīng)是純潔的天使。
(二)盡管現(xiàn)實中有可能被唾棄,但是在崔岫聞的畫面中,女孩依然美好,依然是可愛也值得被愛的天使;相比于冰冷的現(xiàn)實,這一稱呼更像是溫柔的撫慰,輕輕地用羽毛拂過面龐。不出于憐憫的溫柔,是一種莫大的善意。
(三)盡管因為“隱身”而容易被忽略,但她肚子里的胎兒,也是天使;在畫面的四分之三處,她的左手引導(dǎo)著視線,與天空的光線呼應(yīng),像是一種神圣的召喚。此刻,少女成了圣母,而胎兒成了天使。
只不過,這個“天使”矛盾體并不天然,她是經(jīng)過拼貼改裝創(chuàng)造出來的。崔岫聞在表達了女性溫柔的基礎(chǔ)上,還轉(zhuǎn)換了視角,將她塑造為男性眼中的“小妖精”,一個性對象,從消費文化的角度來講,她又是一個取悅男性的玩偶。但是現(xiàn)實生活中很難看到一個如作品中的孕婦。實際上,崔岫聞是把具有性吸引力和喪失性吸引力的不同女性狀態(tài)同時疊加到了模特的形象中。
《洛麗塔》中的洛麗塔,男性情欲的化身,在愛她的亨博特眼中,她媚若無骨,一舉一動都在挑逗和引誘他。某個無所事事的夏日午后,十二歲的洛麗塔趴在草地上看書,被噴水器澆透了也依然樂在其中,連衣裙緊緊貼著她的胴體,顯露出曼妙曲線,兩只玉足來回擺動。她本身似乎對自己的性感有所察覺,又毫不在意,渴望被關(guān)注,又不費力氣去討好。這種介于“yes or no”之間的灰色地帶,正好戳中了亨博特的心坎,這一幕堪稱電影史經(jīng)典。而當她懷孕之后,身材走樣,眼神渙散,發(fā)型散亂,穿著寬松隨意,當初的性吸引力與活力在她身上已經(jīng)被懶散隨意的氣質(zhì)替代。
我們可以理解為:崔岫聞把兩個不同時期的洛麗塔糅合在了一起。她曾表示自己嘗試把成年女性的心理結(jié)構(gòu)放在小女孩身上,幼女承載的就是一個女人成長的結(jié)果。同時,矛盾的少女還包含著她的視角和想象。這些女孩可能被視為藝術(shù)家與她自己成長過程中各個不同階段的身體、心理與情感發(fā)展經(jīng)驗的投射[3],而非完全表現(xiàn)她者。
此外,模特的選擇與合作過程,同樣是作品的意義延伸部分。第一位啟用的模特,成長在中國,父母擔(dān)心拍攝不利于她的身心發(fā)展,于是退出拍攝計劃。第二位模特,五歲移民澳大利亞,在那里住了八年,父母對藝術(shù)的認知和理解,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女兒的價值觀。后來崔岫聞一直跟蹤著模特的成長歷程,發(fā)現(xiàn)第二位模特也走上了當代藝術(shù)的知識生產(chǎn)道路。兩個小模特折射出了不同的價值觀。
“天使”形象是社會中未婚先孕的年輕女性代表,投射了崔岫聞對自我成長的思考,寄予了她對女性的脈脈關(guān)懷,推動觀者透過天使的眼淚,看到更深廣的社會。
參考文獻:
[1]熊秉真,呂妙芬主編.《建構(gòu)的感情——明清家庭的母親》,選自《明清思想與文化》[M].世界圖書出版公司.
[2]呂澎,葉彩寶編.圖像精神與文本敘事——崔岫聞藝術(shù)檔案[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52.
[3]呂澎,葉彩寶編.圖像精神與文本敘事——崔岫聞藝術(shù)檔案[M].中國青年出版社,2016: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