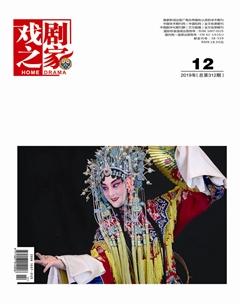新媒體時代下“粉絲”過度參與式追星引發的弊端及影響
張婧
【摘 要】新媒體時代打破了傳統“粉絲”間的各種障礙,賦予“粉絲”群體更多的凝聚性和發聲權,從而形成了現代網絡“粉絲”社群,并由此催生出“粉絲”經濟。盡管如此,過度參與式追星還是產生了一些弊端,而這些問題最終會導致“粉絲”經濟的連鎖反應,影響到“粉絲”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
【關鍵詞】新媒體;“粉絲”;參與式;“粉絲”經濟
中圖分類號:G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9)12-0204-03
一、新媒體時代下“粉絲”社群的崛起
隨著新媒體時代的到來,網絡平臺逐漸從內容發布平臺發展為社交平臺,社會化網絡將原本虛擬的網絡空間以一種極致化的方式真實地融入人們的現實生活,打破了“粉絲”間時空的障礙,同時改善了“粉絲”間信息溝通的效率,將“粉絲”圈子“晉升為一種游弋于真實與虛擬之間的全球性文化”[1]。而處于社會化網絡中的“粉絲”更是擺脫了地域、時間、身份、階層等因素的限制,使自身的地位更平等、群體更為廣泛[2]。這樣的“粉絲”群體就慢慢形成了現代“粉絲”網絡社群。較之傳統傳播模式及前網絡時代,社會化網絡中形成的“粉絲”社群聚合性更強,也更有凝聚力和號召力,并且在眾多網絡社群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并借助互聯網的優勢,形成自己的運行機制和特點,正在參與和滲透在娛樂產業的運行過程中。可以說,新媒體時代造就了現代“粉絲”社群,而“粉絲”社群又推動了我國“粉絲”經濟的蓬勃發展。
二、現代“粉絲”社群追星的特點
在這樣社會化互聯網環境下,“粉絲”社群與偶像的關系變得逐漸平等起來,加之新媒體產生了大數據時代,演員自身的商業價值更多地體現在自己在網絡中獲取的關注和流量,而為偶像做數據貢獻流量的工作則責無旁貸地落在了“粉絲”社群身上。于是,“粉絲”對于偶像的愛從過去在大腦中的臆想幻想、前網絡時代僅需支持票房,到如今變成了具體客觀且可量化的數據。在為偶像打榜做數據的過程中,“粉絲”也切身參與了“偶像生產”的環節,對于偶像在網絡間的宣傳模式熟諳于心,因此,現代“粉絲”的追星模式體現為參與式追星,“粉絲”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體現。當然,這種參與性與詹金斯[3]提出的“粉絲”參與性有所不同,現代“粉絲”社群的參與不局限于對影視劇文本的改編以及同人文的制作中,而是體現在積極參與偶像的打造工程。在其參與式追星的過程中,“粉絲”的在這個過程中,現代“粉絲”社群表現出了“線上”+“線下”復合式追星模式(圖1)。
如圖1所示,依托互聯網的聯通性和交互性,現代“粉絲”社群主要活動的大本營都集中在線上,他們需要為偶像做數據、攢積分,還要為各項人氣打榜投票,這些都是現代“粉絲”的日常;如果遇到偶像有作品問世,“粉絲”們還需要不遺余力地采用各種方式進行宣傳,并帶動大量路人“轉粉”;更重要的是,在網絡社群交際的過程中,現代“粉絲”承擔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職責就是為偶像反擊網絡暴力,進行反黑活動。由于網絡交際匿名性與娛樂圈名利場等多重因素的影響,偶像明星往往是網絡暴力主要攻擊的對象之一,為了維護偶像聲譽和人氣,現代“粉絲”社群不得不在反黑一線進行戰斗,并在此過程中形成了專門的反黑社群,并產生了約定俗成的反黑攻略,針對不同程度的黑料采取不同的策略(圖2)。
除了在線上積極為偶像分擔宣傳任務,線下“粉絲”們也需要承擔大量的工作。出席偶像各種活動的線下應援活動是偶像人氣的又一體現,各家“粉絲”社群都有自己別具一格的口號和名稱,同時也會通過“粉絲”眾籌的形式購買禮物和應援物品為偶像助力。除此之外,以偶像之名做公益也是現代“粉絲”社群發揚光大的粉圈的傳統行為。“粉絲”們仍然通過眾籌或者捐款的形式籌集到一定資金去做各種各樣的公益活動,如90后流量小生鄧倫的“粉絲”社群統計,2018年,不同“粉絲”社群及站子完成的社會公益活動多達四十余次,募捐金額高達2222元。
在這樣“線上”+“線下”的復合式追星過程中,“粉絲”們不僅縮短了和偶像之間的距離,切身參與了偶像的打造,見證偶像成名不易的同時,也把偶像的成功計入自己的努力成果。因此,“粉絲”逐漸對偶像形成了如母親般的責任感。他們不允許任何人做出他們認為傷害偶像的事情,甚至想自行決定偶像的事業發展和資源類型,在“粉絲”心目中,偶像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神靈,而是需要自己悉心照拂的小寶寶。然而,這樣的參與式追星還是呈現出難以避免的弊端。
三、“粉絲”過度參與式追星出現的弊端
(一)情感強烈卻難以約束,造成娛樂資源短期內過度集中。“粉絲”與偶像之間的關系主要是通過對偶像的情感投入來維系的,這也是“粉絲”存在的意義[4]。因此,無論過去還是現在,也不論追星形式和環境發生了何種變化,唯一不變的就是“粉絲”對于偶像無私且強烈的情感付出。以現代“粉絲”社群參與式追星為例,他們日常承擔了偶像人氣的建構、宣傳和維護工作,還要精心策劃線下的各種“粉絲”活動。對于打造偶像的模式也是熟諳于心,在某些層面甚至達到了專業水準。然而與“粉絲”無私投入相矛盾的也恰恰是這份感情,因為這種虛幻的情感不受任何法律、道德的約束,也沒有任何時間上的保障。“粉絲”們經常上演著今天為偶像利益與別家“粉絲”甚至媒體吵得天翻地覆,但是明天就移情別戀,將情感轉向另一個偶像。或者當偶像做出某些“違背”“粉絲”追星初衷的行為,例如公開戀情或者曝出緋聞等,就會毫無顧忌地“脫粉”。這樣極不穩定的感情投入會使得處于大數據時代下的“流量小生們”時刻處于“危機”下,畢竟,穩定的“粉絲”社群是偶像們在網絡中的人氣保障,也是衡量其商業價值的重要指標。因此,為了能在“粉絲”情感付出期獲取其最大的支持和回報,偶像及團隊會在當紅時盡可能爭取一切資源,這一方面會造成娛樂資本的過渡集中;另一方面也會造成偶像過度透支的情況。久而久之,影視劇作品的文藝性和觀賞性就會受到直接影響,對于演員自身的成長也會造成極大的隱患,這對于娛樂產業的健康發展是極其不利的。
(二)易受外界力量影響,網絡暴力事件頻發。在網絡環境中,“粉絲”們的身份認證門檻極低甚至是無門檻,任何人都可以“某人粉絲”的身份自居,這就為網絡“粉絲”社群在互聯網中的生存埋下隱患。不少人可以利用“粉絲”的身份或者借助“粉絲”的力量在“粉圈”中散播某些信息,而“粉絲”由于缺乏在網絡中辨別信息真偽的能力,因此容易被外力操控或者引導,做出一些自認為是在維護偶像的事情,而正是這種所謂的“正義”很可能會演變成可怕的網絡暴力事件。盡管涉及明星的網絡暴力事件形成原因眾多,但是由于“粉絲”社群具有凝聚性和群體性等特點,因此由“粉絲”參與的網絡暴力事件往往持續的時間更久,傳播范圍更廣,影響也更為惡劣。例如,2018年8月,隨著大型古裝玄幻劇《香蜜沉沉燼如霜》播出,劇中幾位主演的“粉絲”就因為自己偶像在劇中的演技、戲份及番位產生一定矛盾,在營銷號的引導和相關制作單位的縱容下,“粉絲”之間的罵戰日益升級,從對劇中人物的評論上升到對演員本身的言語傷害,最終變成影響惡劣的網絡暴力事件,引發了眾多網民關注,劇中幾位青年演員鄧倫、楊紫和羅云熙多次因“粉絲”罵戰登上新浪熱搜話題榜。最終,演員鄧倫的工作室不得不發出律師函來保護藝人的聲譽。然而,截至該劇播出近半年,有關《香蜜沉沉燼如霜》演員的網絡“粉絲”暴力事件絲毫沒有任何減弱和結束的勢頭,甚至劇中幾位演員的一張同框照片都會引發新一輪的罵戰。當然,不管是被利用,還是樂在其中,“粉絲”社群本身不需要承擔任何責任,也不用顧慮事件的后果,更無需對網絡暴力進行解釋,而網絡也缺乏對相應社群的管理和追究辦法。因此,如何管理好和媒體擁有平等發聲權的“粉絲”社群,是維護新時期網絡和諧環境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
(三)干擾娛樂產業的運行規律,挑戰偶像底線。盡管現代“粉絲”社群既熟諳打榜投票之理,也懂得如何經營偶像的形象,各家媒體及娛樂產業對于“粉絲”的評價也是有口皆碑,有些媒體甚至會直接借用“粉絲”們產出的影音資料[4];偶像及團隊、公司更是無時無刻不把“粉絲”掛在嘴邊以示感恩。但是參與并不代表真正融入,不管“粉絲”如何參與偶像的構建,在娛樂產業中,“粉絲”永遠處于文化消費者的地位,所謂的主體性和主動權不過都是娛樂產業和市場賦予其更多選擇權而已。這么做無非是為了更好地刺激“粉絲”的購買力,同時規避市場風險,然后又營造出“粉絲”“主人翁”的盛世景象。但是,“粉絲”對于自己的身份并沒有真正認識,他們當真會以為自己投票、做數據能夠捧紅一個偶像,忽略了偶像成名身后的巨額投資,更忽略了娛樂產業的運行規律和運行模式,只一味根據自己的好惡來決定偶像的發展,并不時和其他“粉絲”社群及媒體,甚至直接和偶像團隊及本人產生沖突。這樣的行為已經干擾了娛樂產業的運行規律,更會使偶像本人處于尷尬被動的局面。而受夠了“粉絲”“過度參與”的偶像們,紛紛開啟了和“粉絲”們“互懟”的模式,例如2019年初,新浪微博的熱搜就出現了“章子怡拉黑粉絲”和“謝娜懟粉絲”這樣的新聞,內容均涉及“粉絲”干預偶像的工作或者職業發展,而偶像對于“粉絲”的過度參與表示不滿,甚至不惜拉黑“粉絲”后援會的核心“粉絲”。由此,我們可以看出,“粉絲”過度參與追星已經超出了滿足自己精神愉悅的需求,同時也有悖于娛樂產業賦予其自主性的初衷。
四、過度參與式追星對“粉絲”經濟帶來的影響
“粉絲”經濟是建立在“粉絲”文化基礎,立足于娛樂產業大環境的新型經濟模式之一。隨著新媒體時代下“粉絲”社群追星模式的改變,參與式追星賦予了“粉絲”社群更多的主動性和主體性,在這種“主人翁”的意識下,“粉絲”逐漸意識到對于偶像的付出不僅需要體現在精神支持上,更需要體現在物質和金錢的支持上。因此,支持偶像票房、積極購買周邊及大量偶像代言的產品都是衡量“粉絲”合格與否的重要指標。而明星官方的“粉絲”福利發放的一個重要標準也是其購買力到底如何。在這樣的大環境下,“粉絲”經濟明顯呈現出蒸蒸日上的景象,據工信部《22018中國泛娛樂產業白皮書》顯示,2016年 我 國 泛 娛 樂 產 業 產 值 達 到 4155 億 元,2017年,我國泛娛樂核心產業產值約為5484億元,同比增長30%。至2020年,中國的媒體娛樂行業的平均年復合增長率將達到8%,位列全球媒體娛樂產業增速前十的國家或地區[5]。與此同時,“粉絲”經濟發展的前景卻不得不引起極大的重視,試想,當現行“粉絲”運行模式不適應娛樂產業的發展模式,當“粉絲”行為已經嚴重干擾了偶像的工作和名譽,當偶像開始不包容、不接受“粉絲”的呵護,那么娛樂產業自身的發展規律勢必會摒棄現在的“粉絲”文化和追星模式,重新引導“粉絲”的價值觀和行為,而這樣的過渡勢必會造成“粉絲”的不滿,也會造成新舊“粉絲”的交替,在這個過程中,同樣會造成對現有“粉絲”經濟的沖擊,甚至會使“粉絲”經濟成為泡沫經濟。因此,尋求相對穩定的“粉絲”追星模式,構建成熟的“粉絲”文化,才是“粉絲”經濟健康發展的前提。
五、結語
經過對現代“粉絲”社群追星特點的分析,本研究發現,盡管現有的參與式追星模式能夠體現出“粉絲”更多的主動性和主體性,使娛樂圈的發展呈現現出更多的群眾意志,同時引領了“粉絲”經濟的多元發展,為我國的網絡經濟發展貢獻了不少力量。但是,“粉絲”的過度參與也造成了一系列弊端,由于“粉絲”自身的情感強烈不受約束,導致這種情感容易被外力操控引發網絡暴力事件,甚至會挑戰偶像的底線,長期以來,這樣的追星模式勢必會干擾到娛樂產業自身的運行規律,同時也會影響到“粉絲”經濟長期健康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閆翠萍,蔡琪.網絡虛擬社區中的圈子文化[J].湖南社會科學,2013,(4): 86-90.
[2]肖芃,高森宇.社會化網絡中“粉絲經濟”的營銷分析[J].現代傳播,2015,(10):118-121.
[3]Henry Jenkins.Textual Poaches: Television Fans and Participatory Culture[M].New York: Rouledge,1992,28.
[4]王藝璇.網絡時代粉絲社群的形成機制研究——以鹿晗粉絲群體“鹿飯”為例[J].學術界,2017,(3):91-103.
[5]范璐月.粉絲經濟在娛樂產業中的影響分析[J].現代商貿工業,2019,(1): 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