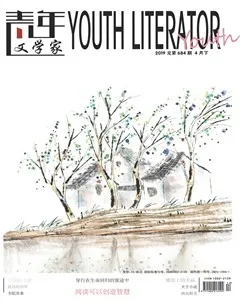穿行在生命回歸的旅途中
作者簡介:遲皓中,男,籍貫:山東省諸城市,漢族,2000年生,山東省諸城超然中學(xué)高中在讀。
闊別半年,又站在了家鄉(xiāng)的講臺上,面對著那些哪怕是對曾經(jīng)淺薄的我也滿懷期望,殷切渴求中醫(yī)文化的人,我不再因為他們是“家鄉(xiāng)的人”這個特殊的意義而分外欣喜,卻多了幾分沉重的責任和如履薄冰的敬畏。半年的洗禮,從初上講臺的青澀,到數(shù)次面對數(shù)以百計孩子的父母,當站在講臺上發(fā)愿用一生去傳播中醫(yī)文化那一刻起,就不再有家鄉(xiāng)的人或是異鄉(xiāng)的人,只有迫切需要中醫(yī)文化的人,正因為有了這些人,才有了肩上沉重的使命,和對生命神圣的敬畏。
在走上講臺之前,我沒有以往的平靜,反而有些戰(zhàn)戰(zhàn)兢兢,學(xué)習振蕩中醫(yī)以來的兩個假期,我都在家鄉(xiāng)進行過分享,從一開始的十余人到后來的三四十人,其中不乏每次都參加的人,而我就像學(xué)習了一個學(xué)期的孩子,要給家長和老師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一樣,我也得給自己一份滿意的答卷,問問自己一個學(xué)期有多少的成長,有多少更深的領(lǐng)悟,有多少可以匯報給家人的新知,而戰(zhàn)戰(zhàn)兢兢就源于這些問題的答案,不敢辜負家人的期盼。如果說那些引領(lǐng)我在中醫(yī)的道路上前行的人是開拓文化的先行者,那么我也得像前人一樣,與那些剛起步的人一起,走入一個全新的境界,我責無旁貸。
初定的脈診學(xué)習由于時間和大部分人是初學(xué)者的緣故,變成了隨機分享,我從接觸中醫(yī)的緣起談起,以一個親歷者的角度去談對中醫(yī)的感受;到我逐漸認識什么是疾病,是身體的序穩(wěn)狀態(tài)失衡,而非某一單一異常,許多的經(jīng)歷顛覆了諸多是我的,也是絕大多數(shù)人的錯誤的疾病觀;再談到所有的病都會涉及到的飲食,排異,情志,告訴大家,健康就在“法于陰陽,和于術(shù)數(shù),食飲有節(jié),起居有常,不妄作勞”之中;到最后談及振蕩中醫(yī),全新的宇宙觀、生命觀、疾病觀、思維方式,雖然聽起來晦澀難懂,卻足以領(lǐng)略到振蕩中醫(yī)的“絕美”。
一上午的時光匆匆,在聆聽者的贊嘆聲中回顧整個講課過程,自己其實并不滿意,與臨近一次分享相比沒有明顯的提升,也就是說這期間的我學(xué)習并不精進,更深知,贊嘆是屬于那些智慧的先人大醫(yī)們的,我們只是巨人肩膀之上的受益者。不經(jīng)意間又想起了韋老的大愿“還醫(yī)于民”,郭老的大愿“天下無醫(yī),生民無病”,不是人人都要做醫(yī)者,但是人人都應(yīng)該懂醫(yī),應(yīng)該了解生命,面對著這些渴求中醫(yī)文化,卻不知道什么是生命的人們,驚覺自己需要做的還有太多,當我們畏懼講臺的時候,并不知道可能因為我們的一句話就改變了別人的生活方式,從此獲得了健康,當我們畏懼摸脈的時候,并不知道我們自慚形愧的水平,可能讓別人從此走上了認識生命,掌握生命的旅程。才發(fā)現(xiàn)以前認為距離我們很遠的文化傳播其實就是身口相傳的一點一滴,是我們都能做的,也是大醫(yī)們的慈悲引領(lǐng),我們作為天下父母的孩子,以后作為天下孩子的父母,必須要做的,因為我們都應(yīng)該走在回歸生命,掌握生命的道路上。
一架橋梁在生命大道與人之間架起,前人將生命文化傳播給我們,我們也應(yīng)追隨前人,將中醫(yī)文化還給全人類。因為中醫(yī),我從迷茫走上了回歸生命的道路,我想,人生的覺悟從發(fā)愿此生為了更多生命的幸福而活的那一刻就開始了,開弓沒有回頭箭,我走在了人生回歸的旅途中,為了更多人能在生命回歸的道路上不息穿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