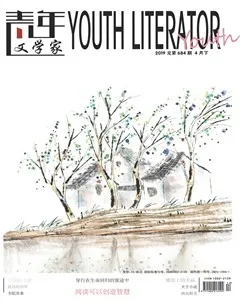論袁宗道的詩學觀
摘? 要:袁宗道是公安派的一位主要人物,對公安派的形成與發展,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其詩學思想中,開拓創新與保守持重互相錯雜,本文著重考察其復雜多面的詩學觀念。通過對袁宗道文章的分析,側重穩健開拓的詩學觀念,從文學通變觀、真情與節制觀、雅俗觀三個方面加以論述,對袁宗道文章的深入了解,有助于深化對袁宗道詩學觀的體認。
關鍵詞:袁宗道;詩學觀;穩健;開拓
作者簡介:潘靜雅(1995-),女,漢,江蘇濱海人,揚州大學文藝學碩士。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02
引言:
袁宗道身為家族長子、士人和士大夫,他肩有傳統儒家士子的家國責任,也有心學、佛學等新思潮推動下士人向往自由創造的激情,這種矛盾同時體現在了他的詩學觀念中。袁宗道不可能完全拋棄傳統,他的詩學觀念體現出從傳統士人矩矱中尋求創新突破的特點,在其詩學觀中呈現出“穩健”和“開拓”并存的風貌。
(一)繼承與發展的輕重權衡
袁中道在《石浦先生傳》中描述袁宗道說:“二十歲舉于鄉。不第歸,益喜讀先秦、兩漢之書。”[1]袁宗道對于古書是盡皆熟讀的,但是袁宗道繼承傳統文學除了是愛好,更存在了一種必然性,袁宗道作為家族長子,擔負著光耀門楣的責任,在古代“士農工商”理念的影響下,致仕是唯一出路,想要致仕必然要熟讀儒家經典,可以說袁宗道前十幾年接觸的都是傳統文學,儒家思想對他的影響也不可能抹滅。除此之外,袁宗道還推崇白蘇,他一度想要辭官歸隱,便是受到他們的影響,白蘇詩中表現出來的灑脫豪邁的精神,正是袁宗道求而不得的,所以他提倡學習古人的精神,汲取前人的文學觀念。盡管如此,袁宗道卻不是盲目擬古,而是取其長而去其短,因此,袁宗道強烈反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文學主張,駁斥了復古派的種種謬論,但是相對于宏道以及其他一些反對模擬文風的文人,袁宗道顯得相對平和、公正。在人們將矛頭指向七子的領軍人物王世貞時,袁宗道卻站出來為他說話:“弇州才卻大,第不奈頭領牽制,不容不入他行市,然自家本色,時時露出,畢竟不是歷下一流人。”[2]也對前后七子的文章做出了公允的評價:“且空同諸文,尚多己意,級事述情,往往逼真。”[3]袁宗道反對復古倒退,卻不是盲目反古,對于有才學的人袁宗道還是會給予肯定,袁宗道真正反對的其實是那些盲目跟隨前后七子的學子,沒有自己的思想,沒有自己的情感,這種風氣需得到整改。
在繼承古人精神的前提下,袁宗道也試圖打破傳統的束縛,提出了許多發展性的觀念。首先,反對在語言上盲目擬古。因前后七子提倡“無一語作漢以后,亦無一字不出漢以前”[4]他們的作品中多是佶屈聱牙的古代字語,讀來晦澀難懂,所以袁宗道便在《論文》中諷刺主張擬古的文人:“彼摘古字句入己著作者,是無異綴皮葉于衣袂之中,投毛血于肴核之內也。”[5]批評前后七子的同時,提出“夫時有古今,語言亦有古今”[6]的觀點,認為語言與時俱進是必然趨勢,不可倒行逆施。對于語言的運用,宗道是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又突破傳統,提出了具有發展性的建議。其次,提倡內容決定形式,抨擊王世貞、李攀龍為了遷就形式,不惜扭曲內容的荒唐做法:“滄溟強賴古人無理,而鳳洲則不許今人有理,何說乎?此一時遁辭,聊以解一二識者摹擬之嘲,而不知流毒后學,使人狂醉,至于今不可理喻也。”[7]如果一味抄襲模擬,只知借用古人形式,套在如今的內容上,便只是不倫不類,既不能繼承古文中的經典,對如今文學的發展也毫無意義。最后,提倡作家要追求獨立自主的人格,在作品中直抒胸臆,要有自己的獨到的見解。袁宗道在《論文》開篇中就提到:“口舌代心者也,文章又代口舌者也。”[8]提出文章乃是表達心意之作,卻多有辭不達意之困,需如孔子所說一般,言辭不需要太多華麗的修飾,只要能表達本意即可。由此可見,袁宗道習古卻不泥古,遏制了文壇中的不正之風,幫助當時文人在繼承還是發展的兩難中開辟一條全新的道路,有助于當時文學的健康發展。
(二)真情與節制的兩端取舍
袁宗道在《論文》中說道:“大喜者必絕倒,大哀者必號痛,大怒者必叫吼動地,發上指冠。”[9]這是說作家在進行創作實踐時,必然伴隨著強烈的情感活動,自然流露出作者的思想、情感。如若模仿抄襲,必然不是自己的真情實感,而是虛情假意,就如戲場中人,不過是角色的扮演者。袁宏道曾在《敘小修詩》中稱贊袁中道:“大都獨抒性靈,不拘格套,非從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10]袁中道也提倡創作時應該流露真情實感,主張作家應獨寫“自家本色”,宏道也明確提出“不拘格套,獨抒性靈”,可見袁家三兄弟在創作觀念上有相似性,相互影響,相互促進。袁宗道受兩位弟弟影響,轉向性靈文學,他并不是一個傳統的士大夫,這與他狂放的性格相關,思維并不僵化,與時具進卻不落俗套。同樣受心學的影響,袁宗道一直標舉學識,崇尚學理,在《論文》中說:“學者誠能從學生理,從理生文,雖驅之使模擬不可得矣。”[11]他認為創作之所以能夠抒發真實感情,就是因為作者具有獨到的主觀認識,只有具備了識別能力,學會進行思考,對創作對象和素材做出正確的判斷和選擇,才能創作出有自己風格的文章,具有自身的個性特點。袁宗道的創作流露真情,卻不似宏道那般狂放恣意,任意妄為,會有意識地有所節制,這種創作中既有真情又有節制的特點可從以下兩點來分析。
首先,從袁宗道的思想性格來看,他從小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表現出儒雅、平和的性格特點,在當時的熱門話題“師心”還是“師古”中保持中立,可見宗道的文學思想有一定的保守成分。而且宗道推崇理學,喜歡用朱熹“格物致知”的方法來論情:“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吃緊功夫,千圣入門之的訣也。”[12]但是宗道推崇的“理”乃是真理,無論是評價他人還是創作作品,都要從事實出發。袁宗道不僅主張崇識尚理,還有“豁之以致知,養之以無欲”[13]的觀點,這表明了宗道重德輕文的傾向,曾在《刻文中子序》中通過比較《莊子》與《文中子》的不同來提倡文學經世致用的作用。所以,袁宗道的經歷導致其創作時不可能一味自由抒發自己的情感,而是有意識往文學的實用方面發展。其次,從袁宗道的人生經歷來看,袁宗道的一生受到了太多限制,他想要辭官受到家人阻止,想要享樂人生受到身體阻止,想要一心鉆研佛學受到責任阻止,但是這些限制說到底都是他自己加在身上的,他不會不顧家人的反對,不會不顧自己身體的健康,不會不顧身上的責任,他的欲望是可以被控制的,可見其意志力之堅定。
最后,袁宗道能夠分清創作與現實的區別。袁宗道在生活中追求功名利祿,可是在他作品中卻是向往田園生活的。他在創作中保持情感克制,雖然看上去不如放任自然的情感來得酣暢淋漓,但是某種程度上契合了藝術創作中審美情感的特性,他的詩文美學思想自有其合理之處,不可簡單判定其保守落后。蘇珊·朗格指出:“一個藝術家表現的是情感,但并不是象一個大發牢騷的政治家或是象一個正在大哭或大笑的兒童所表現出來的情感。”[14]在朗格看來,審美情感與人的自然情感是有區別的,藝術家的審美情感雖來源于自然情感,以自然情感為基礎,卻不是自己真實的情感,這超越了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意志和欲望,袁宗道的創作就是如此,掩蓋了自己真實的欲望,這也可以解釋為什么袁宗道欣賞真情洋溢,但是作品中的情感相對平和克制,確實別有一番特色。
這種創作時的真情與節制與公安派的整體方向不相一致,也與當時主流的文學革新運動相背離,尤其在公安末流那里,將直抒胸臆簡單化,墮落為情感的粗鄙化。袁宗道能夠力排眾議,堅持己見,自有其難能可貴之處。
(三)雅與俗的毀譽之間
明中葉后文學呈現新的風貌,描寫市民的現實生活,表現他們的審美趣味和情感的通俗文學空前繁榮。在戲曲領域取得較大成就的湯顯祖主張“唯情說”,而三袁與湯顯祖交好,他們在與湯顯祖的書信交往中表示了對其文藝觀的認同。三袁也深受李贄的影響,李贄向傳統儒學發出挑戰,對于當時被視為俗文學的戲曲、小說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袁氏三兄弟中以袁宏道最為鋒芒畢露,無所顧忌地對于傳統文學進行了批判,對通俗文學推崇備至,而宗道同樣受自己“穩實”性格的影響,并不能完全拋棄儒學正統,但他也試圖突破傳統文學空間的限制。例如《讀論語》首句:“凡作于意用功夫時,真妄交爭,理欲相乘,有照管有克治,有打點有考究等,俱費力生硬,不相諳習,厭苦不暇,何‘悅之有?時習之,十二時中,語默動靜,相安相忘,不知不覺,妥妥貼貼,即此是悅。”[15]宗道對“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中的“學”和“悅”做出了不一樣的解釋,打破了傳統的思維局限,用新的學術思維來闡釋傳統文學,為公安派其他學者反傳統的理論埋下伏筆。而且袁宗道也將自己的詩文向日常生活空間拓展,游記類散文多為我們細致描繪了當時壯麗的風景,而后回到現實,常發表自己的人生感悟,如《大別山》中先是驚嘆“大別山隆然若巨鰲浮水上”[16],隨后感嘆“豈惟不識曹,亦不識衡矣”[17],諷刺世人過于推崇君子而不顧其是否擁有真才實學。又如《江上游記》中從描繪奔騰的長江中感慨百姓屢遭水患,為此憂心不已。宗道亦常常為日常生活中的人作序,如《唐醫序》、《李母壽序》、《顧使君考績序》等,贈序、祭文、游記、尺牘在袁宗道的作品中占有一定分量,他將朋友逸事、山水風光、逝者恩德皆紀錄在文中,雖是尋常瑣事,卻不拘一格,獨抒性靈,這些文章雖不能流芳百世,卻把明代的生活展現在了我們眼前,通俗易通,對后世產生的影響也較為深遠。
結語:
袁宗道穩健開拓的詩學觀念,以繼承為基礎,以發展為根本,繼承中有發展,穩健中有開拓,既不會顯得突兀,又有其開拓意義。放在公安派草創階段的語境下看,這一穩健開拓之舉,為日后袁宏道等人的淋漓發揮提供了空間,他的詩學觀念是公安派詩學思想早期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公安派文學革新運動的先驅,在公安派的創立和發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動作用。
注釋:
[1]袁中道:《石浦先生傳》,《珂雪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658頁。
[2]袁宗道:《答陶石簣》,《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3頁。
[3]袁宗道:《論文下》,《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5頁。
[4]王世貞:《藝苑卮言校注》,羅仲鼎校注,齊魯書社,1992年,第343頁。
[5]同注釋2,第285頁。
[6]袁宗道:《論文上》,《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83頁。
[7]同注釋6,第285頁。
[8]同注釋6,第283頁。
[9]同注釋6,第285頁。
[10]袁宏道:《敘小修詩》,《袁宏道集箋校》,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87頁。
[11]同注釋6,第285頁。
[12]袁宗道:《讀大學》,《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37頁。
[13]袁宗道:《士先器識而后文藝》,《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91頁。
[14]蘇珊·朗格:《藝術問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15]袁宗道:《讀論語》,《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41頁。
[16]袁宗道:《大別山》,《白蘇齋類集》,錢伯城點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95頁。
[17]同注釋14,第19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