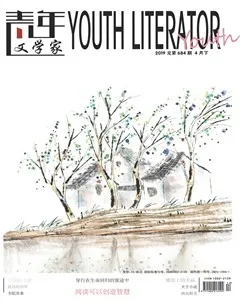從《史記·李斯列傳》出發(fā)淺析司馬遷的人物塑造手法
摘? 要:司馬遷是漢代著名的史學家,由他撰寫的《史記》則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曾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1]。司馬遷《史記》中尤其為人稱道的是他關(guān)于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手法。從《李斯列傳》中對人物的塑造手法出發(fā),可以淺析司馬遷《史記》人物塑造手法。
關(guān)鍵詞:司馬遷;《史記》;《李斯列傳》;藝術(shù)手法
作者簡介:張藝璇(1999.4-),女,河北省徐水縣人,遼寧大學漢語言文學專業(yè)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2
引言:
《史記》為人稱道的藝術(shù)成就之一就是司馬遷在傳記中對人物形象的塑造。《史記·李斯列傳》也是《史記》眾多人物傳記中著名的篇目之一。本篇以《李斯列傳》為主對李斯這一形象的塑造方法進行研究,來分析司馬遷對于人物形象塑造的藝術(shù)手法。
1.將人物置于具體時空背景之中塑造形象
“司馬遷注重擇取反映重大的社會矛盾與斗爭的事件,來構(gòu)成《史記》的基本情節(jié),人物的性格特征往往在這種條件下才顯得深厚、清晰而有光彩。”[2]司馬遷為了突出歷史人物的性格特征,總是在紛繁的歷史事件中,選取一些富有代表性和處在矛盾沖突中的事件,使人物置身于矛盾中。“在《史記》傳記中,隨處可見戰(zhàn)爭、格殺、政變等重大社會變革的記載,傳記人物多數(shù)在驚心動魄的事件中來展示自己的風貌。”[3]
在《李斯列傳》中,在李斯為了避免被驅(qū)逐,上《諫逐客書》于秦王時;在李斯妥協(xié)屈從于趙高的威逼利誘,同意矯詔協(xié)助篡位時;在李斯被捕入獄,在獄中悲傷感嘆時;在李斯自以為秦二世能念及自己昔日功勞免除一死而在監(jiān)獄中上書時;以及最后被判處五刑。司馬遷在李斯處于種種的矛盾沖突中時,對人物形象進行了生動的刻畫,從而使人物形象在廣闊的社會背景和復(fù)雜的人物矛盾中脫穎而出。
“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于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4]這一矛盾,使李斯展示出了過人的口才與能力。秦始皇于沙丘崩殂,趙高企圖與李斯密謀,扶胡亥登基,又使李斯處于了另一個矛盾當中。“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李斯在面對二世責問盜賊猖獗之過時,為了保住自己的榮華富貴,便曲意迎合,表現(xiàn)出了李斯在后期對名利地位貪得無厭的追求。
2.以富有特點的語言揭示人物性格,塑造形象。
在《史記》當中塑造人物形象的一個重要手法之一就是通過富有表現(xiàn)力的人物語言來表現(xiàn)人物的形象,通過富有特色的對話、獨白等各種形式顯示人物的性格特征,揭示人物的內(nèi)心世界。《李斯列傳》中有一段關(guān)于李斯看到廁所里老鼠偷吃東西時發(fā)現(xiàn)人來后驚惶逃跑的表現(xiàn),與糧倉中老鼠的悠閑姿態(tài)截然不同,發(fā)出了感嘆:“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人有出息與否,就如同老鼠一樣,是由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決定的。李斯為何會作此感慨?不難得知,當時的李斯只是一個郡中的小吏,這一段獨白,暗示了他渴求高位與權(quán)力,力圖改變自己所處的境遇的心理,為他成為秦王政統(tǒng)一六國的助力,最終位及丞相做鋪墊,也為秦始皇駕崩后,李斯為富貴形勢所屈與趙高合謀偽造遺詔,留下了較為合理的解釋。
李斯被捕入獄后,有一段在獄中悲嘆的獨白。“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為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游於朝也。”李斯的這段獨白分析了自己所處的形勢,正如同龍逢、比干和伍子胥,又對秦面臨的政治局勢進行了全面的分析。展示了李斯睿智與虛榮,治國之才與助紂為虐的多重矛盾的復(fù)雜形象。《李斯列傳》中的獨白,不僅是富有人物性格特性的體現(xiàn),而且更是人物在特定環(huán)境,特定情境下內(nèi)心活動的外現(xiàn)。
“司馬遷精心為人物擬言立言,描摹的語言符合人物性格特征,道出了人物心靈的奧秘,使傳記人物語言有了個性化的特色。”《李斯列傳》中,李斯上《諫逐客書》于秦王,以睿智的語言陳述秦王下逐客令的種種弊端,分析利害,闡明局勢,最后以“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夠益仇,內(nèi)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最終使秦王放棄逐客,將其官復(fù)原職。“能明其畫,因時推秦,遂得意于海內(nèi),斯為謀首。”條理清晰、有理有據(jù)的語言,使一個治國良才的形象躍然紙上。
當趙高想借助李斯的力量幫助秦二世胡亥篡位時,李斯從一開始的“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也。”“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fù)言,將令斯得罪。”到最后的“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讬命哉。”最終依從趙高偽造詔書。李斯于語言氣勢上的步步退讓,表現(xiàn)出其為形勢所屈服的軟弱心理。李斯被捕入獄以后,渴望求得寬恕,便在獄中上書。“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眾之心,萬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他列舉了自己的七條“罪證”,看似反省罪責,實則條條列舉自己從追隨秦王至今的功績,表現(xiàn)出他對重新獲得皇帝寵信以及功名利祿的向往,同時與開篇對李斯向往功名利祿的描寫相呼應(yīng),人物形象更加完整真實。
3.通過論贊使人物塑造更加具體生動。
《史記》傳記篇末都是“太史公曰”式的議論短文,與傳記有著內(nèi)在的聯(lián)系,是傳記統(tǒng)一結(jié)構(gòu)有機的一部分。是對傳記人物的一首首贊歌、哀歌、諷歌。這是《史記》中很重要的一部分,有的是為了論斷人物的德行品質(zhì),有的是為了補充人物性格特征,有的則是為了揭示人物命運的必然性,進而體現(xiàn)對人物生平的評價以及自己的思想。如《屈原賈生列傳》中,“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司馬遷深受屈原愛國情志的感染,來到他沉江的地點也忍不住潸然淚下,直接抒發(fā)了惋惜與悲傷之情。又如《項羽本紀》中通過“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肯定了項羽的成就,但又表示“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寐而不自責,過矣。”司馬遷又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項羽的錯誤以及其必然失敗的結(jié)果,為后世提供借鑒。
《李斯列傳》中的“太史公曰”,對李斯的一生進行了總結(jié),使人物形象具體化。“入事秦,因以瑕釁,以輔始皇,卒成帝業(yè),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肯定了他的功不可沒。“不務(wù)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阿順茍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強烈批判了李斯聽信趙高的蠱惑,廢嫡子扶蘇而立庶子胡亥的這一不忠不義之舉。“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召列矣。”雖然司馬遷對李斯總體上是不認同的感情色彩,但從這一段文字中仍能看出他對待歷史人物評價的全面性。司馬遷在塑造人物形象時,既融入自己的主觀感情色彩,又能把深刻復(fù)雜的道理以深入淺出之筆法進行闡述,使人物形象更加具體、立體、多層次、更加真實可信。正是“太史公曰”這一點睛之筆,使得作者個人的情感在所評價的人物身上得到體現(xiàn),使得讀者在審美理解的過程中體會到其作品的形象性,情感性,使其作品價值得到充分的體現(xiàn)。
司馬遷將傳主置身于復(fù)雜的時空背景之中,既使得人物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同時也對故事的發(fā)生和人物命運發(fā)展的走向起到了推動作用。“司馬遷筆下的人物,都是一定社會環(huán)境的承受者,或能順應(yīng)它,或能改造它,成為環(huán)境的主宰者。否則,逆來順受或處處被動,就成為社會環(huán)境的奴役者,甚至成為社會環(huán)境的犧牲品。”
司馬遷對語言的靈活運用是《史記》的亮點之一,個性化且富有特點,使人物的語言連貫整個事件和情節(jié)。同時,司馬遷在語言的雕琢上具有大膽的創(chuàng)新精神,將豐富的想象力與精妙的筆法融為一體。“《史記》人物的語言既受作者整個創(chuàng)作思想感情的統(tǒng)攝,又根據(jù)人物不同的性格而呈現(xiàn)出個性化。”司馬遷通過對語言的加工,使人物形象鮮明豐滿。篇章結(jié)尾的論贊也為全文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司馬遷本人的評價,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加立體、多層次、真實可信。
參考文獻:
[1]魯迅 《漢文學史綱要》 《魯迅全集》第8卷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年版.
[2]楊樹增 《史記藝術(shù)研究》 學苑出版社 2004年12月第一版.
[4]司馬遷《史記·卷八十七·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中華書局 2014年8月第一版.
[5]司馬遷 《史記·卷七·項羽本紀第七》中華書局 2014年8月第一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