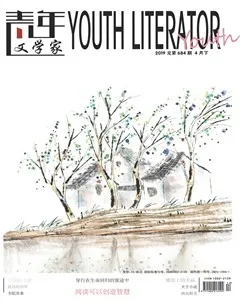理性的曙光: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之謎
綦文多
摘? 要:《哈姆萊特》是莎士比亞四大悲劇作品之一,主人公哈姆萊特猶疑與延宕的性格引發了眾多討論,本文將從哈姆萊特“延宕”性格的表現、成因及意義三個層面出發,從一個新的角度對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之謎進行分析。
關鍵詞:《哈姆萊特》;人文主義;延宕;性格悲劇;理性主義
[中圖分類號]:J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12--02
哈姆萊特作為西方古代文學史上的經典人物形象,其“延宕”性格的產生有宏觀的社會背景和微觀的人性促因,是困境中的人文主義在典型個體性格上的具體表現。其“延宕”的性格具有悲劇色彩,但本文認為,這同時體現了人文主義的自省和理性曙光的初現,是人文主義向理性主義過渡時代下“陣痛”的表現。在哈姆萊特的“延宕”中,我們看到了一個擁有著崇高人文精神跟人性之美的失意王子,用近乎瘋狂的姿態同現實的黑暗與人性的丑惡所作的矛盾斗爭。而這種姿態,恰是人的智識與理性在萌芽階段的顯現。
1、猶豫中的王子——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表現
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主要表現在行動和思考兩個維度。首先,哈姆萊特在行動中呈現出了遲緩猶豫的狀態,主要表現為決定上的謹慎和復仇實施的猶疑。當哈姆萊特聽到自己父王的鬼魂向他訴說叔父奪權的邪惡之舉后,他讓告訴他鬼魂一事的霍拉旭等人反復宣誓“不會將此事說出去”;他沒有輕信鬼魂的話直接復仇,而是選擇裝瘋和用戲劇試探的方式來確定叔父的罪惡。即使在確定了叔父的罪行之后,哈姆萊特也沒有立即殺死自己的叔父。他放棄了叔父正在禱告的時間殺死他,理由是“要是我在這時候結果了他的性命,那么天國的路是為他開放著,這樣還算是復仇嗎?”可見,謹慎和猶豫拖慢了哈姆萊特的復仇行動。
除了行動上的遲緩猶豫,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還體現在其復仇進程中思考的繁密。這些思考包含了復仇計劃,更多的則是復仇之外的深層思考。哈姆萊特在“裝瘋”和“試探”的復仇過程前期,有許多人生哲學層面的思考。這些思考體現出一種濃重的虛無感和迷茫感,由此而生發出的困頓和無力深深籠罩著哈姆萊特,侵蝕著他復仇的決心和腳步。
哈姆萊特所處的世道黑暗,這對一個充滿人文主義情懷的貴族王子,是難以忍受的。凄慘的現實與崇高的理想間的矛盾將哈姆萊特不斷擠壓,使他在痛苦中生出繁密的思考。哈姆萊特的思考內容深刻、覆蓋面廣且極富理性,既有對現實的批判,也有倫理道德與正義觀念的評判,更為重要的則是對人生意義的深刻思考。這些思考是哈姆萊特內心矛盾的體現,他試圖通過這些思考來理清自己的困頓,卻越陷越深,以至于削弱了自己“復仇”的決心。其“延宕”的性格也孕育于這些復雜的矛盾與其思考的載體之中。
2、人文主義者的矛盾——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成因
本文將從復仇的推力、阻力及哈姆萊特人物的特性三個角度切入分析哈姆萊特“延宕”性格的成因。
從“復仇的推力”看,哈姆萊特叔父的行為無疑是罪惡之至。謀殺人,是人的罪惡;篡位,是逆臣的罪惡;娶先王之妻,是亂倫的罪惡。于私,新王是哈姆萊特的殺父仇人;于公,新王也是罪大惡極之人。社會的正義、個人的私憤是哈姆萊特選擇復仇、殺死其叔父的助推力。
從“復仇的阻力”看,哈姆萊特與新王相比,力量弱小,這使得他的復仇面臨著客觀實力上的阻力。同時,即使殺死的是一個十惡不赦的罪人,用“殺人”的復仇方式也難說高明,而哈姆萊特又是一個人文主義者,對“殺人”的排斥較常人更甚。
“推力”與“阻力”交織,必然激起哈姆萊特內心的波動,其思想和行動上的遲緩猶疑也就可以得到解釋。但其“延宕”性格最根本的成因則要從哈姆萊特人物本身的特性去尋找。
首先,哈姆萊特是人文主義者,學識豐富、修養極高。他堅守人性原則和道德倫理,對愛情、美德、貞潔有純潔的信仰。他對自己叔父和母親的做法必然有極大的仇恨。但作為人文主義者,他又天生善良慈悲,有不忍之心。他對母親說:“免得你那種可憐的神氣反會妨礙我的冷酷的決心。”他復仇的對象又是有血緣關系的叔父,這使得他陷入了自己所堅守的人性原則和道德倫理的反背,而無論復仇與否,都無法逃脫出這種矛盾的怪圈。
哈姆萊特又是極富智慧的。當他看到了人性的丑惡,看到了人文主義的局限性與現實的黑暗,他開始思考人生。這種思考能夠幫助他脫離道義的牽絆,但同時又陷入了更深層的迷茫。“復仇”本身的意義在生命虛無的侵蝕下消減,宗法和道義的理由就不再有足夠的力量推動“復仇”的行動。這些思考是哈姆萊特動用理性的結果,也是其“延宕”性格最深層的原因。
3、悲劇中的理性曙光——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意義
《哈姆萊特》創作于伊麗莎白末期——社會黑暗動蕩、人文主義理想破滅的時期。哈姆萊特的悲劇源于其所處的時代,源于人文主義理想深層次的矛盾——過于放縱人性導致的惡果。但在這出理想破滅的悲劇中,新的方向卻依稀可見。哈姆萊特“延宕”的性格不僅展示出矛盾與迷茫,還有人在與矛盾抗爭時對理性的運用,這也是塑造其“延宕”性格特征的最大意義,是18世紀理性思潮的萌芽與曙光在典型個人身上的閃光顯現。
理性的運用是哈姆萊特在無數的角色與身份、理想與現實的矛盾沖突中所安身的唯一選擇。哈姆萊特既是臣子,又是孝兒;既熱愛人性之美,又痛恨人性的陰暗面。在重重“枷鎖”的重壓下,理性為哈姆萊特撐起了一片空間,并帶領他上升到生命意義的深層探討中。在理性的幫助下,人終于超脫世俗的捆綁,找到了自己真正的位置。“這是一場早期現代主體拒斥主導政治意識形態召喚和包容的斗爭。它顯示了覺醒中的主體擁抱理性、邁向啟蒙的迫切愿望,顯示了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對宇宙和人類本體的追尋勝過現實政治和倫理價值承諾的思想取向。”[1]這種思想取向是理性主義的,它給面臨破滅危機的人文主義理想呈現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也給人性存在的可能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哈姆萊特》之所以能夠引發共鳴、成為經典,也正是因為它吶喊出了那個時代“哈姆萊特們”的理想破滅與憂郁迷茫。“哈姆萊特是一個矛盾的綜合體,一個時代的縮影;哈姆萊特的悲慘命運是一個時代的悲劇。”[2]哈姆萊特“延宕”中的理性不是特例,而是一個群體的覺醒。他身上“十分活躍的自我意識、自我觀照、自我求證,也就是人的自我意識、自我觀照、自我求證。”[3]我們在哈姆萊特一人身上看到的理性曙光,也是一個時代的理性曙光。
注釋:
[1]黃必康:《哈姆雷特:政治意識形態陰影中追蹤死亡理念的思想者》,《外國語》,2000年第4期。
[2]許明菊、徐珊:《探析哈姆萊特的人文主義的悲劇性》,《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30卷第5期。
[3]鐘翔、王昊:《關注人的命運探索人的奧秘—“哈姆萊特”沉思錄》,《莎士比亞研究》。
參考文獻:
[1]《哈姆萊特》(英)莎士比亞著;朱生豪譯,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5月。
[2]黃必康:《哈姆雷特:政治意識形態陰影中追蹤死亡理念的思想者》,《外國語》,2000年第4期。
[3]許明菊、徐珊:《探析哈姆萊特的人文主義的悲劇性》,《鄖陽師范高等專科學校學報》,2010年第30卷第5期。
[4] 鐘翔、王昊:《關注人的命運探索人的奧秘—“哈姆萊特”沉思錄》,《莎士比亞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