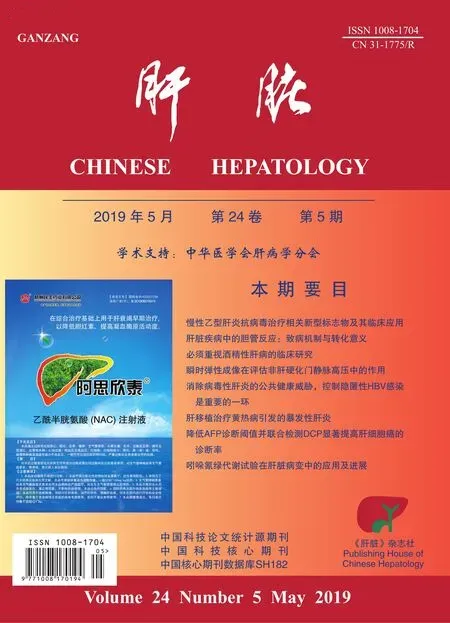IGF1和IGFBP3在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病程中的表達變化
鄒琳 李鐵巖 佘會元
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NAFLD)是全球最高發的慢性肝病,NAFLD包括單純性脂肪肝(NAFL)、脂肪性肝炎(NASH)、NASH相關性肝硬化及肝癌,而其中NASH患者發生心腦血管事件、惡性腫瘤、肝硬化等事件明顯升高,是2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預測的獨立危險因子[1]。
IGF1主要由肝臟合成并釋放,主要受循環中IGFBP3調控[2]。大量研究證實,低水平IGF1與2型糖尿病、胰島素抵抗、心血管疾病進展密切相關,血清低基線水平IGF1肝癌患者的疾病進展時間(time-to-progression,TTP)縮短并且生存時間(overall survival,OS)更短,血清低水平IGF1與肝癌風險升高呈正相關[3]。既往研究還發現NAFLD患者人群較健康人群中的IGF1水平下調,提示IGF1可能與NAFLD疾病有關[4,5]。但IGF1在NAFLD病程中的血清表達水平是否有差異以及與代謝指標的關聯性,目前仍不清楚。本研究采用回顧性研究方法,在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間我院脂肪肝門診,篩選NAFLD患者80例主要探討NAFL、NASH中IGF1、IGFBP3血清水平變化以及與代謝指標的相關性。
資料與方法
一、患者納入及排除標準
采用回顧性病例對照研究方法,在我院(上海市公利醫院)脂肪肝門診, 自2017年1月至2018年1月期間,根據《2017 AASLD 指南:NAFLD的診斷與管理》診斷標準篩選80例脂肪肝患者,其中NASH患者50例,并30例年齡、性別匹配的NAFL患者,納入標準:年齡18~65歲,符合《2017 AASLD 指南:NAFLD的診斷與管理》診斷標準,患者簽署知情同意書,研究通過倫理委員會。排除標準:除外酒精性、藥物性、病毒性、免疫性、遺傳代謝性等肝炎、肝硬化,除外心臟病、嚴重高血壓、腎病、腫瘤等其他嚴重基礎病,除外甲狀腺疾病、腎上腺疾病、垂體疾病、性腺疾病等其他內分泌腺疾病,除外孕產婦,除外大量飲酒(男性持續或最近每周飲酒>14標準單位,女性每周飲酒>7標準單位)。
二、方法
所有患者完善基本項目(年齡、性別、身高、體質量、腰圍);實驗室檢查(谷丙轉氨酶(ALT)、谷草轉氨酶(AST)、AST/ALT、γ-谷氨酰轉肽酶(γ-GGT)、總膽固醇(CHOL)、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HDL)、低密度脂蛋白(LDL)、游離脂肪酸(FFA)、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紅蛋白(HbA1c)、空腹胰島素(FIN)、HOMA-IR指數、尿酸(UA)、同型半胱氨酸(HCY)以及腹部B超檢查,其中BMI=體重/身高2,HOMA-IR指數= FPGFIN/22.5、HOMA-IS指數=1/HOMA-IR、HOMA-β指數=20FIN/(FPG-3.5),CRP,PLT,白介素6。
實驗材料及儀器:人IGF1 ELISA 試劑盒(CSB-E04580h,USA);人IGFBP3 ELISA 試劑盒(CSB-E04590h,USA);生化分析儀(雅培 C16000);腹部B超儀(飛利浦iu-Elite);酶標儀(SPECTRAMAX190,Molecular Devices公司)
三、統計分析
采用SPSS 17.0進行統計分析,計量資料采用Mean ± SD,符合正態分布采用兩獨立樣本t檢驗,非正態分布采用Mann-WhitneyU檢驗,計數資料采用卡方檢驗,變量對NAFLD疾病的影響采用單因素logistics回歸和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計算95%可信區間下的OR值,檢驗水準α=0.05,雙側檢驗,P<0.05說明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結 果
一、兩組患者的基線資料比較
納入NASH患者50例,平均年齡為(37.06+11.72),40例男性,并通過年齡、性別匹配NAFL患者30例,見(表1),其中NASH患者有更大BMI值和腰圍(分別為P=0.029,P=0.045),肝酶指標(ALT、AST、γ-GGT)均明顯升高,P<0.001,Insulin水平和HOMA-IR指數升高,(P=0.002,P=0.017),FFA水平升高(P=0.003),IGF1水平明顯下降,(P=0.034),IGFBP3水平上調,(P=0.003),IL-6較NAFL組升高,但無明顯統計學意義,而膽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C反應蛋白、血糖、同型半胱氨酸、尿酸未見明顯統計學意義。肝臟B超中,NASH組中發生中、重度脂肪肝人群明顯高于NAFL組,其中NASH組輕、中、重度脂肪肝人數比例為32∶12∶6,而NAFL組輕、中、重度脂肪肝人數比例為25∶4∶1,(Chi-Square Test,P<0.001)。
二、單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s回歸分析各變量與NAFLD病程的關系
見表2和表3。單因素分析提示AST、γ-GGT、IGF1、IGFBP3、FFA、Insulin、HOMA-IR、BMI是NAFLD病程的獨立危險因素,其中IGF1、IGFBP3、FFA、Insulin進入多因素分析模型,多因素分析提示IGFBP3 (OR1.091,95%可信區間(1.005,1.184),P=0.038);FFA(OR 161.704,95%可信區間(2.176,12016.894),P=0.021);Insulin(OR1.050,95%可信區間(1.010,1.092),P=0.015)與NAFLD病程嚴重程度呈正相關;IGF1(OR 0.991,95%可信區間(0.984,0.998),P=0.017),與NAFLD病程嚴重程度呈負相關。

表1 兩組患者的基線資料及實驗室檢查(±s)

表2 單因素分析

表3 多因素分析
討 論
NAFLD作為肝臟的代謝綜合征,已成為目前影響公衛健康的主要疾病之一,而當疾病進展到NASH時,則進展為肝硬化、肝癌的風險明顯升高[6]。IGF1是體內重要的代謝調節因子,可能與NAFLD的病程密切相關。在肝臟中,IGF1通過與肝臟細胞中的IGF1受體相結合,并受血漿中IGFBPs調控(主要為IGFBP3),形成動態平衡,因此可以通過循環IGFBP3和IGF1水平來了解IGF1和IGF1R結合情況[4],正常情況下,肝臟僅表達少量的IGF受體,但當病理狀態下(如乙型肝炎、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等情況下,IGF受體表達明顯增加[7]。部分研究發現肝內調節炎癥反應的庫普弗細胞和調節纖維化的肝星狀細胞(HSCs)均可表達IGF1R,這可能影響血清中IGF1水平下調,IGFBP3水平上調[8]。而我們的研究發現NASH組患者IGF1水平低于NAFL組,提示IGF1-IGF1R信號通路與NAFLD發病過程密切相關;而IGF1的經典上游信號通路為“GH-JAK-STAT5b-IGF1軸”,即“GH/IGF1軸”,既往研究中發現NAFLD是成人生長激素缺乏綜合征(GHD)的常見合并癥,GHD患者更容易發生NASH,當GH替代治療后,NASH可以逆轉[9]。而GH受體缺乏的小鼠血清中IGF1水平減少90%,提示GH/IGF1軸參與調節血清IGF1水平并可能參與NAFLD發病[10]。另外,胰島素抵抗、氧化應激ROS、線粒體功能失衡是NASH的重要病理機制[13]。而IGF1可以提高ATP合成,減少線粒體損傷和氧化應激,通過調節胰島素信號通路改善胰島素抵抗,影響NAFLD發病[14]。
綜上所述,血清IGF1水平、IGFBP3水平可能與NAFLD病程密切相關,IGF1與疾病進程負相關,而IGFBP3與疾病進程正相關,BMI、肝酶指標、胰島素水平及抵抗情況和FFA均與疾病密切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