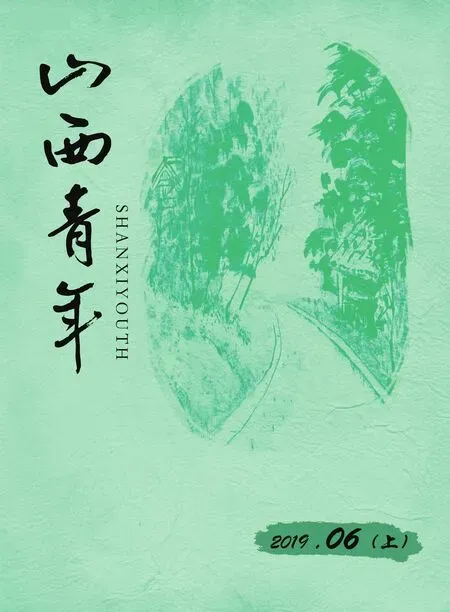希望理論介入犯罪未成年人希望感提高的個案研究
王亞梁
(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務學院,江蘇 南京 210094)
一、研究背景及意義
改革開放四十年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顯著成就、人們享受其豐碩成果的同時,各類社會問題也悄然滋生。其中暴力犯罪的案件不斷涌現,以青少年群體的增長最為突出,尤其是未成年人犯罪形勢嚴峻。在司法社會工作的開展中,值得注意的是,未成年人犯罪不僅對于受害者和社會和諧安定產生危害,也對犯罪未成年人造成了自我傷害。
結合2014年全國未成年人犯罪研究報告、南通市青少年社區服刑人員調查、南京市五轄區涉罪未成年人調查等研究,不難發現當前存在“我國犯罪未成年人性格特征為自卑的人數排在第二位”的嚴峻事實和“青少年因受到犯罪入刑等的打擊,自信心嚴重受挫,發展動力不足,產生認知和行為偏差”的普遍現象。因此,在司法社會工作中,關注并幫助涉罪未成年人消除心理障礙,提高希望感,使他們順利回歸社會成為司法社會工作者實務過程的重中之重。
希望作為人對未來的積極期望,心理健康的標志以及人們應對壓力和挑戰的精神力量,影響著人的許多方面,是個體對未來的一種積極體驗。研究顯示,由于未成年人在生理和心理方面都未臻成熟,希望理論的運用具有較顯著的介入效果。通過文獻分析筆者發現,希望理論在醫務、教育等方面都得到了較廣泛的運用,但國內在社會工作實踐中的理論運用仍十分稀缺,介入犯罪未成年人矯正方面的研究設計甚少。因此,本研究幫助犯罪未成年人克服希望感不足帶來的消極影響之余,也將有利于探索希望理論本土化運用的適用性等,具有極大積極意義。
二、研究理論基礎:希望理論
1991年,心理學家Richard Snyder及其同事開創了一種臨床和認知的希望理論,在心理學界獲得廣泛認可。Snyder等人認為希望模型主要包括三種成分:目標、路徑思維以及動力思維。
(一)目標:目標是希望的核心部分,在個體產生希望的過程中扮演極為重要的角色。它是希望的方向,同時也是希望的終點。目標設置的適宜程度越高,希望水平就越高,人們感知目標過高或過低時都不會付諸充分的努力。
(二)路徑思維:路徑思維就是開發大腦中的預測能力系統,在頭腦中設計出指向目標進而達成目標的計劃和方法,是通過目標在個人的現在和未來之間建立連接的途徑。高希望特質的個體往往能夠更好地規劃出替代路徑以及應對原有路徑受阻礙的境況。
(三)動力思維:動力思維是推動個體產生目標,并沿著所設計的實現目標的路徑前進的維持系統。這是希望的動機因素,即個體運用路徑和策略達成目標的信念。動力思維能夠決定個體的目標產生、路徑設計的過程,并為個體提供堅持下去的動力和支持。

三、案例分析及介入
(一)案主的介紹
案主J某,男,17周歲,犯盜竊罪,于2017年4月8日被宣布附條件不起訴,考察期6個月。經過《艾森克人格問卷》測評,J某屬于性格較內向且情緒不穩定類型。在考察期順利結束后,通過跟蹤調查發現J某因在工作場所與同事發生沖突辭職,生活狀態陷入不穩定,面對困境存在逃避和消極思想。針對此情況,筆者與案主進行了詳細溝通,并使用《成人素質希望量表(ADHS)》對J某進行希望素質的評估,發現案主確有希望感不足、動力缺乏的問題,因此開展此次個案輔導工作。
(二)案主問題的分析
通過前期訪談、量表測量以及進一步的調查走訪后,筆者發現了降低案主希望感的三個主要因素:
1.沒有接納事件及自我和解
越軌行為產生后,案主較多地采用否定、情感隔離等壓抑自己的情緒,并未真正意識到案件已經完結,其仍然是一個壓力來源。在第二次工作的突發事件中,案主認為自己受到孤立和譴責,激發了之前的悲傷體驗,加深了無力感。
2.對自我的認知水平較低
案主于初中輟學,獨立生活并從事服務員,受到的教育和關懷指導不足,學習成長經驗和認知發展水平有限。案主對自身的性格、能力、資源、優勢的認知較消極且不全面,發展的期待感和希望感較低,向上成長的動力不足。
3.對工作喪失了追求
案主獨自生活工作以來一直從事餐廳服務員工作,而在工作場所發生的越軌行為及與同事的沖突,使案主對重回這個工作環境存在抵觸。而尋求其他工作機會的能力、經驗和自信心不足,害怕遭到拒絕,自我否認,畏難情緒重。
(三)個案的計劃和實施
根據對案主問題的分析,在希望理論框架的指引下,本次輔導的目標是:
1.系統地幫助案主通過正確認知、思考及達成目標來改善希望感水平——通過完成對事件的接納重新樹立信心;通過獲得重要他人和自身的認可和接受對自我有更全面的認知;通過尋找新工作來促進自我價值的實現。
2.在此過程中注重培養案主的目標、路徑思維和動力思維,增強案主未來保持并提高希望感的能力。
在目標的指導下,筆者共開展了四階段的個案介入:

個案輔導的過程
四、個案的效果評估
(一)認知行為轉變分析
通過對訪談記錄、觀察記錄和案主自我陳述等材料進行分析和評估,筆者發現,經過整個干預過程,案主在自我和解、自我認知、自我實現等方面得到改善:
1.對事件的接納和認知使自我從失去轉向和解
案主對該案件存在回避和羞恥的態度,一直難以釋懷并自我貶低。通過幫助案主事件的進行正確認知并接納,從其他真實案例受到鼓勵和教育開始新的探索,案主對于該事件是個“傷疤”的態度有明顯轉變,對未來更有信心。
2.對自我有更全面的認知
案主從小的成功體驗并不多,初三輟學、經濟緊張、工作受挫等負向境況使案主容易自我否定,沒能認識到自身的優勢和資源。而經過此次輔導,案主在情緒疏導后更冷靜和全面地認識了自己,補全了自我的多個維度,更加認可自我。
3.找到了新工作來促進自我價值的實現
案主在社工的幫助下通過一系列探索和回顧,循序漸進地尋找一份合適的工作,最終確定了去合肥投奔表哥學裝修。通過后續追蹤,筆者了解到案主仍在表哥處跟著師傅做圍墻板組裝,一邊學習技術一邊工作。雖然身體負荷較大,但案主較認真和細心,也獲得了師傅的認可,對自己的能力和未來的發展具有信心。
(二)量表測量結果分析
為提高評估的科學性,筆者應用《成人素質希望量表(ADHS)》對案主進行了前后測量。對比數據發現,案主的路徑思維和動力思維得分都各有2分提高。盡管提高幅度不大,但希望感提升本就是一個緩慢的過程,改變后形成的良性循環將幫助案主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朝著積極方向發展。
綜上所述,此次干預有效增強了案主的希望信念與內在能量,幫助其順利回歸社會及健康發展,證實了希望理論框架下的社工個案輔導可以提高犯罪未成年人的希望感。同時,此研究一定程度上拓寬了犯罪未成年人的研究領域,豐富了希望理論框架的實踐范圍,立體地展示希望理論教育和改造未成年犯相結合進行研究的可行性和意義。筆者相信,通過更多學者的研究和實踐,希望理論將為司法社工干預犯罪未成年人的研究和實務相關維度的發展貢獻更多的力量,促進司法社會工作的開展針對失足青少年真正做到“安其身、育其心、正其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