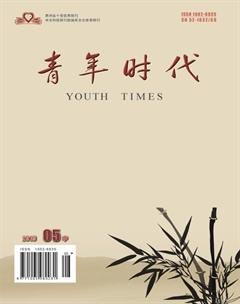文化與自我概念取向研究綜述
林雨雁 胡志偉
摘 要:自我概念是自我的核心成分,它既是自我認識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自我體驗和自我調節的基礎。自我概念取向研究將個體置于社會的大環境之下,在社會事件中研究個體在某種穩定的心理因素驅動下形成的心理和行為傾向規律。近年來,東西方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外來文化大量引入,給當前國內文化環境帶來了極大的沖擊,本文試圖探索中國人自我的特點與現狀。
關鍵詞:文化;自我概念;自我建構
在文化與自我概念的關系中,最具影響力的當屬自我建構理論模型。Markus和日本學者Kitayama在進行了大量的自我概念跨文化研究后提出了一個廣為人知的文化與自我概念模型。這一模型極大的推動了心理學界從尋找自我概念的普遍模型,到探索大的文化背景下自我概念的具體探索。
Markus從文化的角度區分了兩種文化下的自我概念典型特點。亞洲文化下個體強調個體與他人的關系,注重和諧友好的人際交往氛圍,在人際關系的背景下建立自我表征,Markus將這種自我概念表征方式稱為依存型自我建構(interdependent self-construal)。與之相對應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個體追求個體的獨特性,以個人的能力發展、愛好特點和人格特質建立個體的自我表征。這種強調獨立自我的概念表征方式被稱為獨立型自我建構(independent self-construal)。
與Markus自我建構理論體系相一致的還有Brewer和Gardner提出個體建構自我概念的三個來源:個體自我、關系自我、集體自我。由于個體特質的不同,自我建構的來源強度上存在差異。Brewer與Markus的理論較為一致,在三個類別上存在著一一對應關系。Sedikides 等人將這一理論體系命名為三重自我建構理論(the tripartite model of self-construal)。
對于東西方被試在自我建構上的差異,有研究者從思維方式的角度提出了解釋。Peng和Nisbett指出這種差異是民族在歷史演變的過程中形成的元認知模型的體現。這一歷史的沉淀過程包括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文化傳統等。東亞文化以農耕文化為主要生產生活方式,由于農耕活動的復雜性,相信萬物皆有聯系,沒有獨立存在的事物。而西方文化從游牧或漁獵文化發展而來,以世界不變的觀念為主,凸顯個人能力。
Peng和Nisbett 從文化的歷史演變的角度探討了東西方文化在自我上的差異,在對文化和自我的探討中提出了樸素辯證思維的理論,即東方農耕文化以事物聯系,且世界在不斷變化的文化角度,在自我概念方面體現為東方文化群體下的個體在自我認知中存在著更多矛盾的、變化的信息,而西方文化下的個體并不具備這種特征。隨后,研究者在決策判斷,個人情緒體驗、自我的研究領域中都驗證了這一差異。柏陽,彭凱平等以IAT范式為研究工具的內隱辯證自我研究中也證明了這一差異,即中國被試將自我與辯證性的概念聯系得更緊密。
我國的心理學對自我本土化的探討開始得較晚。從臺灣學者黃瑞煥(1973),楊國樞(1974)開始才逐漸開始對自我的研究。而正式開始具有中國特點的本土化自我研究開始于楊中芳(1991)的《回顧港臺“自我”研究:反省與展望》一文。同年楊中芳在另一篇文章《試論中國人的“自己”:理論與研究方向》中提及中國人自我的概念分析:(1)華人的自我發展由道德標準和社會規范內化形成道德自我;(2)華人自我在任何情境下都依禮行事,維護社會秩序;(3)華人期待經歷復雜的自我修養,通過克制、改進、超越自我來成為一個有德行的人;(4)針對個人錯誤,華人重視以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評的方式;(5)自我的界限有伸縮性,在心理上包括多人,甚至一個團體,形成一個大的自我;(6)華人的公開自我和私密自我差異甚大,他們接受并善于忍受二者之間的矛盾及沖突。楊中芳為自我的本土化研究奠定了基礎,此后的研究中陸續從以上提及的幾個方面展開。
楊國樞對中國人自我開展了系統的研究,并以社會取向論為主要基礎建構了華人的“自我四元論”。即中國人的社會取向包括四個次級取向,關系取向、權威取向、家族取向、他人取向。關系取向是個體在與跟自己平行的人際交往中的互動;權威取向是個體在與垂直式的上級及相關他人的相處;家族取向即以大家庭或者衍生到公司等團體內的互動模式;而他人取向則是一種非特定的他人,概化的他人,如“別人”“江東父老”。這四種取向與Markus和Sedikides 等人自我建構中的依存型自我建構有著相似之處,都對自我概念中的建構模型進行了探討。楊國樞的社會取向更詳細地以權威、家族、他人(尤其是非特定他人)更貼合中國人的特點。
在跨文化研究中,以東西方文化的對立為脈絡,探索兩種文化下的個體在自我與周圍環境和人際關系上的不同(互依自我和獨立自我)。當前,東西方文化的交流與融合是世界發展的大趨勢,當下身處文化沖擊中的中國人的自我概念是否受到現代的“個人主義”文化沖擊而發生變化呢?
西方學者Triandis認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以及現代化的進程,集體主義下的互依自我會被個人主義文化的獨立自我所取代。楊國樞等人在最初建構理論時也將社會和個人作為一個維度的兩極,之后在研究中不斷修正理論,揚棄了古典現代化理論。隨后確定傳統與現代是兩組獨立的類型,在不同的文化中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因而,楊國樞建立了社會取向個人取向的二維模型,認為二者可以并存,他將兼容了現代性與傳統性的自我稱為“雙文化自我”。
Markus與Kitayama在“自我建構理論”中,曾假設“獨立我”和“互依我”是兩套可以并存于同一文化中的自我,只是由于個體差異,具體表現會有不同。陸洛等人在以臺灣地區的個體為對象的一系列研究中發現,互依自我和獨立自我這兩套自我系統的“自我融合”現象極為明顯。但是文化差異依然顯著存在:臺灣地區“互依自我”比“獨立自我”要更強。陸洛在對臺灣個體與英國個體的自我概念的研究后指出,在文化融合交流的背景下,原生文化體系仍然會保持它的主流地位。
陸洛針對自我社會性和個人性融合的現象提出了“折衷自我”(composite self)概念。現代生活中,中國人也呈現出越來越多傳統性與現代性共存的現象。集體主義文化下,某些生活的場所(如需要獨立行為的工作環境)中個體也需要培養獨立的自我概念。陸洛認為當下的中國人,一方面以文化傳承的方式,保持著傳統的互依包容的自我,借以維持適當的人際交往;另一方面,由于生活方式生產方式的變遷,生活在現代文化下的中國人也需要借取獨立自我中的元素,來追求個人的成就,注重做事的效率。這一自我融合的現象也在更多的實證研究中得以證實。
楊中芳從傳統文化的角度,以及中國人在自我上極其矛盾的表現提出了中國人的自我是一種“中庸式自我”。她在與林升棟對自我建構進行研究,他們指出在自評問卷上兩極量表中間打鉤的人并不能按照量表分類歸為無自我概念組,他們可能只是自身融合了很多看似矛盾甚至對立的特質。他們提出這群人的自我概念可能是在社會環境和自我之間尋找平衡的中庸自我。他們的這一論斷挑戰了自我建構的二維假設,而以中庸自我的特征來解釋中國人一些極具中國特色,卻又無法為西方所理解的行為模式。楊中芳的研究回歸到中國傳統文化中,配合現代化的心理學研究方法,對中國人特有的中庸自我進行系統研究,組成了“中庸社會心理學”的研究內容。楊中芳認為,中國人特有的中庸世界觀體現的是情境與自我的交融、交變、交感。個體在“過”與“不及”之間“拿捏分寸”,視對立面陰陽兩極為“狀態”,能夠接受即此又彼的狀態,行動的目標是要達到“和諧”。她與趙志裕編制了中庸量表,并建構了中庸實踐思維體系構念圖。其中構念圖中包含著13個關鍵的構念包括兩極感知,轉換感知,待人守則,拿捏意識,處世信念,趨勢掌握,公我意識,私我意識。
在心理學本土化的過程中,許多學者主張“多元典范的研究取向”,即視問題情況的需要,采取最適當的研究典范,遵循該一典范的游戲規則,并用嚴格的判準,來評估學術研究成果。。
自古以來,中國人奉行著一套迥異于西方的自己的行為模式,處事風格、思維習慣不是西方心理學界依據自我建構的思想所界定的“互依型自我”所能概括,也非集體主義文化下的自我能夠解釋。中國人自我中的兩面性是幾千年文化沉淀的結果。“當面一套,背后一套”“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等兩面性的俗語在中國人中卻有十分廣闊的市場。這牽扯出中國人豐滿、迂回、動態、有深度的自我概念。
參考文獻:
[1]李承貴.“自我認知范式”的形成、意義與問題[J].天津社會科學,2019(02):33-43.
[2]肖前國.正念自我的理論建構與實證研究[D].內蒙古師范大學,2018.
[3]郭本禹,修巧艷.馬庫斯的自我社會認知論[J].西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7(01):17-21.
[4]潘志然,崔紅.獨立型與依賴型自我:Markus等的自我結構研究[J].心理與行為研究,2004(02):465-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