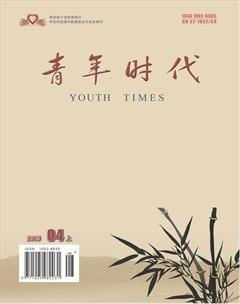試析違法權(quán)益披露義務(wù)的法律規(guī)制
蔣經(jīng)緯
摘 要:近年來(lái),上市公司被“門口的野蠻人”通過(guò)舉牌爭(zhēng)奪控股權(quán)事件頻出,其問(wèn)題主要來(lái)源于權(quán)益披露,其中規(guī)定有持續(xù)增持權(quán)益披露制度的《證券法》第86條及其違法處罰認(rèn)定便成為監(jiān)管部門面臨的巨大挑戰(zhàn),一時(shí)成為學(xué)界討論熱點(diǎn)。
關(guān)鍵詞:權(quán)益披露;大額持股;法律責(zé)任
一、概念釋義
隨著證券市場(chǎng)的發(fā)展走向深水區(qū),證券市場(chǎng)上越來(lái)越多的散戶、風(fēng)險(xiǎn)投資基金不滿足于少量持股交易帶來(lái)的收益,而是頻頻舉牌追求擁有上市公司的控制權(quán)以及更多的參與管理權(quán)限,從而獲得資本聚集效益,獲取巨額邊界利潤(rùn)。而這里所說(shuō)的舉牌,便是即依據(jù)“權(quán)益披露制度”,任何一個(gè)持有上市公司流通股達(dá)到法定一定比例或達(dá)到一定比例后持股比例發(fā)生增減變動(dòng)的投資者,負(fù)有依法披露權(quán)益持有情況的義務(wù)。
二、問(wèn)題的提出
(一)違法權(quán)益信息披露義務(wù)下是否適用《證券法》193條之規(guī)定
1.主體適格性
《證券法》第193條規(guī)定的信息披露義務(wù)人是發(fā)行人、上市公司或者其他信息披露義務(wù)人,而第86條規(guī)范的主體是普通投資者,那么投資者是否屬于其他信息披露義務(wù)人呢?筆者認(rèn)為,前者應(yīng)當(dāng)為后者所包括,根據(jù)《證券法》86條規(guī)定,投資者有義務(wù)向證監(jiān)會(huì)、證券交易所報(bào)告、協(xié)助上市公司公告,其內(nèi)容與《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辦法》第46條第一款所要求的披露義務(wù)內(nèi)容契合,理應(yīng)屬于法規(guī)所認(rèn)定的信息披露義務(wù)人,因而主體具有適格性。
2.行為適格性
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guī)定適用于不按照有關(guān)規(guī)定披露信息/提交有關(guān)報(bào)告的行為,或者所披露的信息/報(bào)告含有虛假記錄、誤導(dǎo)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的行為,其適用的合理性是不容爭(zhēng)議的,但是于第八十六條規(guī)定的在禁止轉(zhuǎn)讓期交易股票的行為是否也適用第一百九十三條尚無(wú)定論。從近年來(lái)證券監(jiān)督管理委員會(huì)(CSRC)的監(jiān)管實(shí)踐來(lái)看,監(jiān)管機(jī)構(gòu)對(duì)這種行為也同樣適用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guī)定。作者認(rèn)為,這一認(rèn)定存在不足之處。首先,根據(jù)本文的規(guī)定,行政處罰的內(nèi)容包括責(zé)令改正、警告和罰款。雖然第193條沒(méi)有具體說(shuō)明“改正”的具體內(nèi)容,但根據(jù)上下文解釋,責(zé)令改正的責(zé)任應(yīng)解釋為尚未披露的披露,虛假披露的真實(shí)披露,重大遺漏的補(bǔ)充披露。重大遺漏的進(jìn)行補(bǔ)充披露即為改正。其次, 《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僅與第八十六條規(guī)定的利益披露義務(wù)相對(duì)應(yīng),并不涵蓋投資者在禁止交易期內(nèi)不得交易股票的義務(wù),而這便導(dǎo)致了立法事故的出現(xiàn),即違反權(quán)益披露義務(wù)同時(shí)違反權(quán)益披露義務(wù)和與禁售期內(nèi)交易股票,其所應(yīng)承擔(dān)的法律責(zé)任是等同的。因此,如果行為人在違規(guī)了大量增減持之后僅適用第193條,第86條規(guī)定的禁止交易期內(nèi)不買賣的義務(wù)無(wú)疑將變成一張廢紙。
(二)違法權(quán)益信息披露義務(wù)下是否適用《證券法》213條之規(guī)定
1.主體適格性
與購(gòu)買股票的普通投資者不同,收購(gòu)者的目的是獲得對(duì)目標(biāo)公司的控制權(quán)。首先,根據(jù)“證券法”第85條投資者可以通過(guò)要約收購(gòu)、協(xié)議收購(gòu)和其他合法手段收購(gòu)上市公司,但沒(méi)有具體說(shuō)明什么是“其他合法手段”。作為收購(gòu)人,通常的方式是協(xié)議收購(gòu)或要約收購(gòu),其表現(xiàn)形式是在30%的時(shí)間觸發(fā)要約收購(gòu)時(shí)訂立收購(gòu)協(xié)議或股份轉(zhuǎn)讓協(xié)議。然而,權(quán)益披露制度只要求通過(guò)場(chǎng)內(nèi)交易的投資者在持股達(dá)到5%和5%的倍數(shù)(小于等于30%)披露權(quán)益信息。故不應(yīng)將“其他法律形式”解釋為已達(dá)到5%但缺乏購(gòu)買意向的投資者。
其次,從“證券法”第86條和第87條披露的內(nèi)容的不同之處可以得知,《證券法》對(duì)收購(gòu)的披露要求更為詳細(xì)和全面,如要求揭露收購(gòu)的意圖等。但由于沒(méi)有對(duì)大股東作此強(qiáng)制要求,筆者認(rèn)為,將持有5%股權(quán)的投資者與收購(gòu)人混為一談,并以此方式適用第213條是缺乏理論依據(jù)的。
2.責(zé)任認(rèn)定
筆者認(rèn)為違法權(quán)益披露義務(wù)適用《證券法》主體不適格,退一步說(shuō),即使按照某些學(xué)者觀點(diǎn)認(rèn)為主體能夠適用213條,其 “責(zé)任改正”亦為補(bǔ)充公告和報(bào)告的義務(wù),而并非在一定期限內(nèi)禁止買賣,因?yàn)樨?zé)令改正在規(guī)則結(jié)構(gòu)上是“收購(gòu)人未按照本法規(guī)定履行上市公司收購(gòu)的公告、發(fā)出收購(gòu)要約等義務(wù)的”的順延,因此對(duì)應(yīng)的也僅為履行公告和報(bào)告的義務(wù)。
(三)違法權(quán)益信息披露義務(wù)下是否適用《證券法》204條之規(guī)定
從《證券法》第204條條文來(lái)看,若想適用《證券法》204條就必須解決限制轉(zhuǎn)讓期的認(rèn)定問(wèn)題,即《證券法》第86條規(guī)定禁止交易期是否包括在204條規(guī)定的限制轉(zhuǎn)讓期當(dāng)中。一般認(rèn)為,《證券法》第204條是對(duì)第38條的懲罰性規(guī)定。
有學(xué)者針對(duì)適用第38條、第204條提出反駁觀點(diǎn),認(rèn)為第204條的閑置轉(zhuǎn)讓期應(yīng)僅理解為股票禁售期,即實(shí)質(zhì)上約束的是《公司法》第141條規(guī)定的董監(jiān)高及發(fā)起人股東在禁售期內(nèi)轉(zhuǎn)讓股票的行為。法律也僅僅規(guī)定禁止賣出股份,而不包括股份買入行為。因此不論是主體還是行為上都與規(guī)定權(quán)益披露義務(wù)的第86條所不符。
然而,筆者基于以下理由,認(rèn)為此類觀點(diǎn)有待商榷:
首先,根據(jù)法律當(dāng)然解釋可知,第38條規(guī)定的限制性規(guī)定自然包含兩種類型,一類為法律對(duì)證券交易在規(guī)定時(shí)期內(nèi)做出限制轉(zhuǎn)讓數(shù)量的規(guī)定,例如《公司法》第141條第2款“公司董事、監(jiān)視、高級(jí)管理人員在任職期間每年轉(zhuǎn)讓的股份不得超過(guò)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的25%”,另一類則為法律對(duì)證券交易在規(guī)定時(shí)期內(nèi)作出禁止出售規(guī)定,例如《公司法》第141條第1款規(guī)定“發(fā)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票,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內(nèi)不得轉(zhuǎn)讓。”即通常所說(shuō)的股票禁售期。而《證券法》第86條規(guī)定的禁止交易期內(nèi)不得買賣股票的行為當(dāng)為第二類所指的規(guī)定期限內(nèi)禁止股票買賣的行為,因此行為可適用第38條的規(guī)定。
其次,第38條與第204條并未指明該等規(guī)則的主體,因此不應(yīng)當(dāng)狹隘理解為《公司法》第141條規(guī)定的董監(jiān)高及發(fā)起人股東,而應(yīng)理解為任何在限售期內(nèi)買賣股權(quán)的股東。以符合權(quán)益披露關(guān)于投資者的認(rèn)定。
此外,最近幾年,各地證監(jiān)局主要依據(jù)《證券法》第一百九十三條的規(guī)定懲罰非法減持,但是,對(duì)機(jī)構(gòu)投資者來(lái)說(shuō),第一百九十三條規(guī)定的最高罰款只有六十萬(wàn)元。與非法增減股權(quán)所獲得的利益相比,這種處罰力度較小。若適用第二百零四條的規(guī)定,可以對(duì)買賣證券處以等額罰款,進(jìn)而對(duì)非法增持減持構(gòu)成更大的威懾和處罰,以避免險(xiǎn)資舉牌,不顧一切地侵害中小投資者的利益。
(四)禁止交易期內(nèi)買賣行為效力與民事責(zé)任
根據(jù)《證券法》第86條的禁止性規(guī)定,有學(xué)者提出據(jù)此原因《民法通則》第58條第5款或者《合同法》第52條第5款,認(rèn)為超過(guò)規(guī)定限額買入股票的交易屬于“違法法律、行政法規(guī)的強(qiáng)制性規(guī)定”,因而認(rèn)定該交易無(wú)效。
那么在交易結(jié)果既定的前提下,是否可以請(qǐng)求違規(guī)交易者承擔(dān)民事?lián)p害賠償呢?
根據(jù)《證券法》第120條規(guī)定,非法交易者不得免除其民事責(zé)任,非法交易所得利益按照有關(guān)法規(guī)懲處。于是,如果背離披露權(quán)益義務(wù)對(duì)股票出賣方造成損害,理論上也應(yīng)賠償其民事上的經(jīng)濟(jì)損失。然而,關(guān)于這種民事責(zé)任,《證券法》及《上市公司收購(gòu)管理辦法》均無(wú)明確規(guī)定,導(dǎo)致現(xiàn)實(shí)中因險(xiǎn)資舉牌而自身利益受損的股東向法院起訴請(qǐng)求獲得民事賠償大多難以向法院提起民事賠償訴訟,并獲得法院的同意。
這種可得利益的損失是否應(yīng)予賠償,還考慮到股票賣方的損害結(jié)果在多大程度上與犯罪者的行為相關(guān)聯(lián),即使犯罪者確實(shí)違反了披露義務(wù),讓股票賣方在不知道新信息的情況下作出出售股票的投資決定 ,但是股票在稍后階段上漲,這可能是由于違法者所作的補(bǔ)充披露所致,也可能是由證券市場(chǎng)的其他因素引起的股價(jià)波動(dòng),事實(shí)上是很難得到證據(jù)的。事實(shí)上,投資者很難證明其損失的經(jīng)濟(jì)數(shù)額,以及這些損失與非法舉牌者之間的關(guān)系,恐怕投資者要得到法庭的同意并非易事。
三、權(quán)益披露制度的完善建議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國(guó)的權(quán)益公開制度沒(méi)有專門的責(zé)任清單和實(shí)施細(xì)則,實(shí)踐中確實(shí)存在規(guī)制無(wú)門的情形。因此,對(duì)上市公司進(jìn)行背后偷襲的黑天鵝事件越來(lái)越多,權(quán)益公開制度保護(hù)中小股東權(quán)益的制度宗旨恐難以實(shí)現(xiàn)。因此筆者擬就以下幾方面探析完善權(quán)益披露制度法律責(zé)任的合理途徑:
(一)區(qū)分“大額持股投資者”與“收購(gòu)人”
我國(guó)在2002年就該事項(xiàng)立法時(shí),將上市公司收購(gòu)和大股東持股劃分為兩類。即《公司收購(gòu)管理辦法》和《上市公司股東持股變動(dòng)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但2006年《上市公司收購(gòu)管理辦法》修訂后,兩部規(guī)章合并在一部法規(guī)中,《信息披露管理辦法》不再適用。然而,這很容易讓廣大股民錯(cuò)認(rèn)為大額持股與收購(gòu)兩者為同一概念,導(dǎo)致法律法規(guī)的使用混亂,進(jìn)而損害了權(quán)力披露制度的立法獨(dú)立性。然而,隨著證券市場(chǎng)的發(fā)展,法律對(duì)利益披露的精細(xì)要求也越來(lái)越高,因此分別制定一套較為完善的利益披露管理辦法勢(shì)必為大勢(shì)所趨。
(二)適當(dāng)增加違規(guī)者的法律責(zé)任
根據(jù)《證券法》一九三條及二零四條規(guī)定限制期內(nèi)買賣股票的法律責(zé)任,相比于193條“三十萬(wàn)元至六十萬(wàn)元的罰款”,204條“處以買賣證券等額以下的罰金”更能以將違規(guī)增減持所得收益以罰款的形式予以沒(méi)收的方式達(dá)到限制違規(guī)增減持有行為的懲處目的。如果《證券法》第一九三條規(guī)定繼續(xù)適用,立法與監(jiān)管機(jī)構(gòu)應(yīng)當(dāng)修訂草案加重該條的懲罰力度并補(bǔ)充對(duì)應(yīng)承擔(dān)行政責(zé)任的條款,包括不限于沒(méi)收違法所得、在改正行為前不享有其購(gòu)買股票的表決權(quán)等。其次,對(duì)于民事責(zé)任,應(yīng)當(dāng)參照歐美等國(guó)散戶投資者的集體訴訟制度,明確民事賠償責(zé)任的賠償額計(jì)算公式,要求違規(guī)大額持股者承擔(dān)對(duì)受損害的投資者的合理賠償責(zé)任。
參考文獻(xiàn):
[1]馬驍著:《上市公司并購(gòu)重組監(jiān)管制度分析》(第1版),第33頁(yè),法律出版社,2009年12月。
[2]李振濤.我國(guó)上市公司大額持股變動(dòng)的法律責(zé)任探析[J].法律適用,2016(1):106.
[3]《證券法》第三十八條依法發(fā)行的股票、公司債券及其他證券,法律對(duì)其轉(zhuǎn)讓期限有限制性規(guī)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內(nèi)不得買賣。
[4]徐聰.違反慢走規(guī)則買賣股票若干爭(zhēng)議法律問(wèn)題研究[J].法律適用,2015(12):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