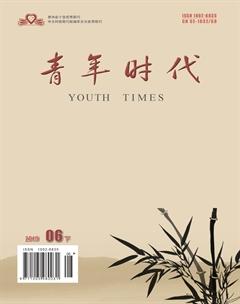表達自由與限制
曾凱
摘 要:自近代以來,自由問題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重視。而表達自由作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也備受重視。表達自由也有其界限,對表達自由限制只是手段,保障才是目的。在表達自由與限制中間把握其中的度,對人類社會的進步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表達自由;限制
1948年《人權宣言》第19條規定:“人人享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此項權利包括持有主張和發表意見的自由。”1966年《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9條進一步規定:“人人持有主張,不受干涉。人人有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此項權利包括尋求、接受和傳遞各種消息和思想的自由,而不論國界,也不論口頭的、書寫的、印刷的、采取藝術形式的、或通過他所選擇的任何其他媒介。”而我國的現行法律也對這項權利作了相應的詮釋。我國《憲法》第41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游行、示威的表達自由是指公民通過口頭、書面以及互聯網、影視作品、錄音、電子出版物和其他媒介表達思想和見解的自由。”
一、什么是表達自由?
表達自由雖然被視為公民的一項基本權利,但是,對于它的定義卻是眾說紛紜,就說我上面提到的三條法律條文,它們對表達自由的詮釋也不盡相同。很多學者將表達自由解釋為“言論自由”,他們認為,表達自由等同于言論自由,內容涵蓋了亞黁、出版、新聞、印刷、創作、思想、演講、講學等詞匯和形式。[1]但有的學者的觀點卻有所不同,他們認為表達自由的內涵要比言論自由的內涵更加豐富,表達的內涵包括言論。還有的學者認為廣義的言論自由就是表達自由的中心。也有學者認為:“在英美法中,表達自由是僅指表達自己思想的自由。”[2]更有學者認為,表達自由一般指言論自由和接受與傳播信息和觀念的自由。
面對形形色色的解釋,我們難免會感到困惑,那么究竟該怎樣理解表達自由呢?我建議可以從三個層次來分析表達自由的內涵:
首先是“表達”。眾所周知,當我們想要表達什么內容時,我們首先就會有一個想要表達的基本內容,然后再用某種形式將這一內容表達出來,這當然也可以被理解為海德格爾的“在場”。也就是說,我們將不在場的內容帶入場中,使別人能夠接觸到。至于表達內容,它一般指人們隱藏或存在于內心的感受、心理與意識,它們通常表現為思想、情感、意見、主張觀點等。因此,我們在談表達的內涵時,既要體現出它的內容,同時也要體現出其表達的手段和媒介。這樣我們就可以把表達理解為通過一定的手段和媒介,將人們想要表達的內容公開的展示出來,使得人們能夠知曉。
其次是“自由”。自由是近代以來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我們難以給自由下一個準確的定義的。但是,具體到表達自由這個概念里,我們通常將其理解為一種否定性的自由,即這種自由的關鍵問題不是主體的意識,而是否定外在于我的存在強加在我身上的意志以及干擾。它是“免于干預、限制、侵犯或剝奪的自由。”[3]所以,這里的自由可以被理解為不被妨礙,不被打擾以及不被限制和侵犯。
最后是“權利”。如前面所述,表達自由是公民的一項權利。既然說它是一項權利,那么,在現行的制度構建中,它必然是被法律規定、認可和保護的。對于這一點我想是毫無疑問的,因為任何一種被承認的權利都有相應的法律基礎,例如財產權,生命權等。我們不能說搶劫是一種權利,因為它不具備任何法律基礎。有人可能會說,法律的提出不正是為了保障權利的嗎?為什么我會說只有具備法律基礎的才能被稱為權利呢?因為現行的實證法應該體現著自然法的性質,而我們的權利不正是被自然法所規定的嗎?可以說一切權利都是從自然法中衍生出來的。
綜上所述,表達自由可被界定為:公民享有的受法律規定、認可和保障的,使用各種媒介手段與方式公開發表、傳遞自己的意見、主張、觀點、情感等內容而不受任何其他人或組織干涉、限制或侵犯的權利。
二、保障表達自由的重要性
首先,表達自由能夠促進人們對真理的探求和發現。縱觀歷史,如果一個社會能容忍對表達自由任意專橫限制,那么就會堵塞真理和明智判斷的出版和流行。一個限制言論的社會將會是一個沒有生機的社會,相反,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才能呈現出生機勃勃,各種思想百花齊放的情景。而真理的火花通常也會出現在各種思想的激烈碰撞之中。對于這一點,密爾就主張,言論市場是人們獲取真理的重要途徑,因此要廣開言路,充分發揮言論辯論中出真理的作用。[4]而在我國歷史上,最明顯的例子就是春秋戰國時期和清朝時期,春秋戰國時期,雖然戰火頻發,但是,仁人志士為了自己的理念而四處奔走,在學術上卻呈現出一派生機勃勃。反觀清朝,統治者實行文字獄,雖然一度出現過康乾盛世,但是民眾的思想終究還是被囚禁在了籠子里,整個社會死氣沉沉,毫無生機可言。在這樣的社會里,真理是很難被挖掘出來的。
當然對于真理這個概念,學術界正義也有很多。人們對真理的爭議主要體現在真理是否是絕對的、普遍的和不變的。我認為,不管真理是不是絕對不變的,表達自由對于它的發現都有重大意義。如果所謂的真理是唯一的絕對不變的,那么,言論自由就可以用來檢驗人們所謂的真理是否就是那個唯一不變的真理,正所謂理不辨不明,我相信,真正的金錠不會在人們的懷疑聲中就變成錫錠,真正的真理也會在激烈的爭辯后發出它那耀眼的光芒。在古代,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曾經一度被認為是絕對不變的真理,但是自從牛頓的物理學登上歷史的舞臺后,亞里士多德的物理學就變得一文不值,這也就是說,人們公認的真理在發表自由的環境中被推翻,新的所謂的真理被戴上了王冠。真正的真理也將最終會在這種一破一立中被發現。美國的霍姆斯大法官曾經說過:“對真理最好的檢驗是一種思想在市場競爭中所表現出的使自己得到承認的力量。”[5]如果真理不是絕對不變的,真理只是相對的真理,那么表達自由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因為,如果真理不是唯一的,那么,任何一種言論都可能是真理,只有人們自由的發表各種思想,這些不同的不為人知的真理才會被發現。如果對發表自由進行極端限制,那么,后果可能是社會上只剩一種聲音,各種觀點的爭鳴與交鋒只會是一種幻想。
其次,從個人層面上來說,表達自由可以促進人的自我實現。人與人之間是平等的,我們都具有平等的人格,有著平等的尊嚴,也有著平等的思想。思想是沒有貴賤之分的。正因為如此,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有平等的機會表達自己的思想,釋放自己的個性。在古代,很多仁人志士感嘆自己壯志難酬,只能看著破碎的山河黯然神傷。在如今這個要求展現個性的時代,如果表達自由受到過多的限制,那么,很多人的思想將無法被表達,個性也將無法釋放,更不用說自我實現了。我們都知道孔子周游列國的故事,雖然他的思想主張并未得到當時的統治者們的認同,但是他的思想確是廣泛流傳了出去,并且伴隨了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試想,如果當時的各個諸侯國都嚴格限制人們的發表自由,那么孔子恐怕連周游列國的機會都沒有吧!更別說他的理想能否實現的問題了。
最后,從整個社會層面上來說,表達自由能夠促進民主社會的建設。對于這一點,相信大家感受都很深刻。什么是民主,簡單說來就是自己做自己的主人,一切政策都能體現所有公民的主張。民主觀念是人民實踐表達自由、參政議政的孕育土壤。[6]同時,發表自由同樣能化作春泥來滋養這片土壤。表達自由形成的社會輿論力量,對于監督政府、遏制腐敗起到了重要作用。盧梭、洛克等自然法學家人民有著先于法律與國家的自然權利,為了避免斗爭與提高社會安全系數,個人根據一紙契約將自然權利的一部分讓與政府,目的是使自然權利獲得更妥當的制度性保護。[7]這也就是說,政府的權利是來自于人民,所以政府頒布的政策也要體現民眾的意志。那么,民眾該怎樣參政議政呢?我認為最好的途徑就是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同時運用這項被法律賦予的權——表達自由來對政府進行監督。政府有什么不對的,我們應當直言不諱的指出來,這樣的社會才能進步。
三、表達自由的限制的合理性
既然表達自由是公民的一項基本的權利,那么,對這種權利進行限制到底是不是合理的呢?學術界普遍認為,對表達自由進行合理的限制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表達自由限制的理由來自于自由本身。在討論自由時,我們無法回避一個問題,即自由代表的是隨心所欲嗎?即康德所提到的自由的任意。面對這個問題,我們的答案肯定是否定的。自由是一種隨心所欲而不逾矩。自由是制度確定的多種權利和義務的復雜集合。各種各樣的自由指定了我們想做就可以決定去做的事情,在這些事情上,當自由的性質使做某事恰當時,其他人就有不去干涉的義務。[8]這也就是說,自由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你的自由不能或者應該盡可能少的妨礙他人的自由,因為我們是社會性的存在,在這個社會里,每個人都要自由,所以只能對每個人的任意自由進行限制,以確保人的相對的自由。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對表達自由的限制其實也是對他的一種保障。
其次,前面也已經提到過,表達自由是被法律所規定、認可和保障的。也就是說,我們從表達自由的定義中也可以看出,實際上表達自由是受法律限制的。情況為什么是這樣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首先得弄清楚實在法和自然法的關系。特別是近代以來,法學家們普遍認為,實在法必須體現出正當性,而正當性就是自然法的特性。自然法是同自然的理性、正義相吻合地生活的自然法則,實在法的制定必須體現出自然法的精髓。表達自由這項權利毫無疑問追溯到底是來自于自然法的,是自然法賦予了人們這項權利,因此,人們的公開言論就應該體現出自然法的正當性。這也就為表達自由提供了最原始的限制。
最后,在更重要的利益面前,對于一些可能是正確的言論進行限制同樣具有合理性,因為對言論的放任自流將可能會損害社會的公共利益。[9]例如,對國家的機密、商業秘密的公開出版等行為。而且,主張表達自由,更多是從表達者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的,有些表達者為了自己的快感,大肆傳播“黃賭毒”等負能量信息,這會對主動或被動接受者造成不良的影響,不利于他人甚至大到整個社會的發展。
四、怎樣對表達自由進行限制
毫無疑問,表達自由作為人們的一項基本權利,它應該被人們所擁有,這一點有一系列的法律作為保障,但是我們說同時也應該對這種權利進行限制,那么到底應該怎樣做呢?我認為我們要把握這其中的度,在表達自由和它的限制之間找到一個平衡點。美國大法官布蘭代斯在1927年“懷特尼訴加利福尼亞案”中指出:“只有在緊急情況下,壓制才是正確的。”[10]這也就說,如無必要,勿增限制,只有在某人的自由表達會對他人或社會造成損失的情況下,我們才考慮對他的權利進行限制。這就好比警察的治安工作一樣,只有某人的行為對他人造成了威脅,警察才有權利限制其自由。我們對表達自由的限制也要符合自然法的正當性,在表達自由沒有超出自然法的規定之下,我們是無須對其進行限制的。
參考文獻:
[1]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2頁.
[2]劉迪著.《現代西方新聞法制概述》.中國法制出版社,1998,第4頁.
[3]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頁.
[4]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2頁.
[5]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1頁.
[6]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5頁.
[7]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7頁.
[8]轉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律哲學與法律方法》.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第237頁.
[9]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4頁.
[10]王峰著.《表達自由及其界限》.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2006,第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