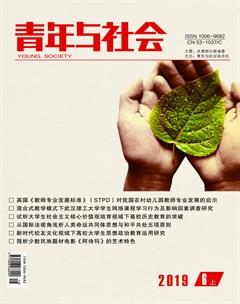淺議早期來華傳教士的不同傳教策略
摘 要:17世紀中葉之前來華傳教士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將中國傳教對象分為文官和百姓兩類,并施以不同的傳教策略。文章從語言、政治社會、本土宗教的角度論證傳教對象分類的合理性,并通過不同的傳教活動探討差異化傳教策略帶來的傳教效果。
關鍵詞:傳教對象;策略;效果
中世紀的歐洲因饑荒和疫情人口銳減,基督教卻得到廣泛傳播。除了通過贖罪券斂財,這一時期的基督教神職人員還通過心靈救贖的口號和宗教治療皈依了許多災民和病患。雖然傳教士源于巫術的宗教醫學實踐“干預了正常醫療活動的進行”,但這種實踐向來是基督教重要的傳教方式之一。
然而17世紀中葉之前來華的基督教傳教士并沒有嚴格地遵照歐洲同行的傳教模式。一方面明末的中國并沒有推行政教合一,單一宗教的影響力有限;另一方面雖然當時有天災和饑荒,但整體上看并沒有程度十分嚴重的大范圍生命健康危機。因而基督教的宗教治療實踐有有限的發揮空間,但克服各方的阻力才是一切傳教策略的前提。為了更有效地完成使命,傳教士根據采取了多種傳教策略。
一、傳教對象的區分
傳教士初入中國時,語言、政治、社會和本土宗教等都成為傳教的困難之處。只有將傳教對象大致分類,才能展開傳教工作。
首先,語言傳播方式上可以區別出不同人群。基督教教義需要被編譯為中文,以書面語的形式傳播。然而中國當時的文盲率高,具備讀寫能力的人集中在文人士大夫階層,因此,傳教對象被分成“文人士大夫”和“不識字的百姓”兩個群體。
其次,從個人對政治、社會生活的影響力考慮,需要在不同的傳教對象群體中構建差異化的基督教形象。中國的文官和皇帝掌握著絕對的政治權力,決定著基督教的合法性和地位,因此傳教事業的首要任務是獲得中國政治集團的支持,而顯然,僅僅編譯基督教教義并不足以實現這一目的。同樣,中國不識字的百姓群體雖然龐大,但以家族、家庭為基本社會單位的結構中難以構建歐洲社會常見的團結的信仰團體。所以傳教士需要以不同方式爭取皇帝、文官團體和相對較分散的百姓家庭、家族個體。
再次,中國已有的主流宗教也影響了基督教傳教對象的分類。中國并非歐洲的單一信仰國家,而是儒、釋、道和多種地方原始信仰并存的社會,因而傳教士必須平衡基督教與不同宗教在特定傳教對象群體中的影響力。例如,儒家思想深深影響著中國文官團體的語言和民眾的行為準則;佛教的因緣善惡概念在民間發揮著一定程度上的心靈救贖功能;而道教與煉金術、巫術等活動的結合又深深影響著中國帝王和百姓的健康觀。所以基督教傳教士不得不考慮受到一種或多種宗教影響的不同傳教對象接受基督教的方式。
二、差異化的傳教活動
如前文所述,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教對象因語言、政治、社會和其它宗教的因素被分為文人士大夫和教育程度有限的百姓。因此,雖然傳教的目的是為了在中國擁有更廣泛的基督教信徒群體,最終在全中國推行單一的基督教信仰,但傳教士在來華初期不得不開展完全不同的傳教活動。
傳教士在文官群體中的傳教動機主要是借助文官的社會地位、社會關系和在朝廷的影響力,獲得基督教在中國的“合法性以及政治上的庇護”,必要時由文官積極 “護教”、“揚教”。因此,文官教徒的發展重點有政治影響力、經濟實力和學習能力且心態較為開放的官員。對擁有一定社會資源的這一類人而言,基督教在歐洲社會提供的心靈救贖、宗教治療等功能并非必要,甚至可能完全沒有吸引力。正如公認的研究成果所顯示,傳教士針對這一群體的工作不僅限于教義的傳播,還包括贈禮、介紹西學和易服。來自西方的禮物或精美或新奇,滿足了中國官員獵奇、虛榮的心態;與中國官員討論天文學、數學等西方學科知識迎合了中國官員知識分子的求知欲,于是出現了眾多傳教士口述、中國官員筆錄合譯而成的西學書籍;而傳教士從著佛服到換儒服的變化也表明了他們爭取中國文官群體的意圖。值得注意的是,傳教士對中國文官群體開展的活動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傳教,有學者認為傳教士與中國官員對西學的探討甚至與傳教活動本身是矛盾的:“大多數在北京的傳教士需要花費大量的時間和中國文人交往……他們花在傳播福音上的時間就相對較少。”
對于教育程度有限的百姓而言,傳教士構建了另一種基督教形象。16世紀末,中國經歷了連年大寒低溫天氣、干旱以及隨之而來的嚴重饑荒,當地的政府官員在管理缺乏社會資源和謀生方法的平民群體時能力有限,而傳教士“興建醫院、孤兒院、棄兒收養所、患絕癥者收容所”,從一定程度上解決了這類人口歸置、安撫的問題。類似的情況也發生在明清更迭的17世紀40年代,干旱、瘟疫、饑荒、恐懼的社會氣氛成為耶穌會士施洗、挽救靈魂的最好機會。
受歐洲傳統傳教故事敘事手法的影響,早期來華傳教士的筆下常常出現通過宗教儀式、宗教圣物給病人治療的故事。在這些故事中,病人常常是求醫困難或是在其它宗教的治療體驗失敗之后找到基督教傳教士,以治愈作為皈依條件。傳教士則通過禱告、提供圣水、贈與宗教圣物等方式引導求助者在精神上皈依,如果碰巧(故事里的多數情況如此)求助者痊愈,則是上帝賜予的奇跡。圣物、儀式的神奇作用似乎被中國的農村教徒普遍被接受。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農村廣為流行的實用主義精神,因為民間的釋、道和其它宗教中本來就有通過物品和儀式“祛病強身”的社會功能,基督教不過是增加了一種途徑而已。
三、傳教效果比較
由于資料的限制,早期皈依的中國教徒情況并沒有詳細記錄,但可以通過傳教士筆下現有數據獲得大致的印象。除了量化的皈依人數,傳教效果的評估還應考慮皈依者對基督教的貢獻。
傳教士筆下有一些中國文官朋友,然而實際皈依的、實名記錄的文官總數極少,利瑪竇傳教時期甚至只有李之藻一人被不同的傳教士記錄。然而如果考慮文官相對平民更重視基督教教義、理解力更強,且1616-1623年南京教案期間數目極少的文官教徒為傳教士提供的巨大幫助,基督教在中國文官教徒群體的傳教效果是值得肯定的。
中國平民教徒很少在傳教士的筆下以真實姓名出現,但考慮總人數,基督教在百姓群體的傳播更廣泛。據傳教士統計,1603年南昌的教徒僅有約20個,1604年增至約300個。1602年韶州的教徒近200個。然而這些數據無法證明教徒的最終保有量;甚至根據傳教故事的描述,很多教徒臨終前才皈依,對于傳教事業的貢獻僅僅是人數的增長。如果考慮到中國教徒在家族、鄰里之間的對基督教的宣傳,或許更能說明基督教在當地的影響力。
四、結語
17世紀中葉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結合中國的具體情況將傳教對象分為文官和百姓兩個群體,并根據傳教事業的發展重點和目標在不同的對象群體推行了差異化的傳教活動。從傳教效果看,在文官群體中的傳教內容稍偏離傳教主題,皈依人數也并不令人滿意,然而借由文官社會、經濟勢力的支撐,傳教事業在突發的政治事件中得到了最大限度的保護;傳教士在百姓群體以宗教治療功能為主,只是在宗教本地化的過程中,基督教與儒釋道同質化程度較高,百姓對教義的認可度低于宗教治療功能,雖然有教徒數量的增長,但還需考慮最終教徒保有量和中國教徒在家庭、社會關系網絡中的傳教作用。
參考文獻
[1] 岳長紅,柏寧.醫學史視閾下醫學與宗教的不解之緣[J].醫學與社會,2010,23(03):59-61.
[2] 肖清和.“天會”與“吾黨”: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體研究[M].北京:中華書局,2015.
[3] 柏理安.毛瑞方,譯.東方之旅:1579-1724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M].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5.
[4] 卜正民.潘瑋琳,譯.掙扎的帝國:元與明[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5] 利瑪竇.文錚,譯.耶穌會與天主教進入中國史[M].北京:商務印書館,2014.
項目基金:文章為成都中醫藥大學校基金項目“西方傳教士筆下中醫藥文化形象、變化與中醫藥國際傳播”成果,項目編號:RWQNZD1602。
作者簡介:孟悅(1988- ),漢族,成都中醫藥大學,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