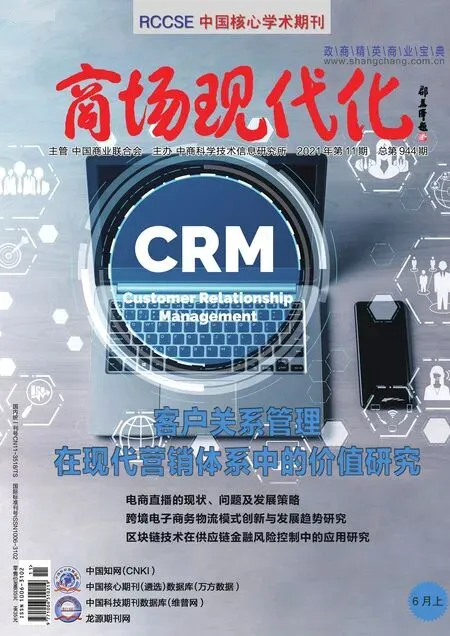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因素及潛力分析



摘 要:在對中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及特點進行闡述的基礎上,通過構建拓展的引力模型對影響中國對外貿易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利用回歸結果對貿易潛力進行測算,本文得出:與預期相同,中國及貿易伙伴國的經濟規模、人均收入水平、中國對伙伴國(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以及和中國簽訂自貿協定等因素對雙邊貿易額起著正向的拉動作用,而距離因素則起著阻礙作用;現階段,中國與美國、巴西、越南和中國臺灣地區等國家或地區的貿易往來處于“潛力再造型”階段,而與其余大多數國家處于“潛力挖掘型”或“潛力巨大型”階段,中國整體上的對外貿易前景仍十分廣闊。
關鍵詞:貿易引力模型;貿易潛力;FTA;直接
作為一國參與國際經濟活動的重要方式之一,對外貿易的發展對中國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作用。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因素及發展潛力方面的研究較多,但多集中于某一地區或某些國家,系統地、全面地對其外貿進行分析的文獻尚顯不足,基于此,本文旨在構建擴展的貿易引力模型來對影響中國外貿中的關鍵因素進行實證分析,并在此基礎上測算其對外貿易發展的潛力。
一、中國對外貿易的現狀及特點
近年來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中國的對外貿易也得到了極大的提升,貿易規模已居世界前列,2000年至2008年間中國貨物貿易總額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3%,盡管受金融危機影響,2009年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有所減緩,但2009年中國出口貿易額占據全球之最,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出口國,并且在進口貿易額中位居全球第二。在此后兩年外貿持續大幅度增長的基礎上,2013年中國躍居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進出口貿易額高達4.16萬億美元。盡管受世界市場需求低迷和國內經濟轉型等因素影響,2015年開始貨物貿易總額連續兩年出現下滑,2016年被美國以204億美元的優勢反超失去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地位,但2017年中國又以4.1萬億美元的進出口貿易額重回全球第一大貨物貿易國,并且在全球進出口中的占比由0.77%提升至10%。
盡管中國的對外貿易總額多以增長為主,但其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卻呈現出“先增后減”的趨勢,2006年中國的外貿依存度達到最高值64.24%,但隨后卻呈現出不斷降低的趨勢,2016年時中國的貨物貿易總額在GDP中的占比降至32.73%。從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來說,這一變化反映出中國經濟的增長已經從嚴重依賴于對外貿易轉向依靠國內消費和投資。
從貿易結構來講,中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結構在不斷地優化,根據Lall(2000)對產品技術含量分類進行統計可以發現,中國低技術含量制成品的比重呈現出不斷降低的趨勢,由2000年的41.21%下滑至2016年的30.92%,而中等技術含量制成品的比重不斷提升,由19.64%上升至24.53%,高技術含量的制成品比重則呈現出先上升后保持穩定的趨勢,2016年的占比為32.59%。同時,觀察進口產品的技術含量可知,中國進口的低技術含量制成品和中等技術含量制成品的比重呈現出顯著的下降走勢,分別由2000年的11.55%和30.37%下降至2016年的4.91%和22.09%,而高技術含量制成品的比重則顯示出大幅度的波動,2006年達到峰值36.59%,2011年降到谷值26.49%。
二、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因素分析
1.模型構建與樣本選擇
在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時,本文借助于學術界常用的貿易引力模型,其思想來源于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并最早由Tinbergen和Poyhonen將其運用到國際貿易領域,其對數化的一般形式為:
其中,T表示i國與j國間的雙邊貿易流量,GDPi、GDPj分別表示i國和j國的國內生產總值,Dij表示i國到j國的距離,μij表示隨機誤差項。
隨著該模型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學者們往往在上述基本引力模型的基礎上引入其他變量,以在實證所關注的因素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的同時提高該模型的解釋力,在本研究中,為了提高模型的解釋力,在此引入人均收入、投資、虛擬變量APEC和FTA等因素,最終構建的模型如下:
其中,Tcj表示中國與其伙伴國(地區)j間的雙邊貿易流量,單位為億美元,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商品統計數據庫;GDPc、GDPj分別代表中國和j國(地區)的國內生產總值,單位為以2010年不變價計算的億美元,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Dcj為北京到j國首都間的距離,單位為千米,數據來自于法國國際經濟研究所CEPII;RGDPc、RGDPj分別代表中國和j國(地區)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用來表示人均收入,單位為以2010年不變價表示的千美元,數據來源于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數據庫;FDIcj代表中國對其伙伴國(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單位為億美元,資料來源于商務部網站;虛擬變量FTA表示“是否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否記為0,是則為1,資料整理于中國自由貿易區服務網;α0表示截距項,αi表示回歸系數,μcj為隨機誤差項。
從表1中各變量的描述性統計情況來看,觀察各變量的最值可以看出,其變動幅度均不太大,最大值中最高的為lnGDPcGDPj,最小值中最低的為lnFDIcj;同時由均值和標準差可知,各序列的離散情況程度也在合理范圍內,其中離散程度最高的為FTA,最低的為lnGDPcGDPj。
在進行樣本篩選時,文章以近五年(2012年-2016年)中國與各貿易伙伴國(地區)間的進出口貿易額的累計值為標準,選取中國的前25位伙伴國(地區),包括北美洲的美國、加拿大,歐洲的德國、俄羅斯、英國、荷蘭、意大利、瑞士、法國,大洋洲的澳大利亞,南美洲的巴西,亞洲的中國香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馬來西亞、越南、新加坡、泰國、印度、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亞、阿聯酋、菲律賓,非洲的南非,這些國家與中國的貿易額在中國外貿總額中的份額達到77.06%;由于商務部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詳細數據始于2003年,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得性和平衡性,故時間上選取2003年-2016年,樣本量共計350個。
2.實證結果分析
在進行回歸分析前,為避免變量間虛假的“偽回歸”現象的出現,文章首先對各變量進行了平穩性檢驗,結果顯示各變量的水平序列均為通過檢驗,但其一階差分后均為平穩序列;且對其進行協整檢驗的結果顯示,中國與其貿易伙伴國間的雙邊貿易額與其經濟規模、人均收入、直接投資存量等變量間存在著長期均衡的協整關系。在此基礎上,本文運用EViews10.0對搜集到的面板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2。
由表2中基本引力模型和擴展引力模型的回歸結果可知,后者顯著地提高了回歸方程對觀測值的擬合優度,修正的R2由0.8025增加至0.8759,已選取的解釋變量對中國與伙伴國(地區)間的貿易流量的解釋能力能達到87.59%,只有12.41%的部分未被解釋,變量的選取較為合理,模型設定較為理想;由F統計量和其概率P值可知,方程整體上的線性關系十分顯著,但這并不意味著各變量均顯著,進一步觀察單個變量顯著性的t檢驗值和其P值可知,FTA在5%的水平上通過了顯著性檢驗,且其余變量均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通過了檢驗,各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十分顯著。
此外,觀察各變量的系數可知,與預先給定的符號相一致,距離變量對雙邊貿易往來起著負影響,距離越遠,進行貿易時的交易成本越高,對雙邊的貨物貿易起著限制作用,且中國與貿易伙伴國(地區)間的距離每增長1%,其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將縮減0.6923%;對比兩個模型中距離的系數可知,隨著其他變量的加入,距離因素對貨物貿易的阻礙作用稍微下降。中國與伙伴國(地區)的經濟規模和人均收入水平對其間的貿易額起著正向的促進作用,一國經濟規模越大、人均收入水平越高,產品的生產能力和需求能力越高,能夠推動其間的貿易往來,由α1和α2的值得出,在其他變量不變的條件下,當GDPc*GDPj、RGDPc*RGDPj增長1%時,將分別引起中國與伙伴國(地區)j間的貿易額增加0.3869%、0.1012%;中國對j國(地區)的直接投資存量與貿易額間更傾向于“相互促進”的關系而非“相互替代”的關系,投資存量每增長1%會帶動貿易額增加0.1781%;與預期符號相同,“是否與中國簽訂自貿協定”對雙邊貿易額也起著顯著的影響,中國與其簽訂自貿區的國家的貿易量是與其他國家貿易量的1.1510倍,自貿區的簽訂能夠帶來更多的優惠政策和減少貿易壁壘,勢必將促進其間貿易的發展。
三、中國對外貿易的潛力分析
對于中國與其貿易伙伴國的貿易潛力的評估,在此借用劉青書、姜書竹(2002)提出的方法,將實際貿易額與通過回歸方程得到的模擬貿易額做比較,并以0.8和1.2為分界點依次將貿易潛力劃分為“潛力巨大型”、“潛力挖掘型”和“潛力再造型”,中國的對外貿易潛力情況詳見表3。
分析表3可知,在現有的情況下,中國與美國、巴西、越南和中國臺灣地區間的貿易處于“潛力再造型”階段,這意味著其間的實際貿易額遠超過了理論貿易額,各國應注重對新的貿易促進因素的培育,以提升未來的貿易潛力。中國與泰國、德國、馬來西亞、瑞士、南非等國以及中國香港地區現處于“潛力挖掘型”階段,其間的貿易潛力還未充分兌現,需要繼續開發。除此之外,中國與其他國家間的貿易均位于“潛力巨大型”階段,這意味著中國的對外貿易尚存在巨大的潛力,未來貿易的前景還十分廣闊,但也應注意的是,實際貿易額遠低于模擬貿易額的情況也表明其間存在著嚴重的貿易壁壘,各國應盡其所能將其排除,以更好地將潛在的貿易量進行兌現。
四、結論
在對中國對外貿易現狀進行闡述的基礎上,通過借助于傳統貿易引力模型構建符合本文研究目的擴展的引力模型來對中國與其前25位貿易伙伴國間貿易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本文得出:經濟規模、人均收入水平、直接投資和簽訂自貿協定等因素與理論預期相同,對中國對外貿易起著積極的帶動作用;而距離因素也與引力模型理論一致,更多地表現為對雙邊貿易流量的阻礙作用。在此基礎上,通過引力模型回歸結果來計算模擬貿易額并將其與實際貿易額進行比較得出,除個別國家外,中國與大多數貿易伙伴間的貿易處于“貿易挖掘型”或“貿易巨大型”狀態,中國對外貿易的潛力尚未得到應盡的開發程度,貿易前景十分廣闊。中國與各國應對其間的貿易往來持積極態度,僅各國所能排除存在的貿易壁壘,以推動中國與各國貿易的大幅度提升。
參考文獻:
[1]段小梅,周瑩.基于產品技術含量分類的兩岸貿易關系研究[J].臺灣研究集刊,2017(03):62-71.
[2]李俊久,丘儉裕.中國對APEC成員的出口潛力及其影響因素研究——基于貿易引力模型的實證檢驗[J].亞太經濟,2017(06):5-13.
[3]孫敬水,馬淑琴.計量經濟學(第2版)[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2,310-312.
[4]黃英婉.“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投資便利化問題研究[D].遼寧大學,2017.
[5]吳昊,陳志恒,王皓,廉曉梅,佟新華.“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筆談[J].東北亞論壇,2018,27(03):3-23+127.
[6]陳繼勇,陳大波.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出口商品貿易潛力的實證研究[J].湖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45(01):109-117+168.
[7]中國重新成為世界第一貿易大國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94091142394937963&wfr=spider&for=pc.
作者簡介:苗澤遠(1989.06- ),籍貫:山西省潞城市,學歷:碩士,研究方向:日本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