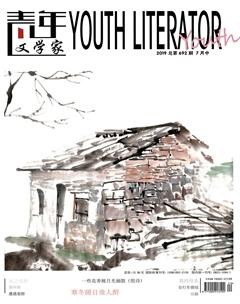殘夢中的破碎山河
石橋楓
摘? 要:格非是一位真正不斷超越自我的先鋒作家,從構建博爾赫斯式的迷幻花園到傳承本土小說傳統,他賦予了筆下小說傳統的美感和民族靈魂。格非在堅持知識分子的理性立場同時,兼有文人的感性情懷,《山河入夢》便用迷蒙的意境和感傷的情調為我們刻畫了一幅中國式的夢。
關鍵詞:意象;古典;紅樓夢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02
如果說早期的格非是一位以學習西方、專注于“怎么寫”的敘事游戲的作家,那么他的江南三部曲就已然轉向了以中國傳統式的美感和神韻表現現實社會的精神困境。《山河入夢》是其中之一,這部小說用迷蒙的意境和感傷的情調塑造出了一個中國式的夢,而這一夢境又不斷被現實消解,夢中山河也由此破碎。格非在本書中運用了許多典型意象,以歷史為背景營造出古典的氛圍,且繼承了《紅樓夢》的寫作技巧和表達,顯得敘事緊密、語言平實質樸。
一、典型意象
格非在書中塑造了“紫云英”、“夢”這兩個典型意象。“紫云英”是核心,在整個故事的走向和主題的闡釋上都發揮著重要作用。格非談寫作經歷時曾說,“寫《山河入夢》時,我想到了陽光下無邊無際的紫云英花地……”[1]紫云英為二年生草本植物,生命力頑強。在文本更深一層的意義中,女主人公姚佩佩便是紫云英的象征,她稱自己為“被浮云的陰影遮住的苦楝樹下的紫云英”[2]。她幼時父母遭難,眾親戚一口咬定是她的“佩菊”一名引起的禍端,由此她不僅要時時刻刻掩蓋住自己的過往,還要遭受寄人籬下的苦楚。男主人公譚功達在梅城浴室發現了姚佩佩,進而把她調入縣政府工作。他如父親般的關愛讓女孩心里產生了報恩的柔情,并將他視為能夠驅散紫云英花地陰影的陽光。但女主人公的心思因譚功達被撤職檢查而無情打斷,譚功達更是在悔恨和消沉中娶了張金芳,錯過了姚佩佩的邀約。同時,姚佩佩經常用紫云英花地的陰影來給自己占卜算命,“我或許生下來就是有罪的呢!……”[3]她似乎從一開始就從紫云英的陰影里窺見了自己的宿命,她在現實中不斷的追求陽光、對宿命做出的掙扎和反抗都是無用的:從界牌逃到蓮塘,再到普濟,她只是走了一個圓圈,最終回到梅城被槍決。其次,“夢”這一意象在小說中的運用同樣典型。開篇第一章,姚佩佩說她夢見閻王爺在清明節派鬼去抓她,為首的小鬼和剛才截車的人長得一模一樣。譚功達哈哈大笑,“你又沒犯什么罪,人家抓你做什么?”但姚佩佩卻反問道,“你怎么知道我沒有犯罪?”這個夢在小說的開頭看起來很荒誕,甚至有誤導讀者思路的趨勢,但文至結尾就有恍然大悟之感,姚佩佩的命運確實和開頭的夢境一樣,犯了殺人罪四處逃亡,而車被截的地點界牌,就是她逃亡途中最重要的一環。
格非用這兩個超現實空間的敘事與現實空間進行對比,昭示出了人物的宿命和反抗的無力感。此時的意象是一種理智與感情的復雜體驗,被作者攫取和加工后成為展開故事敘述的起點,也成為了讀者循跡解讀文本的鑰匙。
二、歷史背景下對古典資源的運用
格非筆下所運用的歷史背景有意地回避了“正史”,他更喜歡加入自身對歷史的感悟和理解,在民間傳統和個人體驗等方面挖掘歷史的“真相”。《山河入夢》的故事發生在新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初期,但作者并沒有重點描繪歷史事件或者重現歷史走向,而僅僅把歷史當做背景,描繪個體的命運和個人在劇變的時代中對烏托邦的追求和沉淪。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都表現出《紅樓夢》對其的影響,而在《山河入夢》一書中尤為明顯。首先,對《紅樓夢》中敘事技巧的借鑒。格非將追求烏托邦這一主題貫穿整個文本,“如果完全沒有烏托邦的東西,沒有一個人對未來社會對自己的命運沒有任何想象性的東西,那就非常可怕”[4]。又運用《紅樓夢》的家族敘事,通過一個家族中第二代人的日常瑣碎之事及其社會關系網,來展示當時的社會圖景和不同道路的探索。主人公譚功達是梅城一位擁有烏托邦夢想的縣長,他隨農業代表團去過外國之后,便不顧連年饑荒和縣財政入不敷出的情況大力修水庫、漠視百姓基本需求轉而建起了公園、在水庫被沖垮時仍惦念著無用的沼氣池。此外格非在敘事中還效仿了《紅樓夢》圓形的敘事結構,以同一件事開頭并以其做結尾,并用視角的不斷變化來豐富敘事技巧。小說故事是從姚佩佩跟從譚功達到普濟水庫視察開始的,譚功達的膝蓋上放著一張手繪的梅城縣行政區域規劃圖,他還不時用一支紅鉛筆圈圈點點。而在文本的最后,姚佩佩留下的信件中再次提到這件事,原來地圖邊緣的空白處,譚功達用紅鉛筆密密麻麻地寫滿了她的名字。看似是主人公無意寄出的信,其實是作者有意而為之的筆法,使得文本首尾呼應,故事更為完整。第二,對《紅樓夢》中悲劇意識的承襲。《紅樓夢》寫了一個大家族由盛而衰的悲劇故事,而在格非的小說中,悲劇正是他所展現的一個重要方面。千百年來人類的斗爭都是為贏得一個安定的生存環境,夢想都是能夠創建一個和諧社會,所以人類社會上很早就出現了像“桃花源”、“天下大同”等烏托邦情結。在《山河入夢》中,譚功達一直是在為建立理想社會而努力,甚至呈現了各種構筑版本,但均以失敗告終,正如他自己所說,“你只要想去做這個桃花源,可能就會有問題。用阿多諾的話來說,產生了強制、暴力和集權。”[5]他個人不滿于日益庸俗化和利益化的現實境遇,想要去構筑一個烏托邦理想社會,他不惜因此耗盡才華拋棄榮譽,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他最終發現,不僅這個構筑糾集著太多的矛盾、同樣充滿了遺憾和罪惡:花家舍的人與人之間冷漠,沒有隱私,小韶的哥哥因輸掉一場籃球賽受到各方面壓力而發瘋……他絕望的發現,理想社會的追尋和構建并不是個人所能完成的,人類自私與貪婪的本性讓一切都變成了空想。第三,對《紅樓夢》中“寶黛型”癡男怨女式愛情觀的繼承。譚功達和姚佩佩相見一開始就帶有“這個妹妹我曾見過”的情調,“她那尖尖的指甲從譚功達手背上劃過,印痕卻留在了他心里。”[6]譚功達本身就帶有寶玉的癡,他身為一縣之長卻不懂官場,他心地善良、天性爛漫,看到漂亮女孩子會發愣,湯碧云甚至說他是“花癡”病,格非筆下的譚功達便是建設年代的賈寶玉。姚佩佩的美和凄苦和黛玉一樣讓人心碎,她和黛玉一般原本家境優渥而后雙親皆亡,生活的變故讓她們變得對人世小心翼翼。同時,姚佩佩和黛玉的愛也如出一轍。她的愛情十分含蓄,眼看著譚功達與白小嫻相親又無可奈何,只能偷偷在她照片上用胸針扎一個洞,得知譚功達給自己在集市上買了泥娃娃十分開心卻又擔心他會把壞掉的送給自己,她在逃亡的路上依舊把譚功達當做自己最信任的人,她的愛真摯深沉,凄美動人。
格非在《山河入夢》中可以說是直接地向《紅樓夢》進行了靠近,恰如書中姚佩佩的一席話,“再好的大觀園,也會變成一片瓦礫,被大雪覆蓋白茫茫一片。”他對古典資源和氛圍進行了開拓性運用和塑造,用細膩的敘事、典雅的語言和循環如春秋的內在結構為讀者展現了一場別開生面的文學盛宴。
縱觀格非在《山河入夢》一書中所運用的手法、塑造的人物,不難看出他已經在利用傳統的古典資源,在典雅細膩的書寫中關注著中國一代又一代人對烏托邦的“追夢史”。他筆下的女性人物豐滿動人,雖然《山河入夢》中繼承烏托邦主題的是男性,但女性在小說中占據了絕大的篇幅和重量。格非“男性視角”下的女性書寫大致在書中分為三類——以姚佩佩和白小嫻為代表的反抗者、以湯碧云為代表的權色制度下的犧牲者和以馮寡婦為代表的歷史的凋零者。這三類女性形象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環境,她們或悲涼或恍惚的身世都匯聚著格非對人類命運的反思。“就小說而言,寫作應是一種發現,一種勘探,更應是一種諦聽。”[7]山河入夢,夢的是理想的山河,讓理想山河破碎的是鐵錚錚的現實。山河入夢,破碎山河里帶著一代又一代知識分子的理想之夢,對破碎山河的理想夢堅持繼承下來的是知識分子的信念和向往。
注釋:
[1]格非:《最有意思的是在心里生長》,《長篇小說選刊》2007年第2期.
[2]格非:《山河入夢》,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10頁.
[3]同上,第184頁.
[4]《格非:不能把歷史當作晾在那兒的風景》,中國青年報2007年1月.
[5]《格非:總有一群柔弱的人在支撐著昂貴的理想》,《野草》2006年第6期.
[6]格非:《山河入夢》,上海文藝出版社2015年版,第14頁.
[7]格非:《小說藝術面面觀》,江蘇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