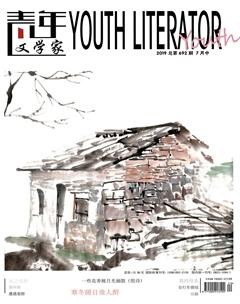淺析林紓之翻譯選材
摘? 要:林紓的翻譯在晚清翻譯運動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地位。無論是林譯的數量還是其影響力都堪稱晚清翻譯史上的奇跡。對林紓翻譯的研究多集中在其翻譯策略或翻譯手段的選擇,其實林紓對翻譯作品體裁的選擇也是全面研究晚清翻譯運動不可缺少的內容。林紓對小說這一體裁的執著受制于內外動力的驅使,這樣的選擇雖然局限了當時國民對西方文學的全面解讀,但卻使得其順利進入晚清讀者視野,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晚清翻譯運動的興起。
關鍵詞:林紓;翻譯選材;內外合力
作者簡介:范榮(1976-),女,漢族,重慶市人,重慶郵電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研究生碩士,主要研究方向:翻譯與文化、語言學。
[中圖分類號]:H0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2
1.引言
作為晚清小說翻譯運動中杰出的翻譯家代表,林紓以其巨大的譯本數量及廣泛的譯作影響堪稱第一人。據統計,晚清純文學作品的譯本大約為300-400種左右,而林紓的作品即使以最保守的計算也有180種之多。基于林紓對晚清翻譯運動的杰出貢獻,后世學者對其譯作研究頗多。然而,學者們大多關注其“歸化”的翻譯策略及“刪、減、改”的翻譯手段,而鮮有討論在翻譯過程中林紓為何對小說這一文學體裁執著的選擇和偏愛。眾所周知,林紓的翻譯發生在晚晴這一“翻譯之社會功能高于文學功能”的特殊時期,因此,探討林紓及當時整個晚晴譯界何以將“開啟民智”這一重任施以小說——這一從問世以來就一直備受中國史家輕視的文學體裁是完善對林譯小說甚至整個晚清翻譯運動研究的有益嘗試。
2.林紓之翻譯選材
1897年是林紓人生歷史上最值得紀念的一年,這位完全不識外文的落第舉人與魏翰、陳家麟等曾經留學海外的才子開始合作翻譯了域外小說,而且憑借引起巨大社會反響、造成“洛陽一時紙貴”的《巴黎茶花女遺事》譯本讓自己奇跡般地走上了自己輝煌且短暫的翻譯生涯。
林紓一生譯作豐碩,在經過歷代學者鍥而不舍的努力考證下,我們對其翻譯作品的數量及類型做出了基本清楚的統計。1982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紓的翻譯》里著錄了林譯作品184種;1982年第六期的《讀書》連燕堂撰寫了《林譯小說有多少種》將其翻譯作品數目更正為183種;1991年商務印書館重印《林紓的翻譯》,其中馬泰來先生在所編的《林紓翻譯作品全目》中指出:林紓譯作多達179種,涉及11個國家的98位作者⑴ 77;在2007年出版的《林紓評傳》里張俊才教授對林紓的譯作進行了詳盡的統計:林譯作品一共246種,其中已發表出版的有222種,未刊作品24種。就其涉及的國家和作者而言,英國:作品106種,作家62名;法國:作品29種,作家20名;美國:作品26種,作家15名,其他的還涉及俄國、德國、日本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品及作家。⑴ 292-293在對林紓譯作進行統計研究的過程中,除了驚嘆其譯作數量巨大之外,本文也發現了林紓先生的在選材上的極為明顯的偏好:林紓所譯的絕大多數作品的類型都是小說。在馬泰來統計的林譯中,除了十余種分別屬于歷史、學術、傳記、戲劇、故事、寓言或筆記,其余均屬小說。⑴ 78本文對張俊才教授所編錄的林紓翻譯目錄也進行了較為詳盡統計,在目錄所列的246種林譯作品里只有58篇外媒對當時中國時政的評論,其余的188種林譯均為小說。1924年林紓去世之后,鄭振鐸曾寫文紀念并盛贊林譯作品中有四十種左右屬于世界小說名著。由此可見,林紓在翻譯選材過程中對小說的偏愛是明顯的,而探究林紓之小說選擇不僅有助于全面剖析林紓的翻譯行為,而且對解讀晚晴整個翻譯運動都有著深刻的意義。
3.小說選擇之內外合力
眾所周知,林紓不識英文。故從翻譯的第一本小說開始,合譯者就開始幫助林紓挑選翻譯原著,合譯者對林紓選材的引導自是不可忽視的。然,在林紓一舉成名之后,其對小說選擇的堅持就絕非再是對合譯者的惟命是從。林紓對小說的執著其實受制于個人內在的文學情結及當時翻譯行為被刻意賦予“教化”“啟迪”之社會功能的外力的共同作用。在這樣內外合力的牽引下,小說在林紓翻譯選材中才會獨領風騷。為了更為詳盡的闡述林紓對小說格外青睞的緣由,本文嘗試從其本人內因及社會施加之外力分別加以探討。
3.1 內在的文學情結
從大量有關林紓生平的文字記錄來看,林紓對文學、對小說的情結無疑是與其從小接受中國傳統教育的熏陶訓練息息相關。林紓出身寒門,童年少年時代嘗盡人生的艱辛困苦,然而,在“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及父輩書香之氣的熏陶下,林紓從懂事之際就非常喜愛讀書。林紓自稱五歲開始讀書,因其家境貧寒,林紓的讀書生涯竟是從書塾窗外偷聽開始的。年少的林紓把讀書看得與生命一樣重要,而且特別的勤奮刻苦。他曾經對自己的孩子們這樣說過,“……時吾攻讀甚勤,嘗畫于壁。而挈其蓋,立人于棺前,署曰:‘讀書則生,不則入棺。” ⑴ 10林紓尤癡中國傳統文學之經典小說,曾用餅餌之錢買殘破《漢書》讀之,因幸得《小倉山房尺牘》而大喜,加之其啟蒙老師薛則柯老先生的諄諄教誨,林紓對中國傳統文學的愛好自是深入骨髓,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可見,熱愛中國傳統文學的種子在孩童時代就深深植入林紓的內心深處,這顆種子深埋于此,默默積累著力量,渴望有朝一日出土發芽長成大樹;因此當林紓無意卻有幸地投入晚清翻譯運動這場具有時代意義的外來文化文學宏潮之際,這顆熱愛文學、癡迷小說的種子終于乘風起勢,長成參天大樹,以不可抗拒之勢推動林紓以近乎偏執的熱情選擇小說作為其翻譯的唯一體裁。
3.2 外在的社會助力
林紓內在的文學情結自然是其選擇外來小說翻譯的原始動力,而促使他堅定不移地走下去則是外在的社會助力——晚清翻譯運動的宗旨。
梳理中國傳統文學的發展史,小說一直以來就是難登文學“大雅之堂”的“末技”“小道”之存在。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提到,“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途說之所造也。”既是“街談巷語”,“道聽途說”,自不能與詩歌、騷賦、古文比肩;然,雖地位低下,小說卻因其內容淺顯易懂,雅俗共賞深受廣大民眾的喜愛,正如康有為所言,小說“道于俚俗,故天下讀小說者最多”,故可成為維護王權統治及道德勸懲的絕佳工具。
然而國人喜好閱讀小說的傳統又為何與晚清翻譯運動的宗旨聯系在一起呢?我們需要剖析一下晚清翻譯運動發起的緣由。晚清翻譯運動發生在晚晴社會及國民迫切渴望學習西方的時期,翻譯西方小說已是醫治國難之工具。1902年梁啟超就小說之社會變革的重大意義發表如下宣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人格;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 ⑵22這種明顯提升小說社會功能的言論卻在當時成為晚清譯者們投身譯界的最強動力。1901年林紓在《譯林》第一冊序中也道:“吾謂欲開民智,必立學堂,學堂功緩,不如立會演說;演說又不易舉,終之唯有譯書。” ⑵25林紓曾一度非常熱衷翻譯偵探小說,在《神樞鬼藏錄》的譯序中林紓指出,“中國無律師,但有訟師;無包探,但有隸役。訟師如蠅,隸役如狼。蠅之所經,良肉亦敗;狼之所過,家畜無免!……果使此書風行,俾朝之司刑讞者,知變計而用律師包探,且廣立學堂,以毓律師包探之材……則小說之功,寧不偉哉!”⑴ 91在林紓心目中,小說的社會功能既然已經提升到學習西方維新改良、開啟民智的高度,那么選擇小說翻譯自是順理成章。
4.林紓小說選擇之得失
林紓對小說翻譯的堅持自是有得有失。首先,堅持選擇小說而非其他文學體裁作為翻譯對象使得西方文學首次進入國人視野時沒有遭到強烈的排斥。而且隨著晚清翻譯運動的如火如荼,不僅是普通民眾被激發出高昂的西方文學作品追捧熱,就連之后在五四運動中強烈抨擊林譯小說有著種種弊病的著名譯家們也承認曾受到西方文學魅力的深遠影響。后世的文學大師魯迅兄弟、錢鐘書及冰心都公開承認林譯作品為自己打開了欣賞了解西方文學的大門。“接觸了林譯,我才知道西洋小說會那么迷人。”“閱讀林譯小說而知道許多外國的人情世故”。⑶303其次,林紓在翻譯西方小說的過程中開啟了中西文學比較的里程,他將司各特的作品與司馬遷的《史記》相比:“……紓不通西文,然每聽述者敘傳中事,往往于伏線、接筍、變調、過脈處,大類吾古文家言。”⑷1-2“左氏之文,在重復中,能不自復;馬氏之文,在鴻篇巨制中,往往潛用抽換埋伏之筆而人不覺。迭更氏亦然。”“西人文體,何乃甚類我史遷也!”⑶289林紓進而還驚喜地發現了中西文學在價值內涵及寫作技巧方面的相似性,“今我同志數君子,偶舉西土之文字示余,余雖不審西文,然日聞其口譯,亦能區別其文章之流派,如辨家人之足音。其間高厲者,清虛者,綿婉者,雄偉者,悲梗者,淫冶者,要皆歸本于性之正,彰癉之嚴,此萬世之公理,中外不能僭越。”⑶286對于狄更斯小說的文學藝術西方魅力,林紓也是不吝贊美:“言哀則讀者哀,言喜則讀者喜,至令譯者啼笑皆非,竟為著者作傀儡之絲矣。”⑸2“左、馬、班、韓能寫妝容不能描蠢狀,迭更司蓋于此四子外,別開生面矣。”⑶289承認西方作家寫作技巧在某些方面比國人高明,這反映出了林紓在翻譯西方小說的過程中已經嘗試超越自身文化文學局限,開始對西方文學有了前所未有的新視野。
當然,林紓執意選擇西方小說為翻譯對象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局限了晚清國民對西方文學全方位的鑒賞,而且為關照也晚清國民對小說的傳統審美情趣所采取的“大刀闊斧”增減改譯一直深受后人詬病。這即便是在錢鐘書老先生深入調查研究后指出,林紓的增減改譯并不完全是語言水平低無法理解原文,而是“他在翻譯時,碰到他心目中認為是原作的弱筆或敗筆,不免手癢難熬,搶過作者的筆代他去寫”,這樣更能悟到“天下文人之腦力,雖歐亞之隔,亦未有不同者”。然而,無論功過得失,我們都無法否定林紓對晚清翻譯運動所做出的杰出成就,林紓之獨特的翻譯選材也是我們全面研究晚清翻譯運動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張俊才.林紓評傳[M].北京:中華書局,2007.
[2]楊聯芬.晚清至五四:中國文學現代性的發生[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郭延禮.中國近代翻譯文學概論[M].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
[4]林紓.《撒克遜劫后英雄略》[A].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5]林紓.《塊肉余生述.續編識》[A].北京:商務印書館,19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