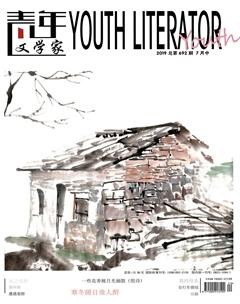試論李漁的情欲觀與道德觀的沖突與結合
摘? 要:在中國傳統思想中,“情欲”一直都被置于“理志”的對立面看待,即所謂“重理而輕情”。然而在晚明世俗生活的潮流和心學的雙重影響下,個性化的情欲的地位被不斷抬高。表現在李漁的劇作中時,其作品無疑帶有明顯的對于情欲的贊揚之情,但是往往又有實在的教化之意圖,將二元對立的觀念有機地統一成為作家必須考察的內容。本文試以《比目魚》為例,探討李漁廣義的情欲與理志的沖突,并在框架內進一步細化狹義情欲中情與欲之分別,探討兩種觀念在劇作中的結合,并最終解釋李漁結合失敗之原因。
關鍵詞:李漁;《比目魚》;情理之辨;情欲之辨;情理結合
作者簡介:任春昊(1998.4-),男,山東青島人,山西大學本科。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02
一、李漁的情欲觀與道德觀的沖突
當程朱理學被作為官方哲學,并逐漸融入百姓日常生活后,情欲與理志的對立關系無疑被放大化了。盡管“存天理,滅(去)人欲”所滅之欲是不合道德的欲,人正當的欲望尤其是正常的夫妻人倫是被肯定的。
但由于語義和執行所產生的偏差,理學最終成為了束縛人自由和加強統治的工具,因此理學之反動也在逐步醞釀。這種反動,在李漁的個人生活和作品創作中被表現得非常明顯,且尤以情感線索曲折、多層的作品為突出,接下來就將以其劇作《比目魚》為例進行論述。
1.情欲與理志之辨
李漁無疑是非常推崇個性化的情欲的,他提倡“不求工而求至美”,并繼承了公安派對“自然”、“性靈”主張的推崇。表現在《比目魚》中,譚楚玉對劉藐姑之一見傾心是如此,而劉藐姑之內心表露更是明了十分:“今日此來,一定是為我。(嘆介)檀郎,檀郎!你但知香脆之可親,不覺娼優之為戲;欲得同堂以肆業,甘為花面而不辭。這等看來,竟是從古及今,第一個情種了。我如何辜負得你?”[1]一段獨白,大膽直白地表達了對楚玉的愛慕之情,而這僅位于將將開始的橋段,速度之快,情感之濃烈,令人驚嘆。
而更加使得一片癡情升華至一境界的,是譚劉身份之別和楚玉“委身”戲班之中兩點。一為士子,一為倡優,即便楚玉是落魄書生,二人地位身份之差異也是天壤間的。同樣,士子贖佳人身常有,而自降格于戲班中卻是不常有的,乃是實在的離經叛道之舉。然而在“至情”觀念之下,藐姑為追求愛情之執,不顧身格,楚玉為追求愛情之癡,自降身格,反而都是最高最純的格,這種“貴與賤”拉開的分別,反而使這份愛情更加具有張力,更加活潑潑,更加具有崇高感。
而這種不同于傳統的表達,其內在邏輯和現實依據是什么呢?在將李漁的作品、生平和其所處時代聯系起來以后,得出以下兩方面的結論:社會結構上的重組以及作為社會思潮的心學的廣泛傳播,對李漁產生了重要影響。這既構成了李漁情欲理念的依據,同時也一定程度說明了沖突的根源。
首先談及社會結構的變化。明中葉尤其是嘉靖以后,隨著商業的蓬勃發展,過往對于士人和商賈的地位的劃分出現了新的取向,財力雄厚的商人的社會地位提升,例如文中的錢萬貫,只一位鄉紳而已,卻使官民同敬同懼。而傳統的士人也由于財富而劃分成兩個層次,過往的同一性被打破了。李漁恰恰處于士人的中下層(從某種意義上譚楚玉正是李漁的化身),他有才學有抱負,可既沒有中舉獲得官職,也沒有較豐厚的財產。他面前的道路要么是繼續科舉,但明清鼎革是他內心無法逾越的障礙;要么就成為平民,但才情又使他不甘于平凡的生活。李漁先選擇了隱居三年,而后待時局稍穩出山,并最終選擇了戲劇這條折中的道路。
再談心學之社會思潮。心學可以說是古代中國繼程朱理學后最為重要的社會思潮。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動,士人發現原有的知識越來越無法解釋急劇變化的社會,這造成了崇高救世的理想和實學思想不可避免地產生了矛盾。王陽明提出的“心即理”極大地解放了人的思想,極強的個性化表達開始盛行。泰州學派更加激進,意為“欲即理”,更加強化了對于物欲的追求,既然“滿街皆圣人”、“即心即佛”,那么外在的倫理道德準則就失去了意義。
然而,在新的變動和思潮的影響下,傳統的社會形態和思想卻并未退潮,傳統的士人精神和新的士人精神、傳統的審美趣味和新的審美趣味發生了激烈碰撞,在這樣的矛盾之中,李漁不可能超越矛盾自身。李漁在其文論中這樣描述:“然卜其可傳與否,則在三事,曰情、曰文、曰有裨風教……情具文備而不軌于正道,無益乎勸懲,亦終不傳。”[2]因此在《比目魚》“至情”之表達過后,又不可避免地帶有著“節婦義夫”的說教意味,即所謂“維風化,救綱常”,從而最終走向了道德倫理化的結局。同樣的,多數劇目中的男主人公但得機會必然科考的情節在本劇中仍然上演,而本被作為楚玉至情至性表現的入梨園行之舉動,也最終因為楚玉高中后因顧及臉面屏退左右而黯然失色。某種意義上,楚玉復生后的科舉之路,恰恰是李漁意圖走而未走的一條路。最后,對劉絳仙的復認,又解決了父母倫常這個大問題,原初的反叛性也最終圓滿消弭。我們不能脫離李漁的時代環境和個人經歷憑空評判,但從觀賞者的角度上來講,這種格上的前后落差,無疑極大影響了本劇的藝術層次。
2.情理之辨下的情、欲之辨
在上一部分的描述中,情欲被作為一個廣義的概念進行表述,而在這個框架下,李漁實際又對狹義的情和欲兩個概念進行了區分。李漁將心靈上的愛情之“情”和身體中的肉欲之“欲”區分開來,而就其文中的觀點,他是褒揚情而貶抑欲的,如杜麗娘一般因著癡情可使死生變幻的至情,是狹義的情欲概念中最真摯的部分。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待《比目魚》中對于準性愛和性愛的描寫,雖然有兩人的愛情基礎,但卻并不完全是現代意義中以愛情為基礎的性愛,有學者認為《比目魚》是李漁情欲結合的典型作品,[3]筆者對此持保留態度。
筆者認為文中情與欲是割裂而不是完全的情欲的結合的原因有以下幾個:其一,二人的準性愛和性愛(除水府一場外),發生場合和動因往往是享樂和壓抑下的親近,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對男女之事的好奇,而非至情所導致的行為;其二,尤以水府一場門外二仆之性愛為例,其場面描寫無論從何種角度看都是為了迎合觀眾的欣賞趣味而并非為體現至情至性的。
楚玉和藐姑有著忠貞的愛情,也有著激烈熾熱的性愛,但并不意味著這兩者具有必然的因果聯系,同時再結合創作的時代性,作者筆下的情、欲,性、愛,只是一種并不牢固的結合,不可避免地產生著誰為主的矛盾。
二、李漁的情欲觀與道德觀的結合
李漁在《閑情偶寄》中有這樣的表述:“‘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4]而同時期的黃周星則更為直截了當:“制曲之訣,雖盡于‘雅俗共賞四字,仍可以一字括之,曰‘趣。”[5]正如前文所述,李漁處在士、民,雅、俗之矛盾中最終選擇了一條折中的道路,因此即便他怎樣強調“一夫不笑是吾憂”,士人的精神卻也是他不可忽略的隱性精神,這種精神是一定要表現在其作品中的,可以說,“機趣”的理論,就是其結合的觀念和依據。
這種“機趣”,在受眾的層面,體現為士人和市井的結合;在主旨的層面,體現為情欲與道德的結合,但是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這種結合最終都失敗了。
在《比目魚》中,楚玉和藐姑的愛情鮮明地體現了“至情”的觀念,這個觀念恰恰是雅俗結合的最好體現,然而這種觀念在劇情發展之后發生了斷裂。一方面走向了大量對性愛、男女關系的庸俗化的描寫,這除了是為了迎合觀眾口味,同樣也是李漁自身私生活的一個寫照。李漁通俗的描寫,讓人甚至懷疑楚玉入戲班的動機究竟是因為癡情還是淫樂,這對本劇的愛情的基礎都產生了動搖。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對至情至性的描寫,最終又轉移到生硬倫理和教化上。這種至情向上之為道德和向下之為庸俗的取向,也正如李漁身份地位、思想與行為一樣充滿著矛盾。
這種矛盾正是李漁戲劇作品試圖將情欲和道德結合而不得的真正原因。首先,由于時代的局限,李漁無法對性愛與愛情有機結合,即一種“天人合一”的境界,仍然將其作為矛盾雙方二元對立起來,其試圖進行的結合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結合,而是在對立的情況下的調和,即前文提到的何者更加重要的問題。其次,由于李漁并不是奉行知行合一的人,因此在其創作中,就必然存在著知和行的矛盾,一方面給人以肉欲的體驗,另一方面給人以教化的旨意,這兩者都不同程度地沖淡了作者提倡的情的抒發。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即便個性解放、心學思潮在社會盛行,我們也必須看到這種盛行的相對性,因為從始至終的主流思潮都是理學的理志,李漁不是一個具有徹底的突破性的作家,在這個框架下,他做的只是一種調和——在理志之下提升情欲的地位。在理解了這個最終的因素后再來回看李漁的《比目魚》,很多原先不能理解的地方,應該得到了相對完善的解答。
三、結語
情理合一的傳統意識,是明清才子佳人戲曲小說普遍的審美趣味,李漁與他的《比目魚》正是這種審美趣味的典型代表。然而,由于他對于審美藝術功利價值的體認,以及整個社會的主流價值并未有根本性的改變,決定了其作品旨趣的悖謬和分裂。這也必然導致一個結果,對李漁的研究,終會使得文學研究轉向社會研究。
注釋:
[1]李漁:《比目魚·笠翁傳奇十種(下)》,《李漁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27-128頁。
[2]胡經之:《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661頁。
[3]鐘明奇:《李漁情愛心理的文化哲學探析》,長沙:中國文學研究,2000年02期。
[4]胡經之:《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695頁。
[5]胡經之:《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第695頁。
參考文獻:
[1]李漁:《比目魚·笠翁傳奇十種(下)》,《李漁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
[2]胡經之:《中國古典美學叢編》,南京:鳳凰出版社,2010年。
[3]鐘明奇:《李漁情愛心理的文化哲學探析》,長沙:中國文學研究,2000年02期。
[4]浦部依子:《李漁戲曲〈比目魚〉中劉藐姑的主導性──對于中國古典戲曲中的兩性關系的一些考察》,上海: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1年05期。
[5]余英時:《士與中國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