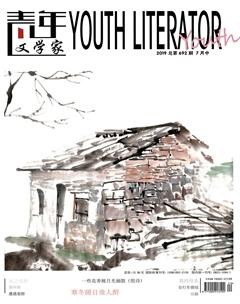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得其自”與“吾喪我”:追溯自我生命的歷程
摘? 要:《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是當前沈從文傳記的最新作品。在內容上,作者對“自傳事實”、“歷史事實”與“傳記事實”的展現構成一個完整的體系,力圖呈現傳主沈從文的文學生涯與文學個性,彰顯了作者的學術思想。在形式上,該傳記以時間為線索,呈現出簡潔明了的寫作風格。通過作者對傳記材料的安排與呈現,給讀者們逐漸呈現出一個鮮明的傳主形象,也體現了作者的學者姿態。
關鍵詞:傳記;沈從文;前半生;得其自;吾喪我
作者簡介:楊晨馨(1994-),女,江蘇鎮江人,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02
如何運用相應的史料來再現傳主的一生,或者說,通過傳記的寫作向讀者傳達什么樣信息,一直是傳記寫作的核心問題。傳記本身建構出以傳主為中心的歷史,向讀者展現出傳記家的某些眼光與觀念。有的西方傳記研究者強調發掘傳記文學的文體潛能,規避數量龐大的史料證據,創造一種以傳主為中心的“敘事”文風,在非虛構寫作的立場上追求傳記文學的修辭效果。①在2018年所出版的傳記中,復旦大學張新穎教授的《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成為他多年研究沈從文的一本總結性文稿,也是他沈從文研究的階段性成果與現階段沈從文傳記的最新作品。作為一名學者,該傳記通過呈現傳主沈從文的文學生涯彰顯了作者的學術思想,尤其在傳記材料的安排上,從“自傳事實”、“歷史事實”與“傳記事實”三方面呈現了傳主“得其自”與“吾喪我”文學創作上的生命歷程,并體現出作者客觀嚴謹的寫作態度。
傳記本身自成體系、有據可尋,這使得傳記寫作介于學術寫作與虛構寫作之間。學者趙白生注重傳記材料的運用,將傳記文學的重點要素歸為“傳記事實”、“自傳事實”與“歷史事實”,并指出該三要素聯系緊密,呈現出“互文”關系,并構成以“傳記事實”為核心的三維體系。其中,“傳記事實”指的是“傳記里對傳主的個性起界定作用的那些事實”;“自傳事實”并非作者自述的事實,即“不純粹是事實,也不純粹是經驗,而是經驗化的事實”;“歷史事實”的定義則比較復雜,作者引述前人“實證”、“主體”、“辯證”的三種觀點,而作者自己對歷史事實的理解則是“不在史,而在傳”。
《沈從文的前半生:1902-1948》一書的寫作方法并不復雜,傳記材料的排列與呈現的方式似乎也頗為簡單,即通過寫明各種事件發生的時間與地點,幫讀者們畫了一個以時間為橫軸、以空間為縱軸的坐標系,摒棄了傳記的多種文學手法,呈現出簡潔明了、樸素無華的寫作風格。隨著傳記“時間”的推移,傳主沈從文的形象逐漸在讀者的腦海中漸漸清晰起來——作者仿佛要通過一種畫卷般的手法一寸一寸地打開傳主的一生。在這一過程中,作者不僅呈現了自己的學術觀點,還使得讀者不斷有新的發現與體會。上文已經論述到,傳主沈從文的文學創作世界是不斷探尋生命本質的,其寫作的過程也是他追溯生命的過程。這一過程被作者張新穎以“時間”的線索呈現出來,讓讀者追逐傳主的生命歷程、把握他的文學創作,增強了讀者閱讀過程中的“在場感”。這種傳記的寫作方式似乎比較傳統,對傳記材料既不重新排列也不重新拼接,這毋寧說是作者的寫作意圖:追溯生命的歷程比得出傳主文學創作特征的結論更為重要②。
通過上兩節的論述來看,作者呈現“傳記事實”的方式的確借助于呈現傳主文學創作生涯這一過程。在“自傳事實”中,作者主要呈現了傳主“棄武從文”的轉折過程;在“歷史事實”中,主要呈現了傳主“棄文從史”的轉折過程;在“傳記事實”中,作者則將這兩次放棄與轉行統一在了傳主“得其自”與“吾喪我”的生命歷程中。《前半生》寫的是沈從文第二次轉行之前的生命歷程,并且這個歷程是在一定文學史背景下呈現出來的,也就是說,作者是將傳主放到了文學史中進行審視,并連帶寫了一些與沈從文文學創作相關的人與事。
從這個角度看,該傳記與四年前出版的《沈從文的后半生:1948-1988》的確有不同之處:前者是將傳主放在文學史背景下進行敘述,將傳主的身份界定為一位作家;后者則將傳主放在特定的歷史語境中敘述,并沒有局限于文學史的背景,作者也沒有非常清楚地對傳主的身份進行界定,其身份也常隨著人事的變動常有變動。因此,這兩本書雖然呈現了沈從文的一生,但比較而言,《前半生》更將傳主局限于一個身份,字里行間表達了作者張新穎的“學者”姿態,尤其在表達“沈從文的世界比人的世界大”這一觀點的時候,更是以此概括了作者對傳主前半生文學創作的觀點。因此,在“傳記事實”的呈現上,該傳記對傳主個性的表現主要集中在他的文學個性上。
在“傳記事實”的擇取與寫法方面,與金介甫的《鳳凰之子·沈從文傳》(由于該書印行多版,文中所用的為2018年7月的最新一版,由北京新星出版社出版的《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比較,也能顯出該傳記在呈現“傳記事實”上的特點。一方面,張新穎的《前半生》多擇取傳主在文學生涯上的歷史片段,而金介甫多擇取傳主所處的歷史局勢;前者注重傳主的文學個性,并試圖通過歷史來突顯傳主個人的文學創作生涯,后者則突出了傳主的歷史觀點對其文學創作發生的影響,有以文證史的傾向。另一方面,在“知人論世”的傳統傳記寫作方法上,如果說金介甫寫作傳記的特色是將沈從文自身的歷史及其所在的歷史大背景與其文學作品互相闡釋的話,那么,張新穎的傳記寫作則重點突出了沈從文在文學創作上的開筆、成長、封筆的過程,其間穿插傳主的戀愛故事、家庭成員在各時期各階段的情況等支線,通過傳主的文學生涯探索其人。
在后記中,作者寫作的初衷得以窺探。因為作者想要“發掘對象的豐富性”,所以不想用自己的觀念與眼光定義傳主的形象,并通過材料的組織表現傳主的一生,給讀者留下較大的思考空間。但實際上,通過前文的論述,作者不但字里行間透露出自己的觀念與眼光,在擇取“傳記事實”表現傳主個性的同時仍然有自己的側重點,并從傳主的“作家”身份出發,來呈現他的前半生。因此,在“傳記事實”的呈現上,傳主沈從文其人與其文之間的距離,是作者沒有把握好的一點。作者對傳主個性的界定雖然非常清晰,但仍有以偏概全之嫌。
作為一位讀者,該傳記在“自傳事實”、“歷史事實”與“傳記事實”所構成的事實體系內快速地了解了傳主沈從文在1902至1948年的文學創作生涯,呈現出一定的“敘事”文風,,突顯了傳主的文學個性,在傳記材料的發掘與排列中呈現一個傳主的音容笑貌。由于平鋪直敘的筆法與樸實無華的文風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非常順利,其可讀性不言而喻。作為一部傳記文學,作者對傳主文學生涯的呈現無意于通過新的理論、新的角度來重新展現與闡釋傳主的一生。作者張新穎所做的“創新”似乎也不是所謂的創新,而是通過對史料的重新展現與闡釋發揮他們的價值。在傳記材料的運用上,作者張新穎在“事實”的建構上,仍是非常客觀嚴謹的。
注釋:
①梁慶標:《傳記家的報復:新近西方傳記研究譯文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第32頁。
②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上海三聯書店2018年版,第361頁。
參考文獻:
[1]梁慶標.傳記家的報復:新近西方傳記研究譯文集[M].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5.
[2]趙白生.傳記文學理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
[3]張新穎.沈從文九講[M].中華書局,2015.
[4]丁帆.中國鄉土小說史[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5]張新穎.沈從文的前半生[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
[6]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
[7]張新穎.沈從文的后半生[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18.
[8](美)金介甫.他從鳳凰來:沈從文傳[M].符家欽,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