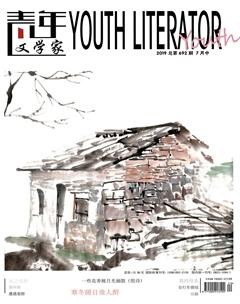孔子“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中道觀”比較
摘? 要:孔子和亞里士多德分別在德行倫理的研究中提出了中庸(中道)原則。兩者在內容和方法上都比較接近,但仍有些微的區別。孔子的“中庸之道”體現出對個體行為的德行之和諧追求,主張一種在世而超越塵世的一種“時中”之中庸之道;亞里士多德“中道觀”以個人幸福為出發點,主張一種代表和實現德性、善的完滿性的“空中”中道觀。“中庸”(“中道”)思想經歷歷史大潮的沖刷和洗禮,至今對個人思想和行為、社會和諧仍有著廣泛、深刻、積極的影響。
關鍵詞:亞里士多德;孔子;中道觀;中庸之道
作者簡介:桑延海(1991-),男,漢族,甘肅武威人,江蘇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碩士研究生,現從事于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化研究。
[中圖分類號]:B22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02
一、孔子“中庸之道”的基本內涵
“中庸” 之意在經書中的最早出現,是《論語·堯曰》引《尚書》的“允執厥中”這句話,是堯傳授給舜的。孔子首次將“中”與“庸”連為一詞而稱為“中庸”,“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從“其至矣乎”四個字來看, 孔子是把它當作很重要的觀念的,雖在《論語》中僅出現一次,但中庸的思想已貫穿于《論語》之中, 到子思作《中庸》,孔子的門徒已經把“中庸”從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高度概括為儒家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兩千多年來,“中庸”這一思想經歷歷史大潮的沖刷和洗禮,至今仍有著廣泛而深刻的影響。
在孔子的思想體系中,“中庸”的基本含義是“執兩用中”。北宋理學家程頤解釋說“不偏之為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熹進一步發揮程頤的說法說:“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至極也。”(同上)所以,在儒家心中,中庸既是極精微的道理,也是極平常的道理。在《論語》中,孔子論述了“執兩用中”的思想方法原則。如“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論語·先進》)這是對人的批判方面的。“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論語·堯曰》)這是對做人做事的看法。“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論語·雍也》)這是對理想人格的刻畫。
對“中庸之道”論述較為全面的是《禮記·中庸》篇,“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在這里,主要指的是人應該將其欲望、情感、行為等控制在到的允許的范圍之內。只有這樣,萬事萬物才能和諧統一,并育生存。
二、亞里士多德“中道”觀的基本內涵
幸福是亞里士多德的出發點,他將幸福定義為“靈魂的一種合于德性的現實活動”。他認為:“在實踐中,確實有某種以其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而一切其他目的都要為著它。……不言而喻, 這一為自身而被期求的目的也就是善自身,是最高的善。”[1]這種最高的善也就是一種終極的善,也就是幸福。終極的善是自足的,因為它“無待而有”,能使生活變得愉快。而我們說幸福也具有終極性和自足性。幸福的終極性表現在幸福是一切善的事物中的最高選擇,是一切行為的目的。自足性是說幸福是“無待而有”,憑其自身就可使生活變得愉快。幸福的終極性和自足性正表明了它的至善性。所以,幸福就是最高的善,就是至善。
在他看來,追求幸福,是作為生命的自然之本然目的。而且,生命都有與之自然之本然目的相適應的能力特征。不在能力范圍之內的目的,或者沒有目的的能力,都是非自然的。作為生命存在的人當然也是能力與目的的統一。人的獨特的能力就在于其理性能力,而且,理性的最基本的能力就是趨善避惡、分辨是非。當人們自覺地運用理性能力指導其行為時,人的理性能力便表現為人的德性。根據自然之目的與自然之能力相統一的理論基礎,那么幸福的生活必然有賴于德性之行為。
所以亞里士多德認為,人的道德目的就是有意識地實現作為善的道德目的。可以看出,亞里士多德將德性分為了目的與手段兩個層面。“德性確保目的的正確,實踐智慧確保目的之手段”,“德性顯示目的,實踐智慧是我們去做的受目的所支配的事情”[1]。作為德性的手段,或者作為手段的德性,就是“實踐智慧”。而且他認為“思慮”和“選擇”,是“實踐智慧”的兩個明顯特征。“思慮”就是要求我們尋求實現目的的最佳手段,“選擇”則是思慮的結果。亞里士多德提出“思慮”和“選擇”兩個原則的意義在于,“思慮”代表了理性主義倫理觀的,而“選擇”則成為自由意志的萌芽。
實踐智慧作為一種在理性原則基礎上的選擇,而且是一種對于德性的選擇,必然有其標準。這一標準被亞里士多德概括為“中道”。他說,“德性是牽涉到選擇時的一種性格狀況,一種適中,一種相對于我們而言的適中,他為一種合理的原則所規定,這就是那些具有實踐智慧的人用來規定德性的原則。”[1]所以,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就是要求人的情感和行為要適中,這又是由實踐智慧規定。
三、兩者思想的異同比較
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從一定意義上來講都是一種實踐智慧,要求人的行為上的德性及其選擇,而且有著很強的政治訴求,就此而言,凄涼中思想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首先,“中庸”或“中道”都要求人們的言行恰到好處,是人們道德水準的體現,都是一種實踐智慧。在他們看來,選擇和行為上的“中庸”和“中道”,是理想的人格和理想德性的體現,也是社會倫理道德的最高境界。在孔子的思想體系當中,“中庸”是一種最美好的品德,但是人們已經很久不具備它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論語·庸也》)。亞里士多德也說,“美德乃是一種中庸之道”。所謂的“美德”,是一種通達完滿至善的實踐智慧。
其次,從方法論角度來看,“中庸”和“中道”思想都具有樸素的辯證精神。“中庸”和“中道”作為實踐智慧,都主張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不管是中庸之道的“執兩用中”,還是中道的“德性之至善”,都表現出對思想和行為的“過”和“不及”兩者之間的矛盾的一種和解。
再次,“中庸”和“中道”思想都是一種社會價值觀,以期形成一種安定的社會秩序。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都生活在新舊社會的交替時期,社會動蕩不安。孔子提倡“仁”,強調中庸之道,希望通過“仁”學體系和“中庸”方法,建立一個上下有序的安定社會。亞里士多德認為,人是有理性的動物,理性的目的就是使人幸福。倫理是低級的幸福,政治是高級的幸福。而“中道”則是通向幸福的現實路徑和基本品德。只要人人都具備“中道”這一品質,那么政治的“善”和幸福的目的也就有了現實的路徑。
盡管孔子的“中庸之道”和亞里士多德的“中道”觀由諸多的共同之精神,但由于他們生活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具有很大的差異,而且其思維方式也有著很大的區別,所以其對于現實世界的體悟與認知也有很大的差異,進而其理論體系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差異在其“中庸之道”和“中道觀”上也有集中體現。
首先,就中庸和中道之本體論意蘊而言,孔子的“中庸之道”之“中”,指的是一種“時中”;亞里士多德的“中道”之“中”,則更多的是一種“空中”。在孔子看來,與其說任何事物都會有一個最佳或最合適的狀態,不如說任何事物都不會有一個絕對不變的最佳狀態。但是這不意味著最佳狀態是相對的,而是說最佳狀態是與時地分不開的。所以,孔子說:“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中庸》)在亞里士多德看來,“中道”是德性的標準和實現方式。與德性之“中道”相反的則是兩個對立的極端,即“過分”和“不足”。過分是“主動的惡”,不足則是“被動的惡”。例如,“自信”是實現自身目的的一種德性,但是過渡自信則為“驕傲”、“自負”,而缺乏自信則表現為“自卑”。在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對于作為“中道”的“自信”,這是一個確信無疑的德性概念,對于其過度的“驕傲”與缺乏的“自卑”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不能算是一種德性。德性是每一個行為和思想的獨一無二的品格,程度適中的邪惡仍然是邪惡。
其次,“中庸”或“中道”的實踐原則也不一樣。孔子的中庸之道之于事物的最佳或者最合適的狀態,其絕對不是唯一的,固定不變的。事物的最佳狀態,是以具體的時間、地點等各方面的條件為轉移的,因而對實現事物之最佳狀態的中庸之道也是有多種選擇途徑的。亞里士多德的“中道”所表示的德性的特質是獨一無二的品格。德性自身是與一切惡相分離的善,不論多一些還是少一些,不符合德性的標準,就不是善,亦或說“中道”所表示的德性之善,乃是的一種完滿性。所以亞里士多德在《尼各馬可倫理學》當中說:“怨毒、無恥、妒嫉、通奸、謀殺,這些活動的名稱已經意味著它們本身的邪惡的性質,并非由于它們的過分或不足才是惡的。所以,要想在不義、卑怯、淫佚的行為中發現的一種中道,一種過分和不足,同樣是荒謬的。”
最后,就境界而言,“中庸之道”和“中道”觀的追求也是不同的。孔子期望一種“中庸而致中和”之境界。他認為,如果人們都具備了“中庸之道”的德性,那么自我身心的融洽、社會的安定有序,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都是都是可以得到的。“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中庸》)孔子追求人的自我實現與自我超越與人間的倫理道德結合起來。但是這種人生的超越之境,并非要人們遠離人間煙火;人生有限性的突破與對無限性的向往與追求,并非要人們舍棄有限。因此,中庸的人生哲學追求的,其實是一種既高明而又平凡的人生。亞里士多德的思想體系中,善是倫理學和政治學的目的,要實現這一目的自然需要德性,而德性就體現為他的“中道”觀。他企圖在“中道”觀的規范下,人們都能享有美好的有德性的生活。根據這一理論,他認為現實政治的德性就體現為中產階級執政,并作為仲裁者。因為“他們不會像窮人那樣覬覦他人財富,也不會像富人那樣引起窮人的覬覦,沒有別的人會打他們的主意。他們不想算計他人,也無被人算計之虞”。這種中道思想作為德性之標準、幸福之至善,對人、對社會的這種規定只是一種外在的規定性。
參考文獻:
[1]亞里士多德.尼各馬可倫理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2]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3]趙敦華.西方哲學簡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
[4]郭齊勇.中國古典哲學名著選讀[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5]張永妍,劉子飛.亞里士多德幸福觀及其當代價值[J].長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02):113-116.
[6]呂振. 孔子中庸思想與亞里士多德中道德觀比較研究[D].華南師范大學,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