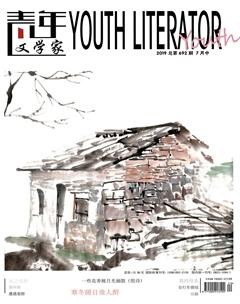淺論東野圭吾小說中暗含的暴力美學因素
摘? 要:推理小說作為大眾喜愛的文學形式,在國內外的研究都開展得如火如荼。東野圭吾作為新生代推理小說作家,他的眾多作品都在國內備受追捧。因此,本文以東野圭吾小說為中心,以暴力美學為理論依托,圍繞著暴力美學一系列的理論,從形式化、人性化書寫角度,對其作品暗含的暴力美學進行深入解讀。
關鍵詞:東野圭吾;暴力美學;推理小說
作者簡介:張唯(1996.6-),女,漢族,江蘇省昆山市人,現就讀于揚州大學文學院2018級文藝學專業,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美學。
[中圖分類號]:I1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2
暴力美學作為一種藝術趣味和創作形式,是從香港電影中衍生而來的一種美學形式。暴力美學主要是在官感上,使得暴力以美學的方式呈現,用詩意的畫面、幻想中的鏡頭來表現人性暴力面和暴力行為。觀賞者往往驚嘆于其藝術表現方式,卻無法對內容產生不適感。暴力美學在當代社會也有愈演愈烈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研究暴力美學并且使用暴力美學理論對文學文本進行研究,暴力美學的范疇也逐漸從電影行業轉移到對文學的研究中來。“暴力美學”在文學作品中可分為兩種不同的呈現形態:一是暴力在經過形式化、社會化的改造后,其攻擊性得以軟化,暴力變得容易被接受,甚至被運用于一些正面人物身上,從而隱匿了其侵害性傾向;二是直接展現血腥過程,渲染暴力的感官刺激,通過作者的藝術化處理,反而增加了作品的美感,從而消解了暴力的殘酷性。日本獨有的暴力美學,反差鮮明而不留余地,游離于野蠻與文明兩極。特別是推理小說家東野圭吾,其作品大多涉及“暴力書寫”,無論是場景描寫的角度,還是社會描寫的角度,都對暴力美學這一范疇作了完美的闡釋。本文擬從其形式化、人性化書寫角度,對其作品暗含的暴力美學進行深入解讀。對于東野圭吾小說中的“暴力美學”的考察更多的是通過對其表現出來的一般性意義的逐一考察,再進行綜合概括的方法去呈現它的綜合性意義。
一、暴力美學的總起源
暴力美學存在三個方面的形態:一是存在于意識與潛意識之中的觀念形態的暴力美學。二是理論形態上的暴力美學,學者對暴力美學進行理論上的分析研究進而總結出觀點、原則。三是實踐意義上的暴力美學,是具有藝術形式的暴力美學。暴力美學一般限定于暴力的藝術表現形式之中,但是當我們拋開道德、法律的約束,僅僅從美學角度去審視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事件時,暴力事件也能給與人們美的感受。現實生活中的事件可以當成是符號來解讀從而獲得符號化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暴力美學化絕對不是暴力的日常化、普遍化,而是暴力的美學化、形式化。
“暴力美學”和“暴力”有著很深的聯系,但是二者又不能簡單地劃等號。觀念意義上的暴力美學雖然沒有具體的外觀,但卻具有內蘊形式,是形式化、藝術化了的具體的暴力。觀念意義上的暴力美學是在心里已經想象出來的暴力的想象形態。現實生活中發生的或顯或隱的暴力事件,究其本質就是暴力。暴力的藝術形式則表現為暴力美學。
暴力欲望是人的根本的人性之一,是不必諱言的人的原始欲望。然而,人是有思想的生命存在,具有自我調節機制。暴力欲望作為可控因素,可以通過其他形式進行調節,從而使暴力欲望達到一個相對平衡的狀態。暴力美學正是人類調節暴力欲望的重要機制之一。
二、東野圭吾小說中形式化的暴力美學敘述
(一)零度情感敘事
零度情感敘事是一種“貌似”不加進敘述者意見的客觀敘述,它“不存心歪曲事實,避免把敘述人的意見寫進事件中”。[1]文學作品中的暴力通過形式化語言,將血腥、暴力轉化為純粹的形式之美,通過塑造典型形象來反映社會生活,從而使得暴力書寫的存在成為可能。
在長篇小說《白夜行》中,東野圭吾用“零度情感敘事”展現了親人與朋友之間的互相殘殺場面,用冷靜的筆觸展現了人性的自私與冷漠,使讀者通過文本感受到深刻的黑暗與絕望。東野圭吾將人性、死亡、生命以形式化的語言進行加工處理,以此給人深刻的反思與警醒。在《白夜行》中,有多處對于死亡的客觀描寫,比如,開頭處便寫道的發現桐原父親死亡時的情景:
“死者衣著整潔,沒有分線、全部向后梳攏的頭發也幾乎沒有變形。”[2]
“桐原亮司今天仍面無表情。陰郁深沉的眼眸沒有浮現任何感情波紋。他那雙有如義眼般的眼睛看向走在前方的母親腳邊。”[3]
另外,在描寫女主角雪穗設計殺害母親時,東野圭吾用近乎冷酷的敘事手法,直接跳過了對西本文代以及雪穗的描寫,筆鋒一轉雪穗已經成為了高雅端莊人人羨慕的養女。東野圭吾以偵探視角,用客觀冷靜的眼光觀察死亡和暴力結果,有一種近乎殘酷的冷漠。
除此之外,東野圭吾也用“零度情感敘事”描寫了多起肉體暴力事件:
“藤村都子上半身赤裸,下半身除了裙子,所有的衣物都被脫掉,丟棄在她身旁。此外,還找到了一個黑色塑料袋。”[4]
“隨著牟田暴怒的吼叫,一個東西塞進雄一嘴里。直到他歪向一邊,才知道那是鞋尖。牙齒咬破了嘴,血的味道擴散開來。他正想著‘好像在舔十元硬幣,劇烈的疼痛便席卷而來。雄一遮住臉,縮成一團。在他的腰腹上,牟田等人的拳腳如雨點般落下。”[5]
零度情感敘事將現實中的不了能變為藝術的可能,為讀者設置了一種真實的邏輯感。“用死亡、血腥來表達他對世界的一種認識,用虛構的記憶來對抗現實中貪婪的人性,從終極意義上對人的生存悲劇和生存宿命的探尋與超越。”[6]通過展現人性的錯位與扭曲,使得作品具有了巨大的沖擊力,成為生命意識升華的暴力美學形式。
(二)“連環套”的寫作手法
弗洛伊德認為,通過閱讀文學作品,可以使讀者的暴力欲望得到合理的宣泄,即通過作品轉移現實中的暴力心理。根據弗洛伊德的三重人格理論,現實生活中“本我”的“暴力本能”無法得到滿足時,“超我”便對“自我”進行監督管理,探尋宣泄“暴力本能”的另一種途徑,即“暴力本能”的替代性滿足。
在東野圭吾的小說中,“暴力本能”的替代性滿足主要通過“連環套”的方式為讀者提供宣泄暴力欲望的途徑,即不斷制造暴力、死亡,以契合讀者的心理期待。《白夜行》的男主人公桐原亮司,他與唐澤雪穗的關系猶如“槍蝦與蝦虎魚”一樣相互依存,亮司對雪穗的愛徹底而又毫無保留。亮司不斷強奸威脅雪穗的女性,為雪穗的成功鋪路。為了保全雪穗甚至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白夜行》中所描寫的戀童癖、殺父弒母、校園暴力等在現實生活中不可能實現的事件,讀者在欣賞過程中作為旁觀者,不斷被暴力所吸引,從而達到暴力欲望的短暫釋放,從而滿足讀者對于體驗陌生世界的期待心理。值得注意的是,推理小說以暴力吸引讀者,并不是說讀者需要暴力,而是讀者需要被暴力引誘從而釋放暴力欲望,從而達到心理的平衡狀態。
三、東野圭吾小說中人性化的暴力美學展現
(一)“血”的意象展現
在《白夜行》中,生命的產生和毀滅凝結為“血”的意象。“血”在中文語境中有“血緣”、“血統”、“血親”等詞匯,指向的是一種人類因生育而結成的關系。“血”常常被認為指向人的靈魂,有一種生命源泉的觀念。
桐原亮司殺父、唐澤雪穗弒母,這是生命本身的表現形式,也是隱含的“血”的意象,基于血親關系的互相傷害,就變成了血跡。小說中個體的生命顯得異常脆弱,往往表現為暴力后的血跡。《白夜行》中有多處對于血跡的描寫:
“胸口有直徑十厘米大小的深紅色血跡。此外還有幾處傷痕,但沒有嚴重的出血現象。”[7]
“牙齒咬破了嘴,血的味道擴散開來。他正想著‘好像在舔十元硬幣,劇烈的疼痛便席卷而來。”[8]
“有東西扎在桐原胸口,由于鮮血涌出難以辨識,但笹垣一看便知。那是桐原視若珍寶的剪刀,那把改變他人生的剪刀!”[9]
發生在至親之間的慘劇,正體現了原始暴力欲望的爆發對社會規則的突破,“超我”未能通過“自我”有效控制“本我”,“死本能”躍居“生本能”之上,人性的陰暗面一覽無遺。
亞里士多德說:“現在讓我們研究一下,哪些行動是可怕的或可憐的。……只有當親屬之間發生苦難事件時才行,例如弟兄對弟兄、兒子對父親、母親對兒子或兒子對母親施行殺害或企圖殺害,或做這類的事——這些事件才是詩人所應追求的。”[10]《白夜行》通過血親之間的悲劇引起人們的憐憫和同情,從而產生了強烈的悲劇意味。進而引發人們對于“血親”更深層次的思考。血親與現實、生命的誕生與毀滅、糾結的血緣與血污,在“血”的意象群中相互糾纏不休。
(二)疏離和毀滅中的人性追問
對社會的憂思、對人性的追問,是一個永恒的話題。因此,東野圭吾始終嘗試深入挖掘解剖人性,解讀人類的精神世界。東野圭吾推理小說符合大部分讀者對于推理小說的既定印象,他所敘述的底層社會群眾的心理狀態與大眾生活相吻合,因此,讀者從他的小說中可以得到精神上的共鳴感。東野圭吾作品往往淡化破案過程,著重描寫揭露人性之惡,實現讀者與文本之間的心靈交融。作品中對于人性的呼喚,是其在各地掀起熱潮的根本原因。
人作為理性的化身,享有智慧的美名。創造自身美好生活也是對生命真實性的解讀。東野圭吾在小說中為我們揭示了另類的“真實”:生命存在的疏離和毀滅。在《白夜行》中表達了對死亡的冷漠和人性的麻木:
“她沒有回答,雙手覆住臉頰,緩緩移動,遮蓋住面容,雙膝像支撐不住似的一彎,蹲在地上。好像在演戲呀,笹垣心想。哀泣的聲音從她手后傳了出來。”[11]
東野圭吾通過描寫了人與人之間互相殘殺的暴力場景表達了對人性的失望、對生存的沉重思考。用暴力的形式嘲諷理性人的虛偽,達到對人性的形而上思考。
原始欲望突破社會秩序的規范而無節制釋放,作為適應社會的“自我”必然要調解“本我”與社會之間的關系。有人認為:“作品中難以抗拒的暴力形式與潛在的人文內核相互纏繞著。事件的悲劇性質明確表現出來。于是人的命運和精神等人文問題一次次被尖銳地揭示和呈示,以引起我們更多的注意和警醒。”[12]人與人成了彼此的地獄和夢魘,在形式層面上拷問著人的存在和生命的價值:發生在有理性的人身上的血腥、暴力事件,在情感缺失的世界中真實地存在著。那么,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生命存在的意義何在?剝去了理性和善的偽飾,崇高的親情被徹底顛覆。對于“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的回答,只剩下了肉體的暴力。相同的肉體為什么能演繹出暴力、血腥、殘殺,仍然是一個謎。也許,這就是東野圭吾小說為人性所提示的問題。
注釋:
[1]徐江:《寫作原理新論批判與構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16頁。
[2]東野圭吾:《白夜行》,劉姿君譯,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5頁。
[3]同注釋[2],第19頁。
[4]同注釋[2],第70頁。
[5]同注釋[2],第84頁。
[6]鄭民,王亭:《文學與醫學文化》,山東大學出版社,2015年,第149-150頁。
[7]同注釋[2],第5頁。
[8]同注釋[2],第84頁。
[9]同注釋[2],第538頁。
[10]亞里士多德:《詩學》,羅念生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第44頁。
[11]同注釋[2],第7頁。
[12]劉樹元:《小說的審美本質與歷史重構 ——新時期以來小說的整體主義觀照》,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23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