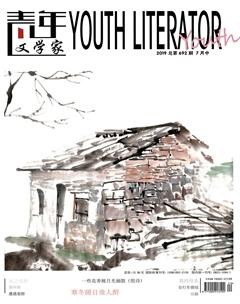從“語言游戲”的角度看《文字下鄉(xiāng)》
摘? 要:本文試圖從“語言游戲論”的角度看費(fèi)孝通的《文字下鄉(xiāng)》,在實(shí)際案例中挖掘語言游戲的意義,體會語言游戲的多樣性、實(shí)踐性、人本性、淺談一下這次跨學(xué)科比對材料研究的感悟。
關(guān)鍵詞:語言游戲;文字下鄉(xiāng);家族相似性;實(shí)踐性
作者簡介:張睿驍(2002.3-),女,漢族,山東日照人,山東省實(shí)驗(yàn)中學(xué)西校區(qū)2020級在讀高中生,研究方向:哲學(xué)。
[中圖分類號]:C91?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9)-20--02
費(fèi)孝通是我國著名的社會學(xué)家,本文涉及的著作《文字下鄉(xiāng)》、《再論文字下鄉(xiāng)》收錄于《鄉(xiāng)土中國》,該書是一本簡述鄉(xiāng)村社會生活狀況的社會學(xué)著作。費(fèi)孝通先生作為一位注重社會實(shí)例研究的大家,文筆很生動幽默、小中見大,選取的研究材料都很有啟發(fā)性、引人深思。在閱讀《鄉(xiāng)土中國》前不久,筆者正好讀過《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zé)任》,覺得費(fèi)孝通寫的《文字下鄉(xiāng)》中一些對于語言的闡述,和維特根斯坦的一些想法不謀而合,在此忍不住想將相似的部分摘出來,進(jìn)行一番對比,談一談自己的淺顯見解。
關(guān)于語言游戲,已有不少學(xué)者闡釋過,也歸納出其特點(diǎn)有家族相似性、實(shí)踐性、語言形式的多樣性、有用法和規(guī)則。筆者認(rèn)為這些概括都很合適,也借用了這些理論。筆者想說,因?yàn)闆]有系統(tǒng)學(xué)過語言游戲說的理論,此文都是斷章取義地節(jié)選一些《維特根斯坦傳——天才之為責(zé)任》、《哲學(xué)研究》中讀起來有感觸的語句,再與《文字下鄉(xiāng)》等比較研究,按照自己的理解解釋,可能有失偏頗。筆者盡力想為語言游戲找到更多的參考實(shí)例,探索語言游戲說與社會實(shí)踐更多的聯(lián)系,在此分享一些淺顯的見解。
“我想大家必然有過‘無言勝似有言的經(jīng)驗(yàn)。其實(shí)這個篩子雖則幫助了人和人間的了解,而同時也使人和人間的情意公式化了,使每一人,每一刻的實(shí)際情意都走了一點(diǎn)樣。我們永遠(yuǎn)在削足適履,使感覺敏銳的人怨恨語言的束縛。”看到《文字下鄉(xiāng)》中的這一段話時,筆者突然意識到,語言不過是信息的載體。不僅哲學(xué)家意識到了語言的本質(zhì),社會學(xué)家如費(fèi)孝通也意識到了,就連普通人也可從日常生活中略窺一二。我們都有過咬文嚼字的經(jīng)歷:按照語文考試中的字題要求,反復(fù)推敲一個字的含義;腦海中不斷回放某人說話的情形,揣測他的意圖;將一句名言放到不同的情景中,以此得到更多啟示,等等。這是因?yàn)檎Z言不是一個精確的載體工具,它雖能輕巧靈便地、跨越時空維度地傳遞著人們的感受,但因主體差異性,每個人面對同一事物都有不同的認(rèn)識角度,造成“橫看成嶺側(cè)成峰,遠(yuǎn)近高低各不同”的有趣結(jié)果。從這里不難看出,脫離實(shí)際,拿一套規(guī)則去解釋另一套規(guī)則,憑主觀臆斷解釋語言,最終會和分析“一場空”沒什么區(qū)別。語言會喪失自己的意義,成為人腦凌亂想象的反映罷了。維特根斯坦的一段總結(jié)分析得非常到位:“事物必須用不著繩子而直接相連,即,它們必須已位于一種互相聯(lián)系之中了,就像鏈條的鏈環(huán)。”語詞與其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不是在理論中,而是在實(shí)踐中、在語詞的使用中找到的。我們要明白語言是信息傳遞載體這一本質(zhì),側(cè)重于理解它,看出它與事物的聯(lián)系。這應(yīng)該是一種科學(xué)審慎的理解,回避了憑空分析,卻要做到從實(shí)踐中來,到實(shí)踐中去,保持嚴(yán)肅的思考。
《鄉(xiāng)土中國》作為一本記錄和分析大量鄉(xiāng)村實(shí)踐的著作,給我們分析語言游戲提供了大量素材。先看語言游戲的實(shí)踐性特點(diǎn)。費(fèi)孝通先生在書中介紹,中國的鄉(xiāng)土社會是一個熟人社會,是面對面的社群,人們都熟悉到可以憑借足音、聲氣、甚至氣味來辨別一個人,說的話自然比較儉省了,正如文中所言:“于是在熟人中,我們話也少了,我們‘眉目傳情,我們‘指石相證,我們拋開了比較間接的象征原料,而求更直接的會意了。所以在鄉(xiāng)土社會中,不但文字是多余的,連語言都并不是傳達(dá)情意的唯一象征體系。”費(fèi)孝通先生在《文字下鄉(xiāng)》中稱這種現(xiàn)象為“特殊語言”,并且一針見血地點(diǎn)出“每個特殊的生活團(tuán)體中,必有他們特殊的語言,有許多別種語言所無法翻譯的字句。”這些“特殊語言”最普遍的是母親和孩子之間的,此外還包括各種行話、年輕人之間的流行語等等。它們形成的條件都是一個社群長期共同進(jìn)行某種實(shí)踐活動,擁有一定的相同的經(jīng)驗(yàn)。語言只能在一個社群所有相同經(jīng)驗(yàn)的一層上發(fā)生。“群體愈大,包括的人所有的經(jīng)驗(yàn)愈繁雜,發(fā)生語言的一層共同基礎(chǔ)也必然愈有限,于是語言也就愈趨于簡單化。這在語言史上看得很清楚的。”也就意味著經(jīng)驗(yàn)賦予了語言意義,而“經(jīng)驗(yàn)”其實(shí)就是指實(shí)踐。再從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的角度來看,語言游戲的實(shí)踐性還有一個理論支持:“物質(zhì)決定意識,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因而《邏輯哲學(xué)論》里把語言看作孤立靜止的描述符號的看法是不被接納的,《哲學(xué)研究》里視之為動態(tài)的人類活動的觀點(diǎn)是被欣然接納的。另外,這種語言含義隨著主體、時間、事件而不同的特點(diǎn),以社會歷史性來概括挺合適的。筆者認(rèn)為語言活動某種意義上可以被粗略地看成實(shí)踐活動——雖然語言活動沒有直接現(xiàn)實(shí)性,與馬克思主義哲學(xué)辯證唯物的觀點(diǎn)又不謀而合。
在《哲學(xué)研究》中,維特根斯坦把語言比作老城,筆者認(rèn)為這個比喻十分貼切。我們的語言確實(shí)像一座不斷翻修、增添的老城一樣,有一定的基礎(chǔ)又十分復(fù)雜多變。應(yīng)實(shí)際要求,我們的語言可簡可繁,像是“結(jié)繩記事”、廣西瑤山部落以銅錢作為救急信號、“指石為證”,這些大都發(fā)生在交流環(huán)境親密簡單的時候。如果是跨城、跨省、跨國交流,商務(wù)、政事文書類就會十分繁復(fù)周密,這是出于“間接接觸”和事務(wù)復(fù)雜程度的要求,這種時候就需要文字有普適性。就像廣西瑤山部落有急,派人送一枚銅錢到另一個部落,對方立刻就知道要派人來增員;然而放到二戰(zhàn)時,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可不能交換銅錢了。因而無論是秦始皇統(tǒng)一文字,還是現(xiàn)代改用簡體中文,改良文字時首先應(yīng)該注意文字的實(shí)用性,從社會實(shí)踐的角度來考慮。正像改造老城時一定先考察老城的原地基一樣。隨著我們處理的社會實(shí)踐復(fù)雜度的提高,我們的“老城建筑”也更加細(xì)致,因此要講究文法、講究說話的藝術(shù),其實(shí)這都是為了不使說的話走樣,盡量減少誤會。畢竟文字只是工具,我們很少在意一個房屋是否漂亮,而是看它是否實(shí)用,對語言來說也應(yīng)如此。不應(yīng)該是專家覺得這樣的語言漂亮簡潔,我們就采用這樣的語言;而應(yīng)是廣大勞動人民群眾使用這樣的語言方便舒心,我們就整理歸納出這樣一套語言。這也是語言游戲的實(shí)踐性給現(xiàn)世的一個指導(dǎo)。
“老城”比喻還給我們一點(diǎn)啟示:人們對后來語言的學(xué)習(xí),都是建立在之前的經(jīng)驗(yàn)上的。《哲學(xué)研究》里還以“五個紅色蘋果”為例,講過一種語詞的運(yùn)算。語言游戲里確乎有一個神奇的語言加法:我們可以用熟知的詞來解釋一個未知的詞,甚至是獲得一種新體驗(yàn)。筆者認(rèn)為,這是語言除了作為一種運(yùn)輸工具外,另一大魅力。各位可以回憶下我們學(xué)習(xí)語文課文時的情形:老師通過大段的解釋來講解一個字的妙處,或是分析環(huán)境描寫的作用時。雖然我們既沒有真的經(jīng)歷過那種場景,但是一經(jīng)老師解釋后我們都可以有身臨其境的感覺、悟性好的還可以得到和作者一樣的人生感悟。《再論文字下鄉(xiāng)》里也提到大致意思,人和其它動物不同是因?yàn)槿擞杏洃浀哪芰Γ@種記憶不一定要用紙上的文字表達(dá)出來。費(fèi)孝通先生認(rèn)為鄉(xiāng)下老農(nóng)不認(rèn)字,但是并不愚蠢,就是因?yàn)橹腔圻€有默會這條傳遞路徑。畢竟正如維特根斯坦指出的那樣,我們要意識到理解的重要性,而不是陷在形而上學(xué)的泥淖里一味的分析,被引誘著用科學(xué)的方法提出和回答問題,不斷地給自己找麻煩。
費(fèi)孝通先生的《鄉(xiāng)土中國》不是哲學(xué)著作,但是他寫的足夠淺顯易懂,又蘊(yùn)含著深刻的道理。筆者認(rèn)為討論哲學(xué)不一定就要拘泥于哲學(xué)著作,如果有更加易懂的例子,我們可以從好理解的入手。我們是為了努力接近本質(zhì),只要目的能達(dá)到,何必在乎用什么方法呢?維特根斯坦不正是強(qiáng)調(diào)“賴端于看出聯(lián)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