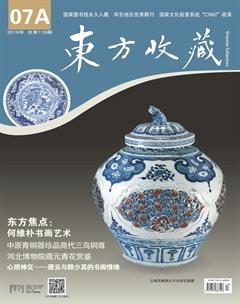以“戲”入畫 以“畫”品戲
沙偉



關良這一名字,對于了解近現代國畫史的人無不知曉,這出于其在畫壇成就卓著,對后人影響深遠。而他集戲劇藝術與寫意人物繪畫于一體,熔兩者于一爐,做到“畫中既有唱念做打,戲中又有筆情墨趣”的戲劇人物畫,更是別開生面、獨樹一幟,可謂以國畫寫意人物的藝術表現形式,將戲曲經典劇目中的重要橋段所展現的人物造型、身段手勢,能夠以筆墨語言躍然紙上(圖1 關良和他創(chuàng)作的戲劇人物畫老照片)。
藝術創(chuàng)作的成因
幼時父親偶得的幾張“洋片”(香煙牌子),十來歲“會館聽戲”的經歷,就引領少年關良于朦朧中,走進一個集社會、歷史、文化于一體的藝術世界。三國、水滸、西游、紅樓等這些生動的故事、有趣的造型、簡易的線條、多姿的色彩,令他以古典小說與戲劇題材為主,“絞盡腦汁”地收集數百張香煙畫片,并從此開始意猶未盡地模仿涂鴉。
青年時代的關良原來是留學海外學習西畫的,但至上世紀二十年代初,回國后的他卻形成了回歸傳統的意識。他加入了當時群賢聚集的“上海東方藝術研究會”學術研討活動,并主動結識吳昌碩、黃賓虹、潘天壽等中國畫壇領軍人物。且在這些文化名人的影響下,臨摹明清大家作品、觀摩參觀國畫展覽、欣賞名家收藏畫作。同時與沈雁冰、郭沫若、茅盾等文壇大家開始交往,并在堅定“師古人之心不師古人之跡”的藝術追求之時,為更多地借助中國畫筆墨與觀念,而探索一條新的“表現中國”的繪畫主題之路。且在國畫與文學的相互交融中,他意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集中體現、其從小熱愛的戲劇,正是他苦苦追尋之新的契機。
關良走入中國畫創(chuàng)作道路的動力之一,就是戲劇中演員的身段眼神、布景道具的程式化意識、燈光服裝的色彩構成,這些均成為了他筆下的構圖、造型、氣韻、色彩之創(chuàng)作元素。并由此開始以“戲劇人物畫”為創(chuàng)作主題,成功實踐了西畫與國畫的結合,出現了第一次重要的轉折。如他創(chuàng)作的《游龍戲鳳》(圖2 1944年作,80×99.9厘米,中國美術館藏)、《白蛇傳》(圖3 1956年作,67.5×70厘米,中國美術館藏),不僅為關良實現“我之為我,自有我在”的藝術境界找到了方向,而且還體味出他的寫意畫高度,以及其概括的筆力神韻與藝術趣味。
稚拙渾樸的畫風
縱觀關良的戲劇人物畫風格, 首先是線條語言的運用。在中國傳統繪畫中, 最具表現力的造型手段、最具審美意味的藝術語言就是線條。而在關良的戲劇人物畫中,線條的內涵卻更加豐富。用線除了輪廓造型之外, 結構也隨動勢用短粗的線條寫出, 猶如行草的書寫,卻又氣韻流動而貫通。故此種意義上,他的戲劇人物造型“似乎”結構比例不準,殊不知這正是他不拘泥人物解剖結構本體及細枝末節(jié)的簡單肖似,而求神奪勢、筆從氣來之高妙手法。以《烏龍院》(圖4 上世紀60年代作,67.5×44厘米,中華藝術宮藏)、《空城計》(圖5 上世紀60年代作,34.5×34.5厘米,上海中國畫院藏)和《武松打虎》(圖6 1974年作,68×43厘米,中華藝術宮藏)為例,三幅作品的線條指向重在傳達神韻氣勢,并不在簡單地塑造結構。仿佛一筆寫出畫中人物, 氣息連貫整體。同時充分利用戲劇人物臉譜的造型與色彩,匠心獨運、大膽生辣地進行面部處理, 令造型夸張、用色飽滿之余,線條恣意勃發(fā)。作品雖看似稚拙的“兒童畫”, 用筆功力卻透出凝滯、舒緩、力透紙背, 完全是一種中和內斂、深沉樸茂的審美意味之體現。
在關良的戲劇人物畫中,其強調臉譜、服飾、動勢、道具等戲劇本身的造型元素,而人物則趨于平面建構,弱化了三度空間的立體造型。如他的《孫悟空三打白骨精》(圖7 上世紀70年代作,31.5×34.5厘米,中華藝術宮藏)、《魯智深倒拔垂楊柳》(圖8 上世紀70年代作,68×68.5厘米,中華藝術宮藏)。這是他吸取了民間藝術的造型特點,可謂與漢代石刻藝術異曲同工。同時他不求面面俱到, 但求大膽概括,重點刻畫藝術形象的動態(tài)與情感流露,注重整體動勢造型, 似得其意而“忘”了其形般,以勢奪人地傳達出不同人物的精神氣息與神態(tài)之美。特別是在表現塑造人物的動態(tài)方面, 他更是汲取到漢代畫像磚的精華, 不僅極具蓄勢待發(fā)之力, 更充滿一種潛在的生命力度。而開張生動的簡潔造型,亦形成了飽滿充實、凝重渾樸的畫作構圖。
“他的畫在表現方法上繼承了國畫的優(yōu)良傳統而自成一派,重神似而不求形似。”這是一代京劇大師梅蘭芳在其《漫談戲曲畫》中談到的關良。與關良為莫逆之交南派武生泰斗蓋叫天,亦曾評價“關先生的(戲劇人物)畫是活的,看上去很神”,這說明關良對戲劇十分懂行,能選取戲里最為生動傳神的動作神態(tài)入畫。由于戲劇中的看、瞟、盯、瞧、觀、見,全得憑借一雙眼睛觀察,是對戲劇藝術家、畫家的考驗,因此關良點睛目也是把畫全部完成后才進行。而不同的人物、場合看不同的對象都有不同的感覺,故畫家和戲劇藝術家一樣,對此要把握分寸、細細揣摩,最后才能大膽準確地落筆。如關良的《打漁殺家》(圖9 上海中國畫院藏)、《鴛鴦樓》(圖10 上海中國畫院藏)、《春香鬧學》(圖11 1983年作,67×67.5厘米,中華藝術宮藏),眼神就抓住了戲中人物的轉瞬即逝,并將單純的舞臺動作,提煉成傾吐角色內心活動的肢體語言;再進一步將肢體語言提煉成筆墨精妙、極具寫意性的繪畫語言,且使之躍然紙上。
傳世佳作賞析
關良的戲劇人物畫《晴雯補裘》(圖12 1985年作,68×46厘米,中華藝術宮藏),描繪的是《紅樓夢》題材,即晴雯帶病連夜織補賈母送給寶玉的孔雀氅之場景。作品不拘泥于對人物的解剖和透視,并以戲劇人物造型為基礎,不加修飾地將夸張、變形之手法傳神寫照,甚至帶有兒童畫的稚拙。且畫家力求質樸平易、凝重自然的筆勢筆趣,讓筆墨變化多端。同時演員的“看”“瞟”“盯”“瞄”等眼神捕捉到位,令人物情態(tài)純真幽默、惟妙惟肖。
《捉放曹》(圖13 1980年作,68×68.5厘米,中華藝術宮藏)是關良創(chuàng)作的《三國演義》題材。作品中陳宮身穿黑袍、手持寶劍,而曹操身穿紅袍、伏案假寐。作品在色彩上一黑一紅形成強烈的對比,觀眾的視線瞬間就被抓住了。而在色彩的運用中,畫家對色彩的過渡與對比很注重,并且吸收了西洋繪畫的表現手法。您瞧位于陳、曹中間的黃色桌案,不僅弱化了由于色彩對比過于強烈而產生的視覺刺激,還令畫面顯得更加和諧統一,讓黑、紅兩色有了融合和與過渡的空間,使得觀者看來更加平和舒適。另外,“點睛”之筆是關良的戲劇人物畫創(chuàng)作中之鮮明特色。其看似粗枝大葉,實則細膩嚴謹。同時戲劇內容、情節(jié)表現、人物性格的不同,決定于人物眼神或喜或悲、或瞋或怒的明顯差異,宛如此作中陳宮眼里流露出的猶豫與悔恨,皆對作品的主題思想進行了充分表達。
《蘇三起解》是京劇《玉堂春》中的精彩片段,“京劇四大名旦”梅蘭芳、程硯秋、尚小云、荀慧生均曾有過精湛的表演。關良作為現代水墨戲劇人物畫的開創(chuàng)者,亦非常鐘愛此劇并反復畫過這一題材。關良創(chuàng)作此幅《蘇三起解》(圖14? 1979年作,96×90厘米,上海中國畫院藏)時年近八十高齡,當時正是畫家迎來晚年創(chuàng)作的一個新高峰。此作《蘇三起解》中,畫家采取了背景留白之畫技,對人物的神態(tài)進行了著重凸顯。而蘇三和崇公道兩人稍微錯開的左右之勢,亦極具舞臺效果,暗示出一個戲劇發(fā)展的縱深空間。由此可見,中國戲劇藝術強調“動作語言”的內在精神,與關良的戲劇人物畫所具有的簡練概括、寫意傳神之畫風,具有相通之處。
關良的這幅水墨戲劇人物畫《太白醉寫》(圖15 關良79歲時創(chuàng)作),繪的是同名京劇中最有戲劇性的一幕,內容取材于《今古奇觀·李謫仙醉草嚇蠻書》。中國傳統戲劇是寫意文化的產物,全憑角色的唱、打、做、念表演之“神”才有“戲”,舞臺上人物和道具實在是不多,故別具一種簡練傳神的韻味。關良在這幅作品中正是抓住了“簡”與“神”兩點,完全描繪出了自己的意趣。畫作以若不經意的線條,中部繪出李白自信酣暢的神情,左右兩側再巧妙地表現出高力士與楊國忠既驚又怕的眼神,最后又在李白后方巧妙地寫出楊貴妃順服的表情。其處理看似“漫不經心”,實則滿是關良灌注其數十年對戲劇情節(jié)的熟識、對戲劇人物性格的把握,才使得其運用線條、墨色的睿智一覽無余。此作的妙趣在于虛實相生,尤其是畫紙上的人物如戲劇場景定格的瞬間般躍然紙上,因此作品極富表現力。
熱愛戲劇的關良以“戲”入畫,以“畫”品戲,曾言“戲劇表演與繪畫相通”。 華美的戲劇,寫意中國畫,夸張變形的西方現代繪畫,使得他以戲劇人物為題材,以東西方繪畫技巧為手段,對此披荊斬棘、繼往開來地進行了一生的探索和創(chuàng)造,成為了中國繪畫史上篳路藍縷的先行開拓者。并通過戲劇人物的情感, 在作品中抒發(fā)陽剛、浪漫的個人情懷, 彰顯出一種樂觀、剛正的民族精神,且令戲劇人物畫這一獨特的藝術形式,逐步形成了自身的“標簽”和“品牌”。現今筆者在此淺析其獨特藝術語言,企盼能為當代的中國畫壇提供一些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