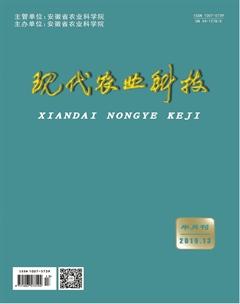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的客觀影響因素分析
胡曉峰
摘要 ? ?本文分析了影響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的客觀原因,認為傳統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兩大因素對農民參與農田整治有重要影響,需要在農田整治時引起重視。
關鍵詞 ? ?農田整治;農民參與;影響因素
中圖分類號 ? ?F323.211 ? ? ? ? 文獻標識碼 ? ?A
文章編號 ? 1007-5739(2019)13-0255-0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開放科學(資源服務)標識碼(OSID)
長期以來,在基本農田整治管理模式之中仍然堅持傳統的行政管理模式,堅持“長官意志或者專家至上”的原則,普遍將農民群體作為政策的接受者和輸入者,忽略了農民在政策中的主體地位,導致農民的參與意愿不能得到有效激發;部分農民的合理權益受損后得不到合理的訴求,既影響了農田整治項目的長期效益,也損害了政府在群眾中的良好形象。
從現實需要來看,農田整治需要農民參與,讓有參與意愿的農民參與進來、讓參與意愿不強的農民重新燃起參與的激情,是使基本農田整治規劃更加科學、項目實施更加順利、項目后期管護更加長久、項目效益長期發揮的重要保證。本文從傳統政治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等方面對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的影響因素進行分析、歸納、總結,以求對癥下藥,引導、鼓勵農民積極參與到農田整治項目中,使基本農田整治能夠達到預期效果。
1 ? ?影響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的客觀原因
1.1 ? ?傳統政治文化環境的影響
1.1.1 ? ?傳統政治文化環境導致了政府集權和官本位思想。高度集權的行政模式使地方政府在農田整治管理中占有絕對優勢,農田整治項目開展的決定權在當地政府;農民在決策過程中處于劣勢,只能被動地接受。官本位思想導致農民被排除在政府管理之外,農民的參與作用被忽視。在這樣的思想理念影響下,農民無法參與到農田整治過程中,信息獲得少而滯后,意見和建議也沒有通暢渠道反映。農田整治的立項選址、規劃設計、具體實施、驗收管理和后期管護都是政府在唱“獨角戲”,政府在農田整治過程中扮演決策者、執行者和管理者多種角色,把農民排除在項目建設和管理之外。項目實施和管理過程中的其他利益相關者都會對政府或者對上級負責,把政府和上級意圖放在首位,當政府或者上級的意圖與農民的意愿發生偏差時,往往犧牲農民的利益。于是,部分基層干部會采用封鎖消息甚至欺騙的手段迫使農民按照他們的意圖開展工作;即使有農民參與,也由于無法獲得充分有效的信息,導致其權益得不到充分尊重,使參與流于形式。
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政府機構在農田整治公共管理事務中處于特殊地位,很容易導致部分干部在行使職權時或多或少地謀求一些私利,如在農田整治涉及農民土地占用和拆遷補償時降低補償標準甚至不補償,損害了項目區農民的利益;或者采取多種手段來阻止農民參與,如封鎖項目消息、提高農民參與成本、設置參與壁壘等。行政機構的內部約束規范不健全、外部制約機制又不完全有效,使行政管理方式不規范,害怕農民參與。農民參與的一個重要障礙來自這種價值選擇上的困境[1-2]。
1.1.2 ? ?傳統政治文化環境壓抑了農民的個性追求,致使其參與意識淡薄。參與權利的強弱,往往取決于傳統文化的價值取向。由于我國的傳統文化是以“儒家文化精神”為理論基石,其在國家“大一統”“天下興亡匹夫有責”“仁義禮儀”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但是其推崇的“王權至上”“臣民意識”等導致人們積淀了“權威崇拜”的政治思想,認為自己不可能對社會政治產生影響,只有順從和依附權威。在長期的思維定式之下,民眾的政治意識嚴重缺失,對當代民主社會進步也產生了一定的消極影響[3-4]。在農田整治管理環節之中,多數農民受傳統文化的深遠影響,認為農田整治與自己無關,表達的建議和意見政府也不會采納,在表達意愿和維護權益方面顧慮重重,普遍缺乏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
1.1.3 ? ?傳統政治文化環境致使規劃機構和施工企業的角色錯位。目前,我國農田整治項目的管理是由政府主導,農田整治的規劃目標和實施效果是通過規劃機構和施工企業轉化而成。從角色扮演來看,規劃機構和施工企業是政府和當地農民的中間協調者,一方面因與政府機構的親密交流,能為政府決策和管理提出合理的建議和意見,有時可以利用其掌握的特有專業知識引導政府順利開展工作;另一方面,又能與農民無縫隙對接交流,能夠第一時間掌握農民的最迫切需要,體現了一定的社會公益性。然而,從現有的農田整治規劃和實施來看,規劃機構和施工機構習慣地認為自己是政府的代言人,唯“政府”是從,對政府負責,而忽視規劃和實施的公平公正性,甚至有的規劃機構和施工機構還認為,農民參與會限于無休止的爭吵,浪費規劃和具體施工時間,影響項目進度。因此,規劃機構和施工機構不重視農民參與,全靠技術方法解決問題,缺乏維護農民公共利益的意識,從而不可避免地會使農田整治項目成為少數利益集團謀利或者帶有傾向性意圖的手段。農田整治項目服務于社會大眾且具有一定的社會公益性,不能以某個利益集團價值為衡量標準,農田整治項目如果不能代表農民的公共利益也就失去了項目本來存在的意義[5]。
1.2 ? ?制度環境的影響
1.2.1 ? ?我國農田整治項目管理缺乏公眾參與程序化和法定化的制度安排。制度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需要程序化,不能朝令夕改。程序化是保障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立項、規劃設計、實施管理、驗收和項目后評價等各階段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因素。目前,我國在農田整治中農民參與決策過程有2種可以利用的正式渠道。一是人民代表大會和政治協商會議,人民可以通過選舉人民代表和推薦政協委員的方式參與政策過程;二是黨和政府開設的來信來訪、村民代表大會、村民座談會和問卷調查等渠道。前者是間接參與,對農民參與的要求較高,一般普通農民參與也較少;后者是直接參與,也是目前最常見的農民參與,但仍過于形式化,無實質性的效果[6-7]。
1.2.2 ? ?對農民參與農田整治決策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從我國土地管理立法現狀來看,立法只注重農田整治工作的實施和開展,對農民參與農田整治決策沒有明確規定;只是近10年以不同文件和政策強調項目開展時需要農民參與,但政策文件的法律力度不夠,沒有強制性,導致各地開展工作時隨意性很大。是否執行農民參與農田整治項目政策,成為當地政府自由裁量權范圍之內的事情,容易造成農民參與權利的缺失[8-9]。此外,我國的農田整治項目管理模式是政府強制實施、農民被動參與的單一管理模式,也容易造成農民的合法權益被侵害,部分行政主管部門或管理人員為了“圖省事”或者謀取不當利益,回避農民參與。
1.2.3 ? ?當前的政務信息公開制度也不能完全滿足農民參與的要求。現階段,政府在農田整治立項、規劃設計、實施管理、驗收和項目后評價過程中占據主導地位,政府的公務信息公開程度直接決定著農民參與的程度。盡管《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對政府信息公開的范圍、方式和程度都作了具體的規定,一些政府部門也結合實際情況出臺了相關的政府信息公開制度,但是在工作中仍然存在以下4個方面的情況。一是信息量的不對稱性,一方面政府部門公布的信息與實際需要公布的在量上不對稱,另一方面政府部門公開的信息量與農民需求的不對稱;二是信息公開時效的滯后性,包括信息時間滯后和內容滯后2個方面,前者表現為信息公開不及時,后者表現為信息公開的內容陳舊、過時而又不及時更新;三是既成事實性,即在事情發生后公布事項相關結果或者是將決策結果直接告知相關者,這種信息公開其實是排斥公眾參與;四是缺乏互動協調性,主要表現為過程參與者之間缺少協調互動或者是協調互動效果較差。正是因為這種政務公開僅是以公開為主要內容、以告知為主要目的,其特征是單向性、不具有互動性,實質上是一種處于告知和咨詢的參與初級階段,與真正的公眾參與還有一定的差距[10-11]。
1.2.4 ? ?我國農村集體土地產權不明晰限制了農民參與力度。一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晰。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是指農村集體土地所有者所擁有的、受國家法律保護的占有權、使用權、收益權、處分權等排他性專屬權利,所有權的主體具有確定性和唯一性。《憲法》《土地管理法》《土地承包法》等法律均明確規定農村集體土地歸農民集體所有,但并未明確規定這個集體到底是指哪一級。法律上的農村集體所有,實際上是集體成員共同所有,但是集體經濟組織成員是一個處于不斷動態變化的概念,致使農村土地所有權主體變得虛位。由于產權所有者整體性特征,多數農民會產生“搭便車”的心理,希望自己不參與、不付出勞動,坐享別人的成果。農村集體土地所有權主體不明晰也使農民難以把握自己的土地權利,對非自己承包的農田或土地整治工程漠不關心,認為與自己的利益無關,不愿意參與其中;有的是參與時給予的意見和建議不具有整體性和合理性,這就是項目出現“斷頭路”“畸形溝渠”的最主要原因[12-13]。二是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限制了農民參與積極性。農村集體土地承包經營權是指農村土地承包人對其依法承包的土地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一定處分的權利。《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耕地的承包期限為30年”。沒有農田所有權的農民不愿意花費太多的時間、精力關心農田的長期發展,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農民參與農田整治發展的事項。雖然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明確“保持土地承包關系穩定并長久不變,第二輪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長30年”,但農民的思想觀念不會即轉改變,因而農民參與的積極性仍然不高。
2 ? ?對基本農田整治農民參與工作的啟示
根據上文中對影響農民參與基本農田整治因素的分析可以發現,傳統文化環境和制度環境2個客觀因素對于農民參與基本農田整治過程和結果具有重要影響力。因此,在農田整治實際過程中,需要結合當地實際情況和民情具體問題具體分析,針對性地選取最佳方案并加以實施,從而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4-16]。
3 ? ?參考文獻
[1] 許霞.我國惠農政策執行研究[D].湘潭:湘潭大學,2011.
[2] 田北海,王彩云.民心從何而來?:農民對基層自治組織信任的結構特征與影響因素[J].中國農村觀察,2017(1):67-81.
[3] 張倩秋,曾秀蘭,譚靖.村級組織政策執行力調查與思考:以農村新型合作醫療政策在廣州市白云區神山鎮的實施為例[J].南方農村,2014,30(7):71-75.
[4] 王艷麗.論我國農村基層民主機制的完善[D].西安:西安科技大學,2010.
[5] 袁浩斌.高標準基本農田建設中利益博弈分析[D].廣州:華南農業大學,2016.
[6] 信桂新.山地丘陵區土地資源流動與整合機制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16.
[7] 吳詩嫚.農地整理過程中利益協調機制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4.
[8] 鄭華偉.農村土地整理項目績效的形成、測度與改善[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2.
[9] 夏春云.土地利用規劃實施評價與實施保障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11.
[10] 劉向東.基于利益相關者的土地整理項目共同治理模式研究[D].北京:中國地質大學,2011.
[11] 王長江.農村土地整治權屬調整與管理模式研究[D].北京:中國礦業大學,2011.
[12] 楊華均.土地開發整理項目社會影響評價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08.
[13] 董祚繼.中國現代土地利用規劃研究[D].南京:南京農業大學,2007.
[14] 謝雪群.農地整理過程中農民利益表達機制研究[D].武漢:華中農業大學,2013.
[15] 孫鈺霞.重慶市土地整理可持續發展評價[D].重慶:西南大學,2012.
[16] 張黎.重慶市推進城鄉統籌發展的土地整模式研究[D].重慶:西南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