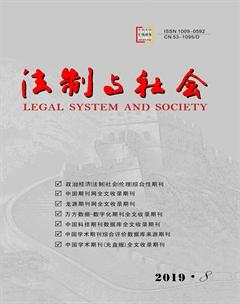“常州毒地案”的法學思考
關鍵詞 “常州毒地案” 土壤污染 責任主體 環境公益訴訟 土地修復
作者簡介:彭梓宜,首都師范大學附屬中學。
中圖分類號:D920.5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文獻標識碼:A ? ? ? ? ? ?? ? ? ? ?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9.08.019
2016年,江蘇常州外國語學校學生身體狀況的異常引起了社會對于學校附近修復的“毒”土壤的關注。同年,北京市朝陽區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共同對三家污染企業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提起公益訴訟。要求三家企業向公眾賠禮道歉,承擔污染土壤和地下水的環境修復費用3.7億元,并承擔原告因本訴訟而產生的費用。常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判決認為,污染土地已在當地政府的組織下,逐步完成了土地污染修復工作,原告目的已經實現,因此判決原告敗訴。此后,兩原告不服分別提起上訴,兩上訴人認為,環境污染修復責任應由污染者治理,政府只在履行其管理職能,因此政府為此所支出費用應由三家公司承擔。江蘇省高級人民法院二審最終判決,撤銷一審判決,三家污染企業在判決生效后應在國家級媒體上向公眾道歉,承擔上訴人因本次訴訟而產生的律師費及差旅費共46萬元,并且承擔一審判決和二審判決的受理費各100元,駁回上訴人的其它訴訟請求。
本案引發了三個法學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首先,土壤污染責任主體該如何界定?其次,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存在什么問題,該如何完善?最后,我國的土地修復法律及相關制度該如何完善?筆者將分別探究上述問題,并為建立健全我國生態文明相關制度、完善我國法治建設提出理論與實踐建議。
一、土壤污染責任主體的界定
關于土壤污染責任主體的分配問題,應當嚴格遵循“誰污染,誰治理”的環境法原則,并依照2017年《污染地塊土壤環境管理辦法》實行污染者治理的終身責任制。因此,在本案中,作為土壤污染者的三家污染企業江蘇常隆化工有限公司、常州市常宇化工有限公司、江蘇華達化工集團有限公司應當承擔土壤治理責任,當地政府不是承擔土壤治理的責任主體,而是土壤防治的監管主體。政府代替污染者履行土壤治理責任不符合污染者治理原則。政府在代替污染者治理土壤后,污染者應當支付相應的治理費用,政府可以向污染者追償其已支付的費用。此外,按照建設用地“凈地”出讓制度,本案中作為土地出讓方的三家污染企業應確保該土地符合“凈地”標準,對土地是否存在污染情況應告知受讓人,以確保受讓人對土地污染情況的知情權,否則受讓人不承擔污染責任。本案中,三家污染企業將原占有土地出讓時并未遵循“凈地”標準,因而其試圖以“環境污染修復責任應由土地受讓人承擔”為由拒絕承擔土壤污染責任不具有正當性、合法性。
二、完善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制度
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特別是原告有待進一步擴大。本案中,訴訟原告以及上訴人自始至終是北京市朝陽區環保組織自然之友和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綠色發展基金會兩家環保組織。環保組織作為公益訴訟原告符合《侵權責任法》和《民事訴訟法》的相關規定,即對土地污染等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法定組織可提起公益訴訟。但是《民事訴訟法》第55條還規定檢察機關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現行立法并未規定自然人可以提起環境公益訴訟,這會產生至少兩方面不良影響,僅就本案而言,因土壤污染受害學生的合法權利未能得到充分保護,且不利于受污染土地的及時修復。當然,以自然人為原告的訴訟主體需要嚴格限制,因為若允許所有間接的利益相關者行使訴權的請求權,會導致環境公益訴訟領域濫訴現象,浪費司法資源。為了平衡利益相關者和司法資源的關系,政府機關(檢察院)和環保組織可以代表間接利益相關者行使訴權請求權。
三、規范土地修復法律等相關制度
(一)土地修復訴訟費分擔
本案一審判決訴訟費用全部由原告兩家環保組織承擔,該巨額訴訟成本的分配明顯不合理。雖然二審判決將該成本轉移到敗訴的被上訴人,但仍引發兩個方面的反思:其一,若上訴方仍敗訴讓其承擔所有訴訟費是否合理;其二,二審將巨額訴訟費轉移被上訴方是否合理。關于這兩點疑問可以借鑒美國和德國環境公益訴訟費制度的成功經驗。例如,美國在環境公益訴訟制度上建立多元性的費用規則,并采用實質性減輕或免除公眾或其他團體所承擔的訴訟成本方式,以激勵環境公益訴訟參與者能夠積極參與訴訟。又如,德國利他團體訴訟的收費機制對我國具有啟發性,其每一審級的訴訟費用都比較廉價,對環保組織起到了激勵作用;環保組織可以通過募捐等方式解決訴訟成本問題;此外還有訴訟保險等靈活的費用配套制度。根據美、德的經驗,我國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也應當適度減免環保組織的訴訟費用,建立多元化的訴訟費用來源,最終激勵我國環保組織訴訟積極性,達到修復土壤等環境保護目的。
(二)環境影響評價制度
規劃環評作為戰略環評的一種方式,可以彌補建設項目環評的缺陷,真正實現環評制度從末端治理到源頭預防的轉變,因而能最大限度預防環境問題的產生。我國2002年《環境影響評價法》和2009年《規劃環評條例》都規定了規劃環評是我國環評的重要內容。在本案中,三家污染企業的選址依據是《常州市城市總體規劃用地規劃圖(2004-2020)》,然而該規劃圖中并未提及污染土壤的治理和修復,也并沒有公開資料顯示該規劃進行了實質而有效的環評。可見,正是由于在城市規劃和企業選址的過程中,忽略了規劃環評特別是排污可能造成土壤污染的評估,才引發了嚴重的“毒地”事件,對人體健康、生態環境以及社會安全等方面造成了一系列損害。因此,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應當進一步明確規劃環評的實施主體與監管主體,建立更嚴格的責任制度,以強化規劃環評制度的實施力度。使規劃環評成為城市建設特別是工業企業建設的必要環節,將環境污染危害從末端治理提前到源頭防治。
(三)雙重訴訟目的的平衡
本案在一審判決中,法院以污染土地已在當地政府的組織下逐步完成了土地污染修復工作為由判決原告敗訴。然而該判決因對土地污染和訴訟成本的不合理分配而飽受爭議。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主要目的是消除環境公共利益損害,同時需要公平合理地配置因環境公共利益損害而產生的成本。為了平衡二者關系,二審法院撤銷了一審判決,要求三家污染企業向公眾道歉,承擔本案所產生的一切訴訟費,并歸還當地政府對已支出的污染治理費用的追償權。按照法律規定的侵權要件,環境公共利益損害的救濟,只需要滿足損害行為、損害結果和因果關系三個方面的條件,因此要求三家污染企業承擔一切訴訟費用具有正當性。將已填補修復土地費用追償權歸還政府,一方面體現了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裁量權,另一方面也能提高修復土地等環境行政執法的公平與效率。二審法院的判決體現了環境民事公益訴訟中兼顧環境公共利益與合理分配環境損害責任的雙重目的,既能夠落實土壤污染責任中“誰污染,誰治理”原則,又提高了環保組織等訴訟原告保護環境的積極性,對環境民事公益訴訟制度的發展以及生態環境保護具有重要意義。
四、結論
“常州毒地案”一審判決引發社會廣泛批判,二審最終判決三家污染企業向公眾道歉,承擔上訴人在一、二審判決的所有訴訟費。本案引發一系列環境污染公益訴訟、土地污染防治理論與實踐的問題。首先,關于污染責任主體該如何分配,應當依照“誰污染,誰治理”原則,明確污染企業是污染責任主體。其次,我國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范圍特別是原告需要進一步擴大,環保組織、政府、檢察機關以及直接利害關系人都應當參與到環境公益訴訟中,以全方位、及時保護生態環境。最后,我國的土地修復及相關法律仍存在諸多問題:其一,我國訴訟費用分配應當借鑒美國、德國等國外先進制度,適當減免環保組織等訴訟原告的訴訟費用,建立多元化的訴訟費用來源機制;其二,我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特別是規劃環評制度對實現生態環境保護的源頭預防至關重要,應當進一步明確規劃環評的主體與責任制度。此外,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的最終目的是消除環境公共利益損害以及公平合理地配置因損害所產生成本,因此環境公益訴訟審判實踐中應當注重平衡兩種訴訟目的,以杜絕類似于本案一審的錯誤判決。
參考文獻:
[1]江蘇高院對“常州毒地案”作出終審判決[N].法制日報,https://www.cenews.com.cn/legal/201812/t20181229_891090.html,2019-03-31.
[2]李茹彥.常州毒地案評析[D].湖南大學,2018.
[3]馬騰.我國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完善研究——對常州毒地案一審判決的法理思考[J].中國政法大學學報,2017(4).
[4]何香柏.風險社會背景下環境影響評價制度的反思與變革——以常州外國語學校“毒地”事件為切入點[J].法學評論,2017,35(1).
[5]徐以祥,周驍然.論環境民事公益訴訟目的及其解釋適用[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7,27(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