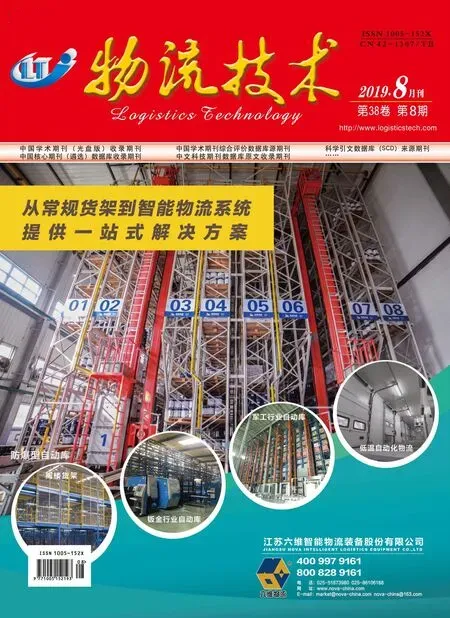中國城市群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其機制
邱晨園,梁紅艷
(福州大學 經濟與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116)
1 引言
城市群已成為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區域協調發展的重要途徑。交通基礎設施作為城市群一體化的重要支撐和先導條件,被視為區域經濟發展的命脈。推動城市群交通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構建綜合交通基礎設施體系,對促進城市群區域經濟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那么,當前我國城市群交通基礎設施是否促進了經濟一體化發展?在不同城市群中,其作用存在怎樣的差異?不同基礎設施的作用又存在怎樣的差異?這種促進作用的主要機制是什么?針對這些問題,本文重點考察我國城市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其機制,并對不同城市群進行比較分析,據此提出城市群一體化發展的針對性建議與差異化政策。
關于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發展的影響,早期的研究偏向分析交通基礎設施的直接影響。Aschauer[1]率先測算了主要交通基礎設施的產出彈性,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確有促進作用。Munnell[2]也指出交通基礎設施的確能推動經濟增長。交通基礎設施影響經濟發展的另一個重要途徑是提高區域經濟聯系的緊密度,通過中心城市的集聚與擴散效應帶動區域經濟發展。鑒于此,該領域的研究開始側重于考察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網絡外部效應。Boarnet[3]的研究發現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公路對經濟增長存在負向空間溢出效應。Chen and Haynes[4]則研究發現美國公路、鐵路和航空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空間溢出效應。一些學者也研究了中國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5-12],且大多都發現交通基礎設施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明顯的空間溢出效應。
關于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有研究從多個角度進行了有益探索,但還存在一些可拓展深化之處:(1)在空間單元方面。已有文獻主要選擇全國、東中西部地區、省域等作為研究的空間單元,但以城市群作為區域空間單元的研究相對較少。(2)在研究對象方面。已有文獻通常以交通基礎設施整體展開研究,較少探討不同類型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的空間溢出效應的差異。(3)在研究內容方面。已有研究僅考察了交通基礎設施對經濟增長空間溢出效應的存在性,而忽略了這種空間溢出效應產生的機制。鑒于此,本文以中國城市群為空間單元,研究不同城市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并從交通基礎設施影響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的角度探討其溢出機制。
2 模型構建與變量說明
2.1 模型構建
由于無法獲得城市鐵路里程數據,本文無法將各類交通基礎設施存量納入生產函數,通過估計其空間滯后變量的系數來考察其溢出效應。考慮到交通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主要通過影響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進而產生溢出效應,本文即利用交通基礎設施對應的時間距離設定空間權重矩陣,通過分析時間距離權重矩陣下物質資本、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等生產要素的跨地區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的影響,來考察我國城市群交通基礎設施的空間溢出效應及其機制。
空間滯后模型(SAR)、空間誤差模型(SEM)和空間杜賓模型(SDM)是分析地區間空間依賴性的常用模型[13]。在模型估計之前,需利用(Robust)LM檢驗來判斷SAR或SEM是否比不含空間效應的模型更適宜于研究樣本[14]。如果SAR和SEM中,任意一個成立或兩者同時成立,應進一步考慮SDM是否更適宜[15]。基于此,本文首先構建如下SDM模型:

其中,i表示地區(i=1,2,...,N),t表示時間(t=1,2,...,T)。Yit代表城市i在t時期的經濟產出;Kit,Lit,Hit分別表示城市的物質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水平;GOVit、POPit、FDIit、UBDit、EXPit分別表示城市的政府干預程度、人口密集程度、外商投資、城鎮化程度、出口貿易額;wij為空間權重矩陣W的元素。β1至β8為對應變量的系數,ρ和θ為空間滯后系數。μi、vt分別表示空間效應、時間效應;εit是服從獨立同分布的誤差項。
LeSage and Pace[16]指出,采用點估計分析空間溢出效應,所得結論有偏差,并提出了偏微分求解方法。通過該方法,可以相對更準確地得到解釋變量產生的直接影響和間接影響(即溢出效應)。本文在后續研究過程中,采用該方法展開分析。
2.2 變量說明
(1)被解釋變量(Y)。本文利用人均GDP衡量城市經濟產出。為消除價格因素,利用城市GDP平減指數將人均GDP換算成以2003年為基期的不變價。
(2)核心解釋變量。本文通過分析交通基礎設施對物質資本、勞動力與人力資本這三種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的影響來考察其溢出機制。三種生產要素的變量說明如下:
①物質資本(K)。資本存量估算通常選擇永續盤存法,其公式為Kit=(1-δit)Kit-1+Iit,其中Kit和Kit-1分別表示城市i在第t年和第t-1年的資本存量,Iit為城市i第t年的固定資產投資額,δit為資產折舊率。資本存量估算需要確認以下四個變量:當年投資額:利用各城市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利用全國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計算得到以2003年為基期的價格縮減指數。折舊率:采用張軍等[17]的測算結果,設定為9.6%。基期資本存量:采用Hall and Jones[18]提出的增長率法,表示為Ki,2003=Ii,2003/(gik+0.096),其中Ii,2003為城市i在2003年按當期價格計算的固定資產投資額,gik為城市i在2003-2017年的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率,0.096為固定資產折舊率。
②勞動力投入(L)。本文利用城市就業人數指標衡量勞動力投入。具體而言,利用全市范圍內的單位從業人員與私營和個體從業人員之和計算就業人數。
③人力資本水平(H)。本文利用受教育時間衡量人力資本水平,計算公式為:H=6S1+12S2+16S3,其中S1、S2、S3分別代表該城市接受小學、中學、大學教育的人數。
(3)控制變量。為了避免遺漏變量的可能,本文選取政府干預程度、人口密集程度、外商投資、城鎮化程度、出口貿易額作為控制變量。①政府干預(GOV),本文采用扣除了教育和科研支出后的財政支出表示政府干預程度。②人口密集程度(POP),本文利用全市人口數量與該市面積的比值表示城市人口密集程度。③外商投資額(FDI),本文采用當年實際使用外商投資金額代表外商投資額。④城鎮化程度(UBD),本文利用城鎮人口占城市總人口的比重表示城鎮化程度。⑤出口貿易額(EXP),本文利用城市出口貿易額代表出口能力。
(4)空間權重矩陣(W)。本文借鑒王雨飛和倪鵬飛[19]的方法,將基礎設施對應的時間距離空間權重矩陣設定為其中,wij為空間權重矩陣W的元素;tij為城市i經普通公路、高速公路或鐵路至城市j所需時間為城市i與j間三種交通基礎設施對應的最短總里程數,v為對應交通工具的運行速度。三種基礎設施對應的dij利用中國公路網絡地圖與中國鐵路網絡地圖測算得到;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的車輛運行速度v根據《中國人民共和國公路工程技術標準》與《鐵路安全管理條例》來確定。
2.3 研究區域說明與數據來源
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開放程度高、創新能力強的三大區域。本文選取這三大城市群展開研究,并根據相關批復文件對其空間范圍進行界定,最后確定三大城市群共包括45個城市。本文使用中國三大城市群45個城市2003-2017年的面板數據展開研究,所有數據來源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區域經濟統計年鑒》、《中國城市統計年鑒》,以及各城市的統計年鑒和經濟發展統計公報。其中,缺失的數據采用線性插值法補齊。
3 檢驗結果與分析
本文按照模型選擇步驟,分別確定三大城市群在不同空間權重矩陣下的空間計量模型,進而對模型估計結果展開分析。其中,控制變量的影響不是本文關注重點,故不做具體分析。
3.1 長三角
表1給出了長三角城市群的非空間面板模型與三種空間權重矩陣下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根據表1,非空間面板模型的空間固定效應和時間固定效應都具有聯合顯著性,因此各空間權重矩陣下的(Robust)LM檢驗結果也相應在雙固定效應模型的基礎上得到。
(1)在普通公路與高速公路對應的時間距離權重矩陣下,模型均未通過(Robust)LM檢驗,此時應選擇非空間面板模型。這表明長三角普通公路與高速公路并未通過影響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
(2)在鐵路對應的時間距離權重矩陣下,根據(Robust)LM檢驗結果,雙固定效應SDM的Wald和LR檢驗結果以及Hausman檢驗結果,應選擇雙固定效應SDM。針對雙固定效應模型的估計,本文采用Lee and Yu[20]的糾偏方法進行了修正。表2給出了SDM中核心變量的直接影響、溢出效應與總效應。①根據表1第5列,空間滯后系數ρ的估計結果為0.458 0,意味著隨著鐵路互聯互通水平增強,本地經濟增長1%,周邊地區經濟將增長0.458 0%,意味著鐵路對長三角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溢出效應。②關于溢出機制,根據表2,物質資本的溢出效應為1.326 6 且在1%的水平上顯著,即本地資本存量增加1%,周邊地區人均GDP將增加1.326 6%,說明在長三角,鐵路互聯互通有助于物質資本在城市間擴散,從而促進周邊地區經濟增長;勞動力投入的溢出效應為正但不顯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溢出效應為-2.157 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這意味著在長三角,本地人力資本水平增加1%,周邊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將降低-2.157 7%,可能是隨著鐵路互聯互通水平增強,人才不斷向核心城市集聚,對周邊地區產生了虹吸效應,從而不利于周邊地區經濟增長。
3.2 珠三角
表3給出了珠三角城市群的非空間面板模型與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根據(Robust)LM檢驗結果、雙固定效應SDM模型的Wald和LR檢驗結果,以及Hausman 檢驗結果,在普通公路、高速公路與鐵路對應的三種時間距離權重矩陣下,隨機效應SDM 模型均更有效。表4給出了三個SDM模型中核心變量的直接影響、溢出效應與總效應。
(1)根據表3,三個模型的空間滯后系數ρ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354 0、-0.410 0、0.996 9,而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表明在珠三角,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的負向溢出效應,而鐵路則具有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

表1 長三角的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

表2 長三角核心變量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
(2)根據表4,分析三種交通基礎設施的溢出機制。①在普通公路的作用下,物質資本的溢出效應為正但不顯著;勞動力的溢出效應為0.759 2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說明在珠三角,普通公路互聯互通有助于勞動力在城市間擴散;人力資本水平的溢出效應為-0.815 7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是在普通公路影響下,人才向核心城市集聚,造成周邊地區人才匱乏,不利于其經濟發展。②在高速公路的作用下,物質資本與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都不顯著;勞動力的溢出效應為1.235 7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③在鐵路的作用下,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都不顯著;物質資本的溢出效應為0.559 2 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

表3 珠三角的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

表4 珠三角核心變量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
3.3 京津冀
表5給出了京津冀城市群的非空間面板模型與空間面板模型的估計結果。根據(Robust)LM檢驗結果、雙固定效應SDM模型的Wald和LR檢驗結果,以及Hausman 檢驗結果,在普通公路、高速公路與鐵路對應的三種時間距離權重矩陣下,隨機效應SDM 模型均更有效。表6給出了三個SDM模型中核心變量的直接影響、外溢效應與總效應。
(1)根據表5,三個模型的空間滯后系數ρ的估計結果分別為-0.862 0,0.103 3,-0.725 0,而且都在1%的水平上顯著,這表明在京津冀,普通公路和鐵路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顯著負向溢出效應,而高速公路則具有顯著正向溢出效應。
(2)根據表6,分析三種交通基礎設施的溢出機制。①在普通公路的作用下,物質資本與勞動力的溢出效應均不顯著;人力資本水平的溢出效應為-0.768 1 且在5%的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依然是人力資本向核心城市集聚而造成的區域內生產要素高度不均衡。②在高速公路的作用下,物質資本的溢出效應不顯著;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分別為-0.175 3 與-0.656 7 且都在10%的水平上顯著,可能的原因與前文一致。③在鐵路的作用下,物質資本的空間溢出效應不顯著,這表明京津冀鐵路未通過影響物質資本跨地區流動而對經濟增長產生顯著的溢出效應;勞動力與人力資本的空間溢出效應分別為-0.189 0 與-0.838 3 且都通過了顯著性水平檢驗,這與高速公路的表現一致。
3.4 三大城市群的對比分析
根據前文檢驗結果,三大城市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和鐵路對區域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其機制的對比見表7。
(1)關于不同交通基礎設施的溢出效應。長三角的鐵路、珠三角的鐵路和京津冀的高速公路對區域經濟增長都具有正向溢出效應;而珠三角的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京津冀的普通公路和鐵路都表現出負向溢出效應,表明這些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使得核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生產要素產生虹吸效應,不利于周邊地區經濟增長。
(2)關于不同交通基礎設施的溢出機制。①關于物質資本,長三角與珠三角的鐵路均有利于物質資本擴散而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而其他城市群其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未能通過促進物質資本跨地區流動而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溢出效應。②關于勞動力,珠三角的普通公路與高速公路互聯互通均有助于勞動力擴散,從而帶動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而京津冀的高速公路與鐵路的互聯互通在改變城市時空關系時,造成周邊地區勞動力流失,不利于周邊地區經濟發展;而其他城市群其他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未能通過促進勞動力跨地區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顯著溢出效應。③關于人力資本,長三角的鐵路、珠三角的普通公路、京津冀的普通公路、高速公路和鐵路,使得人力資本向核心城市高度集聚,致使周邊地區人才流失,不利于其經濟增長。總體來看,京津冀交通基礎設施的發展,使核心城市對周邊地區生產要素形成了相對更明顯的虹吸效應,阻礙周邊地區經濟發展,不利于城市群整體繁榮發展。

表5 京津冀的空間計量模型估計結果

表6 京津冀核心變量的直接效應、溢出效應和總效應

表7 三大城市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的溢出效應及其機制對比
4 研究結論與政策啟示
本文利用2003-2017年的城市面板數據,通過構建空間計量模型,考察了三大城市群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對經濟增長的溢出效應及其溢出機制。主要得到以下結論:(1)在長三角,鐵路通過促進物質資本跨地區順暢流動對區域經濟增長產生正向溢出效應,而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沒有表現出顯著的空間溢出效應。(2)在珠三角,鐵路有利于物質資本擴散,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則有利于勞動力擴散,但普通公路導致人力資本向核心城市高度集聚。在擴散效應與極化效應的綜合作用下,普通公路和高速公路對經濟增長具有負向溢出效應,而鐵路表現出顯著的正向溢出效應。(3)在京津冀,高速公路和鐵路導致勞動力向中心城市高度集聚,普通公路、高速公路、鐵路導致人力資本向中心城市高度集聚,但三種交通基礎設施都未帶來物質資本流動的經濟增長效應。在多種因素的綜合作用下,普通公路和鐵路對區域經濟增長最終表現為負向溢出效應,高速公路則表現出正向溢出效應。
根據上述研究結論,可以得到以下幾點政策啟示:(1)各城市群需認識自身的交通基礎設施短板,重視薄弱環節。其中,長三角、珠三角在當前“一核五圈四帶”、“雙引擎多支點”網絡格局基礎上應加強普通公路與高速公路互聯互通;京津冀在當前“一核,雙城,三軸,四區,多節點”網絡格局基礎上需加強普通公路與鐵路互聯互通。(2)當前三大城市群中,僅少數區域個別類型交通基礎設施通過促進生產要素跨地區流動對經濟增長帶來了溢出效應,更多地表現為促進生產要素空間極化或無明顯推動作用。鑒于此,各級政府需統籌城市群交通基礎設施規劃、建設與運營,打破城際壁壘,增強互聯互通水平,從而推進城市群經濟一體化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