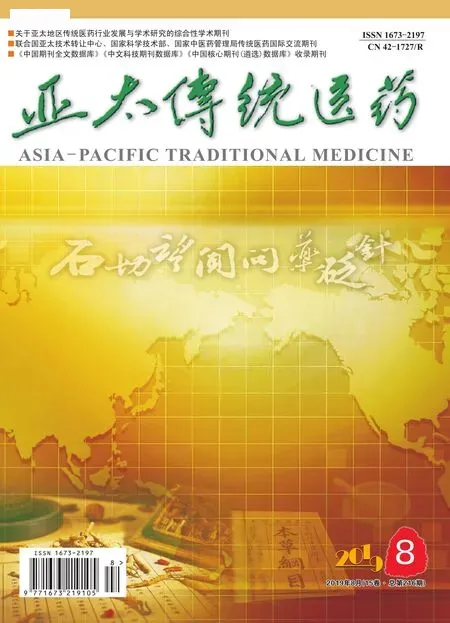內外合治慢性腎臟病臨床研究
王紅軍,張 磊,李 俊
(駐馬店市中醫院,河南駐馬店 463000)
有研究顯示,我國慢性腎臟病(chronic kidney disease,CKD)發病率為10.8%,約為1.2億人[1],約有2%的患者會進展為尿毒癥。延緩CKD患者進入腎臟替代治療,中醫藥治療受到社會廣泛認可。已有很多研究表明[2-5],采用結腸透析聯合中醫藥治療能夠降低CKD患者血肌酐、尿素氮、尿酸等水平,改善患者癥狀,提高患者營養水平,保護殘余腎功能。結腸透析由于其療效確切、操作方便、并發癥少,患者依從性較好,可有效提高CKD患者的生活質量,因而被廣泛接受和認可[6]。本研究采用內外合治法對來我院就診的CKD3~5期患者進行治療,取得了較好的臨床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臨床資料
根據K/DOQ1(2002年)CKD診斷標準,選取2015年7月-2018年10月于我院就診的患者,選取180例CKD 3~5期患者,隨機分為3組各60例,分別為常規結腸透析組(A組)、結腸透析加中藥保留灌腸組(B組)、結腸透析配合中藥保留灌腸組加補腎解毒顆粒口服(C組)。入組的180例患者中,試驗結束,A組脫落8例,B組脫落11例、C組脫落13例,最終148例患者納入研究,3組患者脫落情況見表1。3組患者臨床資料兩兩組間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均>0.05),組間均具有可比性,詳見表2。

表1 3組患者脫落率 (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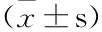

組別例數(n)男/女(n)年齡(歲)SCr(μmol/L)BUN(mmol/L)UA(μmol/L)HB(g/L)ALB(g/L)A組5228/2448.25±6.55390.24±188.6720.05±9.73498.12±99.29109.82±10.1236.33±6.87B組4920/2950.77±8.56368.54±168.9416.33±6.78512.20±100.2999.43±9.8740.65±10.86C組4725/2253.98±9.13300.39±130.6718.93±7.29479.56±50.29102.06±18.1238.99±9.09χ2/F0.255.9873.4185.9836.9073.4503.698P0.1940.5491.9800.7630.5580.9961.234
1.2 納入及排除標準
根據K/DOQI(2002年)CKD診斷標準,簽署知情同意書,獲得醫院倫理委員會批準,所有程序均符合倫理標準。排除標準:嚴重痔瘡、腸內炎癥出血等結腸透析禁忌證患者;有嚴重心腦血管疾病、呼吸、消化、血液系統疾病者;急性腎衰竭患者;病情危重,需行腎臟替代治療者;已行腎臟替代治療者;有嚴重感染、電解質紊亂、出血、休克等疾病者;有精神障礙及依從性差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女性。
1.3 治療方法
基礎治療:3組患者均給予常規對癥支持治療,積極糾正原發疾病,如嚴格控制血糖、血壓、糾正貧血等。
A組給予結腸透析治療。應用廣州今健JS-308D型結腸透析機。治療前,囑患者自行排便,取左側臥位,治療分2個步驟進行:第一步,采用反滲水給予全結腸灌洗至腸道干凈無糞便排出;第二步,給予透析液開始結腸透析,適當保留一定時間,然后更換透析液再次灌入。每周3次。
B組在A組患者治療基礎上加用中藥保留灌腸治療。結腸透析后,待腸內透析液排空后,灌注中藥,保留0.5 h左右,每周3次。灌腸中藥為我院院內制劑,組成:生大黃、煅龍骨、蒲公英、白花蛇舌草、六月雪、煅牡蠣、積雪草、槐米、熟附子、三七、澤瀉、青黛等。
C組在 B組患者治療基礎上口服我院院內制劑中成藥補腎解毒顆粒,每周3次,補腎解毒顆粒于2015年獲得河南省藥監局制劑批號(豫藥制字Z05170038),其主要組成為熟大黃、六月雪、西洋參、蟲草菌粉、山藥、白術、蒲公英、淫羊藿、丹參、黃芪、黨參等。補腎解毒顆粒每天1包。
1.4 觀察指標
分別統計患者治療前后HB、SCr、BUN、UA、ALB指標;觀察治療前后兩組患者心電圖、谷丙轉氨酶、谷草轉氨酶;記錄治療期間患者的不良反應。
1.5 統計學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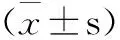
2 結果
2.1 3組患者治療前后腎功能變化情況
治療6個月后,3組患者血肌酐、尿素氮、血尿酸較治療前均下降(P<0.05),組間比較,B組、C組均優于A組(P均<0.05)。見表3。


組別時間SCr(μmol/L)BUN(mmol/L)UA(μmol/L)A組治療前390.24±188.6720.05±9.73498.12±99.29治療后333.12±130.45*14.78±6.98*444.78±67.36*B組治療前368.54±168.9416.33±6.78512.20±100.19治療后297.66±89.23*△10.98±5.12*△430.63±90.77*△C組治療前300.39±130.6718.93±7.29479.56±50.29治療后210.43±66.12*△8.87±3.76*△△384.55±34.17*△△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治療后A組比較,△P<0.05,△△P<0.01。
2.2 3組患者治療前后血紅蛋白、白蛋白變化情況
治療6個月后,3組患者血紅蛋白量、白蛋白量較治療前均有升高(P<0.05),B組、C組升高水平與A組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均<0.05)。見表4。


組別時間HBALBA組B組C組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治療前治療后109.82±10.12118.12±9.87*99.43±9.87115.20±10.12*102.00±18.12120.12±13.08*△△36.33±6.8739.70±6.87*40.65±10.8644.44±6.17*38.99±9.0945.62±6.31*△△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A組治療后比較,△P<0.05,△△P<0.01。
2.3 不良反應
治療期間,有5例患者出現輕微肝酶升高,給予聯苯雙酯滴丸口服后肝酶正常;有3例患者出現腹脹加重,給予適當調整藥物、飲食后改善;2例患者出現心慌、汗出,心電圖顯示竇性心動過速,給予減慢結腸透析進出水速度后緩解。其余患者未出現明顯不良反應。
3 討論
灌腸法首見于《傷寒論》陽明篇中的潤導法,通腑泄濁,“魄門亦為五臟使,水谷不得久藏……六腑者,傳化物而不藏,故實而不能滿也。”為結腸透析及中藥保留灌腸的中醫治療提供了理論依據。慢性腎臟病的根本病機為脾腎虧虛,濕瘀互結。脾腎虧虛,開闔失司,升降失常,水液代謝障礙致水濕內停,郁久化熱,濁邪壅塞,瘀血凝滯,其累及全身,出現惡心、嘔吐、頭暈、乏力、水腫、少尿等癥狀。本病屬本虛標實、虛實夾雜之證,故治療宜補瀉兼施、正邪兼顧。慢性腎衰竭患者腎臟清除尿素、肌酐、尿酸等能力降低,而通過腸道排毒是中醫治療的重要方法之一,聯合我院院內制劑補腎解毒顆粒治療,能提高臨床療效。補腎解毒顆粒主要組成為熟大黃、六月雪、西洋參、蟲草菌粉、山藥、白術、蒲公英、淫羊藿、丹參、黃芪、黨參等。大黃通腑泄濁、蕩滌腸胃,現代研究表明,大黃具有延緩腎小球硬化,從而改善腎臟高代謝狀態、調節免疫、清除堆積的氧自由基等功能[7];有研究表明[8],大黃可抑制毒素生成,可增加雙歧桿菌、乳酸桿菌,減少大腸桿菌,進一步改善患者胃腸道紊亂。蟲草菌粉可增強機體免疫力,扶正氣以驅邪外出。黃芪“能補元陽,治虛勞,長肌肉”,此方中起到補中益氣的作用,聯合淫羊藿、黨參、西洋參助腎氣恢復,有化生氣血之功。同時配伍活血化瘀藥物丹參,補氣不留瘀。山藥、白術調理中焦脾胃,固護后天之本。六月雪、蒲公英清熱化濁,驅邪實,邪去正可安。全方選藥精煉,補瀉兼施,正邪兼顧,共奏補腎泄濁之功。
本研究表明,結腸透析配合中藥保留灌腸加補腎解毒顆粒口服組(C組),血肌酐、尿素氮、尿酸水平下降與單獨使用結腸透析組(A組)及結腸透析加中藥保留灌腸組(B組)比較,差異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血紅蛋白量及白蛋白量升高也具有顯著統計學意義(P<0.01)。推測原因:①結腸透析直接將腸道代謝廢物及毒物直接排出;②中藥保留灌腸使中藥通過直腸黏膜及靜脈吸收直接到達血液,使腸道局部血藥濃度升高,研究表明[9],我們每日攝入的蛋白質、代謝產物及毒素3/4由腎臟排出,1/4由腸道排出,而慢性腎衰竭患者腸道毒素可由1/4上升到4/5,通過中藥保留灌腸使腸道局部血藥濃度升高,抑制氧化應激反應,清除自由基,抑制炎癥因子生成[10];③口服補腎解毒顆粒到達全身,達到穩定血藥濃度的作用,可起到改善全身微循環及微炎癥狀態的作用[10-11]。
綜上所述,內外合治慢性腎臟病能改善患者營養狀態,延緩病情進展,值得臨床推廣應用。但本研究脫落病例比較多,屬于單中心臨床試驗,結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倚,缺少后續長期隨訪觀察,因此有待進一步大樣本多中心隨機對照觀察試驗研究。